珍.奧斯汀如何變成男性讀物
英文中,珍.奧斯汀的粉絲有個專稱,叫「Janeite」,意即「拜珍教徒」。這個單字的來源是吉卜齡的同名短篇。該故事發表於一九二四年,情節如下:
主角是個粗人,在歐戰中負傷仍不退役,自願上西線做個炊事小兵。他發現,高級軍官之間好像有個秘密結社「拜珍教」,無論誰,不管層級多低,只要讀透珍.奧斯汀,說出通關密語,就能與這些軍官平起平坐。主角開始囫圇吞棗,讀不懂亦不罷休。一日敵軍炮火格外猛烈,整個部隊都陣亡了,身負重傷的主角出口即珍言珍語,巧的是搶救傷患的護士亦嗜珍如命,主角因此受到特別照護得以存活,等於是珍二姑救了他一命。戰後回國,他依然天天讀救命恩人的書,邊讀邊緬懷死於戰壕的那些弟兄。因為有那幾本小說可讀,戰爭於他甚至亦有了可愛之處。故事末尾讀者才知道,主角其實已經有一點瘋了。
奧斯汀的世界莫非舞會、牌局、適合散步的莊園綠野,〈拜珍教徒〉中的世界卻是炮火、操課、血泥橫飛的陰暗戰壕。奧斯汀筆下角色都是君子遠庖廚,家中皆有僕歐,〈拜珍教徒〉寫的卻是一名談吐粗鄙的炊事小兵。奧斯汀的結局總是大團圓,〈拜珍教徒〉的結局卻是一整代青年的死亡與瘋狂。然而,主角從頭到尾卻說得眉飛色舞,開開心心,因為他讀珍奧斯汀。
故事背後的故事其實是如此:大戰一開打,吉卜齡的獨子被送上戰場,吉卜齡就開始靠著讀奧斯汀排遣思子之情。七個月後前方傳來愛子失蹤的消息,日子一個月一個月過去,音訊渺然,吉卜齡的心情漸漸從焦慮轉為絕望,但仍繼續讀他的奧斯汀。所以他寫〈拜珍教徒〉,有很大的意味是為了悼亡,同時也向奧斯汀表達故事中主角所感受到的那種感激,感激她陪一個父親度過最難熬的歲月。
「拜珍教」組織當然是吉卜齡的想像。但若說大戰中許多英軍陣亡將士口袋中皆有一冊奧斯汀,卻離事實不遠。大戰開打不久,英國政府就廣印小說往前方送,印最多的正是奧斯汀,因為官兵反應最愛讀的就是她。奧斯汀不碰戰爭是有名的,雖然在她創作的年代,拿破崙戰爭正如火如荼,報紙每日都是戰事進展,她的作品卻全無煙硝味,頂多是幾個紅衣軍官以舊情人(《勸導》)或調情聖手(《傲慢與偏見》)的身分出現而已。沒想到百年後,竟是由另一場大戰將其風靡程度推向另一高峰,由一位以歌頌武勇著稱的男性作家,以一則戰爭故事向她致最高敬意。
所以說,一進入二十世紀,奧斯汀就不再只是女性讀物了。至於二十世紀晚期,最有名的「拜珍教徒」無疑是管理大師杜拉克。杜拉克文學素養甚佳,著作中信手拈來就是一本小說名著,不過眾所周知,他最愛讀的一直是奧斯汀,最常提到的也是她。原因不難理解,杜拉克給自己的定位是社會生態觀察者,小說家中最符合這個標籤的正是珍奧斯汀。她不像狄更斯與喬治桑那樣,有社會改革的雄心,作品只充塞她對世情百態的觀察。
六本小說寫的都是待嫁女兒,老半天都不知要嫁給誰,總要到結尾才搞定,這樣的情節怎能給管理學帶來什麼啟發?當然能!奧斯汀是最愛提錢的作家,書中角色她都交代清楚:有沒有錢,有多少錢,有沒可能更有錢。情節的重要轉折常是錢在做怪。以《理性與感性》為例,故事展開,就是愛蓮娜姊妹突然變窮了;芬妮嫌愛蓮娜不夠有錢;上校不能娶伊萊莎,則是因為她太有錢;魏樂比欠錢,又丟了繼承權,所以甩了瑪麗安;愛德華幸好是丟了繼承權,不然也娶不得愛蓮娜。錢就是資源。奧斯汀的女主角多少都要扮演資源管理者的角色。
除了錢,推動奧斯汀小說情節的另一大動力,就是感知與事實之間的差距。《傲慢與偏見》開頭就是「此乃舉世公認的真理」,整本小說卻都在質疑:什麼是真理?什麼又是舉世公認?奧斯汀是熟讀十八世紀認識論的。《理性與感性》的書名用的並不是reason與feeling兩個字,
而是休姆與洛克皆深論過的sense與sensibility。Sense不只有理性,有時亦有感性的意義。Sensibility有時亦可做理性解,憑前後文而定。Sense的原始意義是感官,sensibility則為運用感官的能力,兩個字還有同一個形容詞sensible。因此小說講的絕不是拿一理性一感性的兩姊妹互為對照那麼簡單,而是「感官與感知力」。套一句杜拉克愛說的,就是「資訊管理」。
女主角在嫁得好丈夫之前,必須先破除隱情、謊言、誤會、偏見、曲解、錯估的重重關卡。《理性與感性》從頭到尾,有多少事要瞞,又有多少事要費疑猜,真是不勝枚舉。愛蓮娜猜妹妹一定是瞞著婚約,真正瞞著婚約的卻是愛德華。上校和愛德華都瞞著自己離開巴頓的原因。露西打擊愛蓮娜的策略,就是把該瞞的婚約選擇性地透露給她聽。判讀這個資訊對愛蓮娜來說是相當煎熬的過程,透露出去於她本身絕對有利,但因為識大體的性格使然,還是幫忙瞞下去。
愛蓮娜簡直可做管理者的典範,倒不只是她識大體。除了《諾桑覺修道院》,珍奧斯汀的女主角多少都是識大體的。愛蓮娜的特殊,是她有紀律,有管理者的使命,所處的環境也需要她一肩扛起管理的責任。《艾瑪》的女主角總是資訊判讀錯誤,不該管的也管,整本書可說是一則負面管理案例。
至於《傲慢與偏見》中的伊麗莎白,聰明顯然是超過愛蓮娜,但她並沒有管人的意願。她的談吐行事都較圖一己之快。把貝奈特太太搬來《理性與感性》,讓她做愛蓮娜的媽媽,出的醜一定會少很多。也很難想像愛蓮娜的妹妹會跟人私奔。伊麗莎白與達西的對話是高來高去,至少也是平起平坐;愛德華卻較像愛蓮娜的管理對象之一。愛蓮娜雖然愛他,念茲在茲的卻不是要嫁給他,而是要激發他的最佳表現,並幫他遮掩缺點。這不正是杜拉克最常強調的管理者之責嗎?杜拉克亦常說,「領導不該靠魅力,而要靠紀律。」愛蓮娜正是這句話的最好體現。
吉卜齡創作〈拜珍教徒〉之時是聲譽正隆的英國文壇泰斗,也是英國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人。但在今日,他最有名的,或說惡名昭彰的,恐怕是「白種人的負擔」之語了。英國的頭號帝國主義者最崇拜的不是莎士比亞或狄更斯,而是珍奧斯汀,是巧合嗎?《理性與感性》中的布蘭登上校顯然沒打過拿破崙戰爭,只在海上捍衛過大英帝國的利益。那我們可不可以因為他是個正面人物,就指控奧斯汀也是帝國主義者?
當然,奧斯汀時代的不公不義很多。像《理性與感性》中的愛德華,母親本來打算要送他進國會,但他一喪失繼承權,別說進國會了,根本連投票權都會喪失。但奧斯汀並沒點出這一點,還讓我們以為他們夫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難道她不贊成普選嗎?天知道三流學者為了升等會掰出什麼。
我們只知道,在法國欲向全歐輸出暴力革命的年代,她寫了六本小說,表面寫的是婚姻,隨時隨地的關注卻與法國大革命如出一轍,也是階級不平等。她筆下的貴族與富人常常既愚又俗,心胸亦小,賺來讀者會心一笑,但也只是一笑而已,絕不會想送這些厭物上斷頭台,因為她筆下貧賤男女的氣質可能也好不到哪裡去。教養無分貴賤,全靠自己修為。每一本奧斯汀的小說都是一本教養教科書,教讀者該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優雅,如何富而好禮。就算你無意從她學管理,不必靠她打發戰壕中的無聊,不必悼亡,好好讀她也會有這點最起碼的收穫。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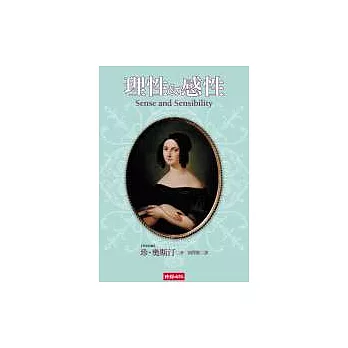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