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於洞察人心 共感他人痛苦
宋文郁首部散文作品
「我想成為一個能感受到他人痛苦的人」
《禮物》一書寫下與外公、外婆、罹患精神疾病的舅舅一起生活的真摯情感;寫出臺灣年輕學子,在考試、升學競逐路途中的困頓疑惑,在比拚的過程中失去自我、精神耗毀;寫出性別不平等經驗的憤怒與不堪......作為首部作品,初啼之聲已確立敏察人心亦共感他人痛苦的獨特風格。
「是無數次這樣的選擇決定了我是怎麼樣的人。我是一個看見死老鼠會停下腳步看著牠、記住牠的人,因為我明白牠存在,牠的痛苦真實發生,而我不願意移開視線。」
散文作為一種真誠的文類,正因為作者選擇感受別人的痛苦,理解、共感。懂得社會中許多弱勢,其中曾經有她深愛的親人。當一般人可能選擇無視或轉過頭去,她選擇正眼直視,正是真誠直面這些旁人或許不敢碰觸的痛苦,使《禮物》如此特別。
專序:
蔣亞妮
各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宇文正,作家
胡靖,聯合報副刊編輯
栗光,作家
陳珊妮,音樂人
陳珊妮,音樂人
藍佩嘉,台大社會系教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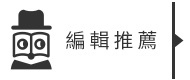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