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第三個情人
陳玉慧
我曾經說過,他是我的第三個情人。一個略嫌醜陋而且麻煩和狀況不斷的情人。但我和他的關係維持了二十多年,一直到最近才宣告分手。我應該是不會再回頭了。
他就是新聞工作。我為台灣平面媒體一共工作了二十四年。生命中有這麼長的時光是和新聞共度,而新聞工作的性質其實繁冗瑣碎,你必須永遠保持警醒好奇,必須喜歡無止盡的探索打聽。
在做新聞工作之前,我原來是在巴黎學習戲劇,從未想過在新聞事業發展。那一年夏天,我到紐約玩,結果留下來打工。而我打工的工作便是紐約記者。在那之前,我其實是個文藝少女,偶爾寫寫散文,刊登在各大媒體副刊,並沒有被退稿的經驗,不過,我從未寫過新聞。
從巴黎來到紐約,一切變得好大,車大,樓高。美金兌換法郎的匯率也很高。我決定在紐約停留,賺取學費。聽說,《中國時報》早已在紐約大舉進軍,興辦了《美洲中國時報》,有可能還需要記者。我打電話去詢問,那時的採訪主任是周天瑞先生(後來是台灣《新新聞》雜誌的創辦人),他決定應徵我。
他要我去皇后區法拉盛一棟工廠改裝的報社見面,「褚紅色的建築,」他說,多年後,我還記得後來每天在七號地鐵,三十三街,在Rawson站下車。那時報人余紀忠先生決心在美國大展鴻圖,不想讓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專美,但他還得與《立報》競爭。彼時余紀忠網羅了重要知識精英,包括如黃肇松、周天瑞、卜大中、詹宏志、胡鴻仁、金維純、杜念中、楊澤、傅朝樞等一時之選,但在奮鬥多年後,最後還是解散,那是另一個故事。但我要說的是,我去了褚紅色的建築,從此,我的人生多了一個情人。
那時我是一個奇裝異服的小文青,他看了我一眼,沒特別問我什麼,拿了一則《美聯社》的新聞稿要我翻譯成中文,我當場借坐別人的辦公桌就翻譯了。他讀了一下,問了我三個問題。一,你會照相嗎?那時已經有傻瓜相機,我也有一部,理所當然地回答他:會啊。會講廣東話嗎?我不會,但我一點沒猶豫,會啊,他看著我,問我最後一個問題:那你會沖洗照片嗎?那個年代一切尚未電子化,傻瓜相機也得使用底片,我當然不會沖洗底片。但我看著他,很鎮定地說:會啊。我被錄取了。
第二天便立刻上班跑新聞。第一件新聞事件是唐人街殺人案,採訪地點在華埠Canal street的警察局,那個警察局的警察一半都是黃面孔,我走進記者會,天啊,記者會居然以廣東話進行,我成為丈二金剛,什麼都聽不懂。我懷疑警察局的另一半白人警員都聽得懂?記者會才一結束,我立刻衝上前,找到一個說英文的警察,劈頭便用英文問了一串問題,他耐心地回答我,太好了,我把整件事件全弄清楚了,便返回皇后區的報社。
才把背包放下,周天瑞便問:新聞採訪好了?Yes, 我說。那去寫吧。好啊,我坐下來開始寫稿,這對我並不難,我從小有寫作習慣,新聞也讀過一些,我很快便寫好稿子,把稿子交給周天瑞時,心裡還很得意自己交了差,誰知他卻問我:照相了嗎?我說,當然。他說,那快去沖洗吧。
我當場愣住。我本來做好打算,一旦錄用,我可以找時間慢慢學,怎知,他要我立刻沖洗?我該告訴他實話嗎?極可能,他會立刻要我走路。我決定咬緊牙關,帶著底片膠捲和一個電話號碼,走入報社的沖洗室。在黯黑的暗房,我打電話給我剛好認識的名攝影師柯錫杰,我想,他應該可以幫忙。但他不在家!接電話的人是他的美國助理,好像叫蘇珊。在電話上,我硬著頭皮問她,「妳可以教我怎麼沖洗底片嗎?」她倒是很好心地提綱挈領講了一遍,我小聲地說話,並在漆黑的沖洗室裡把步驟記了下來。
接下來,在不到一小時之內,我以她教我的方式沖洗出照片!我走出沖洗室,把照片交給周天瑞,他看了照片一眼,只說了一句:有點模糊。我總算完成我第一個工作,那則新聞第二天刊登出來,我從此便如此跑起新聞。
那兩年的紐約記者生活對我後來的特派員工作倒是奠定了不錯的基礎。我每天都在採訪移民及新移民,但不只於華人之間。紐約之所以是紐約,正因為這裡便是移民的大熔爐。我採訪小義大利餐廳老闆、皇后區著名愛爾蘭酒吧主人、印度紗履店女主人、希臘香料和橄欖油店業主、法國網球明星、歌手、以色列作家、La Mama 劇場創辦人等等不一而足。我曾因採訪而上了雙子星大廈最高樓餐廳,我也因採訪結織了許多朋友。那時我的朋友都是紐約怪咖,有改裝舊家具的藝術家,半夜在路邊撿家具;也有波西米亞詩人爵士樂手,來我住處為我即興演奏;白天我是記者,晚間卻繼續我的戲劇生活,和同學或同好在外百老匯自編自導貝克特,生活好不熱鬧。
但這樣過了兩年,我卻想回到我另外兩個情人那裡。我向周天瑞請了一個不可能的長假,準備返回巴黎繼續我的戲劇學院,我記得周天瑞這樣告訴我:你才二十五歲,很多人一輩子也做不了這個工作,但你卻輕言放棄。我沒法回答他。
不過,很多年後,在我為《聯合報》擔任特派員的多年後,他倒是曾經詢問過我可否去出任《新新聞》的總編輯。我婉拒了,這也是後話。
總之,我的人生又回到戲劇。
我回到巴黎繼續戲劇學業,課餘,我在聯合報系的《歐洲日報》(Europe Journal)擔任法文翻譯,翻譯法文新聞,有時也做新聞採訪,因此採訪過前法國總統席哈克及前總統密特朗的夫人,甚至我頗喜歡的女歌星波金(Jane Birkin)或者大導演波蘭斯基。同時,我在那些年中,開始大量自編自導舞台劇,不但和同學在西班牙巡迴演出,還飛回台灣為國家戲劇院編導大型作品。
一直到一九九二年,我移居德國,那時是台灣經濟起飛的九○年代,《聯合報》為了拓展國際新聞的發展,正在全球各地徵求特約記者,我人在德國,從事戲劇之餘,覺得自己該有份固定的工作,於是再度寫信給報社。
那些年,「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在全球各地已有近五十名特派或特約記者,包括蘇聯甚至南非,但是在德國卻沒有人。
記得,王效蘭女士還對聘用我一事發表了意見,她在公文上批寫,「她是一名優秀的藝術家,能做特派員的工作嗎?」感謝效蘭女士只是略略懷疑,我被雇用了。而且之後為《聯合報》服務了二十年。
至今,我仍覺得,能用不同的語言採訪各地領袖精英,或者去到重要國際新聞或戰爭現場,真是有趣的人生。但如果人生從來一次,我會無怨無悔擔任特派員二十年嗎?我不是很確定,但人生反正不能重來一次。
新聞究竟教了我什麼?新聞教會我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如何把事件弄清楚,並且把弄清楚的事寫明白,讓讀者清楚。
過去,因為我的多重身分,遊走於戲劇、新聞和文學之間,常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新聞寫作與小說寫作有什麼不同?
對我而言,新聞寫作與文學寫作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兩件事。新聞寫作需要事實,除了事實還是事實,而文學創作最需要的不是事實,是想像力。寫新聞的人不能運用想像力寫新聞,那是編造。
新聞寫作首要在於寫作者必須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而且能尋覓到所有與新聞事件相關的事實佐證。而其實大多數我們聽到的,多是意見,而非事實我們看到的,也只是觀點,而不是真相。
新聞的真相就在於,事件並沒有真相,與人生一樣,有的只是向真相靠近的態度。因為所有的事件都要看從什麼觀點去看,不同的觀點呈現的便是不同的真相。
在我追跑新聞的過程中,我很少聽信任何人說任何話。我是一個根本的質疑者。那倒不是因為我覺得人總是在說謊,而更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從自己的觀點出發,有時意見非常個人或者也偏頗。如果新聞記者不參考所有與事件相關的各種不同的觀點,那麼也有可能淪於少數或個人的觀點;這是為什麼,同樣的事件,我必須查證多人,盡可能地搜集多種觀點,最後再從各種線索中歸納成我認為最客觀的說法;然後,我會盡可能地把新聞事件以更準確的文字呈現,以便讓讀者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包括當事人的語氣和神情,現場的細節或氣氛。如果我強調某個細節,那一定是因為那個細節成為這則新聞角度的參考點。
我極少用「據悉」二字,新聞本身便是據悉。該用引號時,我便援用引號,因為引述更能客觀呈現事實。引述必須巧妙,那是為什麼閱讀德文新聞時可以學習許多,因為德語文法嚴謹,寫新聞時,文法本身便可以說明是什麼時候,到底誰說了什麼話;法語新聞的分析感強,經常有獨特的分析和角度;而以中文寫作新聞有挑戰性,挑戰在於,以中文敘述事件的時態不易,因為中文文法沒有時間的概念,而敘述新聞事件發生的前後秩序和邏輯感很重要,所以中文的新聞寫作得分外注意;另外,記者不但不能使用「我」這個主詞,在行文當中都不該有太多「我」的意見;除非是分析性的特稿,新聞記者應該做的便是引述關鍵人的關鍵話。事實,事實,再事實。
新聞學其實是五個W(what where when who why),再加一個How。但是,有時,線索非常有限,時間又如此急迫,乃致於我常常被迫做的決定是,在這麼少的時間內,我認為讀者至少應該對這個新聞事件知道什麼?這個思考會決定我的採訪內容方向。
很多人也對我的特派員生活很好奇,是怎麼工作?需要常常出門嗎?其實,特派員的工作是一個讓自己處於消息靈通(Keep self well informed)的過程,那並不只是一小時或一天的事,那是時時刻刻的事。在適當的時機必須找到適當的人說出讀者應該知道的事;這關乎判斷力和平時對當地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去外地採訪,生活的地平線雖然得以擴展,得以增廣見聞,但通常也是極度的耐力考驗,有時,接到訊息便必須立刻出門,連機票都是在計程車上訂購,到了現場才能決定下榻在那裡?
也有這樣的時刻,譬如搭飛機到巴黎,轉搭快速火車(TGV)到法國西岸港口,因為法國國家造艦局(DCN)便在那裡。才走進旅館房間,電話便響了,一位男子說法語:你最好趕快走,這裡沒有人歡迎你……那是一九九四年初,我是為了追查拉法葉艦的造艦之地這通電話當然迫使我換了旅館,也找不到原先答應受訪的造艦局人士。
為什麼有這通電話?原因並不只是台灣死了一個尹清楓上校以及拉法葉佣金案,原因更是法國國家造艦局為台灣建造拉法葉艦但怕得罪中國政府,另外,售台武器違背自己的國家政策,因此極度隱暪,不打算讓任何記者看到拉法葉艦開出造艦局的船塢。
我來到了樂里昂港。早在十七世紀,耶蘇會教士由此出發到遠東中國甚至台灣傳教,而三個世紀過了,這個港口早已被歷史遺忘,港城需要工作和資金,因此法國政府決定賣船給台灣。市長倒是笑嘻嘻地接受我採訪合照,西裝筆挺,一排金鈕扣;我怎麼可以錯過這艘建造完成,取名「康定號」,要駛回台灣高雄的這一刻?
猜猜我如何見證這一幕?船塢得經過河道才能駛向大西洋,我只需要知道船塢在那裡,我只消站在船塢河道的對岸,再加上望遠鏡。我甚至看到所有站在拉法葉艦上的人的表情,以及,另一個重點,這艘船的下水典禮如此低調,甚至不能覆蓋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一幅歐盟的國旗……清晨一大早,我到今天仍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恐嚇我?
或者,我在莫斯科採訪盧布貶值,多位銀行家怕說真話,全不敢具名接受採訪,戈巴契布也接受專訪,且熱烈與我合照,但他很親切地問:可不可以不要問那麼多兩岸問題,多關心一下俄羅斯?但真的關心俄羅斯,讓我們真心談談車臣問題吧,戈巴契夫卻也沒多說什麼。
我也曾訪問愛爾蘭總統羅賓遜女士(Mary Robinson),她可能是全世界最鐵齒的政治人物,我跟她有一番攻防戰。她確實比較能掌握國際政治語言,並且有些手腕,在總統任期結束後,到今天都在聯合國任職高階職位並有許多表現。我們談了許多北愛問題,她讓我見識到另一種政治人物的風範。
也有這種荒謬的時刻: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時,貝爾格勒電訊都不通了,我終於打通電話,找到反對黨黨主席左杭丁吉克(Zoran Đinđić),後來米洛塞維奇被審後,他出任總理但卻被暗殺。那通電話時值轟炸最慘烈之日,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電話等待中的音樂是帕海貝爾的卡農(Canon D),而在與左杭丁吉克談話之中,我居然聽到轟炸聲。
又或者去了布吉納法索,全球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是我們的邦交國。訪問總統龔布雷,他應該是以政變取得權力,完全不避諱談起利益政策,只要對布吉納法索有利的便是國家政策,但是布國人也肯定台灣農耕隊種下去的種籽,傳授給他們的農業技術;總統很和氣地介紹他的視聽室,彷彿是一個微型電影院,足球迷的他都在這裡看足球,這應該是台灣納稅人埋的單,而他陪我走過,到隔壁的貴賓室接受採訪。在一組大沙發群中,我們以法文交談,龔布雷頭頭是道,條理清楚。我以為我在極權國家,但隨後,我又驚訝地發現,布吉納法索也有新聞記者敢批評總統的作為。
那些年,訪問了波羅的海三小國三位總統,切身感受他們在蘇聯解體後,多麼努力地尋找國家的自我身分認同。爾後,我也在巴爾幹半島往返,訪問多國總統或總理,保括保加利亞總理高斯多夫,他直言台灣用錢買邦交沒有用;也搭乘聯合國提供的記者專機往返提亞納和史高比耶,身邊坐了一位織打毛線的男記者,隔沒幾天,在旅館看CNN,那架專機已經墜毀。
伊拉克戰爭期間,去土耳其採訪,坐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旁的咖啡館訪問異議人士。他居然也住過德國,和我一樣,曾經愛聽里奧納多‧柯恩的歌曲,他流亡時期女友變了心,但他成為作家,因為他,還有帕慕克,我從此愛上伊斯坦堡。
還有,二〇一一年的茉莉花革命,我到了埃及,站在塞滿群眾的開羅解放廣場,氣氛是沸騰的,群眾是期待的,欣喜溢於言表。漫步廣場,想到高寧在推特上的留言:「埃及,我差不多想念你三十年了!」心裡真是激動。夜晚走回旅館,經過許多坦克車及軍隊,一位軍人當街公然對我表示,他需要女伴,非要一起與我返回旅館不可,我望向他身旁的軍中同僚,沒有人覺得他的要求奇怪。
在希臘,親眼見識這個古老文明國家現代化的困難。國家比英國還小,但公務員的數目是英國的六倍,且薪水也差不多一樣,希臘政府一直借貸過日,使用的是國際市場借來的錢。希臘買空賣空已十數年,三千億歐元的債務,還不構成整個歐洲最大的威脅?訪問國家財政局和觀光局的首長,我發出這樣的疑問,兩人都非常驚訝,其中一位還非常憤怒。我到雅典衛城下採訪智庫學者,學者的意思是希臘經濟只占歐盟的百分之三,根本吃不垮歐洲,他要向政府建言醫療經濟和度假經濟,希臘是全世界最多小島的國家,不然賣掉幾個?我遙望建於六世紀的雅典衛城(Acropolis )上的雕像,似乎也全無言地垂看雅典。
這麼多的國際大事都經歷過了。二十分鐘內必須寫完一則頭版頭條新聞的事情也都做過了,好幾次甚至因為過於匆忙而按錯鍵,或不小心刪除,而必須用更短的時間重寫一篇。
只有台灣這樣的國家,才會有我這樣的特派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台灣這樣的命運,也不會有一個國家的特派員必須追跑那些新聞,因為台灣的歷史和政治以及國際處境獨特少有,幾乎不是台灣人不可能明瞭……而我那些年和那些西方通訊社或報社的記者群坐在一起,我提問的問題永遠與他們不一樣;我怎麼理解世界?世界又如何明瞭台灣?如果,所有的新聞事件都沒有真相,只有靠近真相,那麼,我或者我們到底能多靠近真相?
記者,其實是問者。好新聞常常來自好問題,向當事人提出好問題,是記者最應該做的事之一。第二,是聽懂回答者真正的意思。
離開第三個情人,我不會後悔。但讓我驚愕的是,一年多前,我移居台北長住,卻發現此地並沒有新聞,更別提國際新聞,電視甚至從來不報導國際間發生什麼事。走遍世界,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現象,這是什麼國度?讀者不需要國際新聞?不需要新聞?八卦充斥,名嘴當道,但從來沒有人在乎真正的新聞,什麼是真正的新聞?
我任職特派員這二十年,正值台灣從一再要走出去的九○年代,一路到因反服貿條例而走上街頭的今天,台灣仍未走出去,沒有,台灣一點都沒有走出去,反而比以前更封閉更鎖國了。從前報社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個據點,現在只能負擔兩、三個,我幾乎是末代特派員。台灣最輝煌的國際新聞時代已經殞落了,平面媒體甚至開始要消失了。
在這個資訊氾濫的網路時代,人人都在寫新聞,但正因為對內容的饑渴,我們比任何時代更需要新聞,我們需要更有質地,更有趣味,更有遠景的好新聞。當然,正因為我有這麼多年的新聞寫作經驗,我不會隨便使用「我們」這兩個字,因為我也會問:我們是誰,誰代表我們?我不認同許多人為「我們」代言。我只能說,我自己期待更多更好的新聞,我也期待一個新的新聞時代。
因為,新的新聞時代已經降臨。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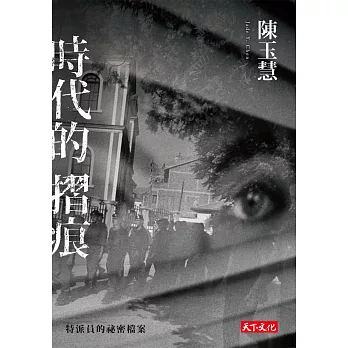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