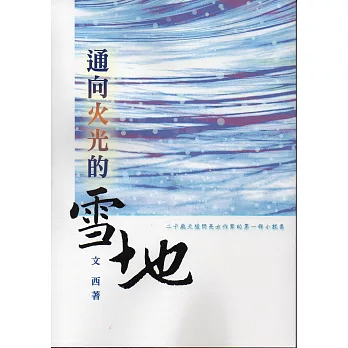我不認識文西,更沒有見過她,知道文西這個人的時間也不長,才兩月不到。今年七月十九日,我陪同《青年文學》原執行主編、作家和出版人唐朝暉先生去八百年土司故都老司城遺址,才第一次從他的口中聽到文西這個名字。記得當時我們站在正在舉辦一個什麼活動的草坪裏,談到湘西作者時,他說有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子,叫做文西,詩寫的非常不錯,問我認識嗎?我問他這人是湘西哪里的,她答保靖的。然後,因為別人插話,因為亂哄哄的環境,我們就沒再繼續這個話題了。
但我記住了文西這個名字,記住了她是保靖的。保靖與我所在的永順,是湘西北兩個相鄰的縣,相距非常之近,我對我們這個偏遠的地方能出一個在外面有些反響的文學後輩,心裏自然是十分欣悅的。我在保靖有幾個非常要好的搞寫作的哥們,但他們都沒有跟我提起過這個叫做文西的女孩。這倒讓我對文西有點神秘的感覺。從老司城回來之後,我就在網路上搜索文西的作品,陸陸續續地讀了她的一些詩作。其中有幾首我是蠻喜歡的,像《我反復跟蹤一個人》、《走近墓園》,寫得厚重和詭譎。於詩我是一個外行,只能憑感覺和喜好判斷。我喜歡文西的詩,但那時我不知道文西到底有多大,寫作多少年了,更不知道她的身世、成長環境以及職業等等,因此不能對她的詩歌作品做更深的探尋,讀過也就過了。
有一天,文西像從天而降,或從地下冒出來一般,突然找到我,要我給她的《通向火光的雪地》小說集寫序,著實嚇了我一跳啊!不是說她找到我的方式嚇著了我,而是這女孩不僅詩寫的不錯,小說集也要出版了,這是其一;其二,這時我才知道她是一個在校大二的學生,僅僅才二十歲,這麼年輕,真嚇人!
從文西的交談中,我得知她出生於保靖鄉下,很小的年紀就離開親人進縣城裏讀書,是在遠離親人的孤獨和寂寞的歲月中漸漸長大的。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是放養式長大的。所有的少女都有一顆敏感的心靈,文西肯定比別人更要敏銳一些,否則她不會從十來歲就開始寫作,立志要成為一名作家。我在閱讀她的小說時,對抗孤獨和親情缺失幾乎是她大多數小說的主題。《通向火光的雪地》、《秋雨》、《地上的虹》、《喬利的左眼》,就是她開掘這類主題的試驗。在《通向火光的雪地》中,龍興和吳盛這對兄妹因為父親早逝,母親改嫁而分離,作為哥哥的龍興一直千辛苦萬苦地努力想得到妹妹吳盛的理解和接納,他一次一次地逃跑,一次一次地想去長沙看望妹妹,直至跳火車摔斷了雙腿,但在妹妹這裏,身份的恥辱永遠是她內心的一道陰影,拒絕哥哥進入自己的生活也是她本能的反抗,最終親情只是雪地上一閃而逝的火光,終身孤獨註定是龍興的宿命,他無法突圍。文西小小年紀,就把人間世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喬利的左眼》卻是關於失敗的孤獨和反叛的親情。少年喬利因為小時不小心磕到了左眼,因父親喬木拖延就醫而瞎掉。從此喬利與父親形同水火,左眼提前了他的叛逆期。與張―的性愛的失敗更扭曲了他的心靈,最後他竟然出賣妹妹去換來一只籃球。文西在這個小說裏直指人性深處的幽暗和扭曲,畸型成長毀掉了喬利的成長,也必然要毀掉喬利的整個人生,卻使得這個作品更加震撼人心,發人深省。
毫無疑問,文西的寫作是一種真正的寫作。我不敢肯定文西是個天才,通讀她的小說後,我至少能肯定她有寫作的天分。她肯定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比如她的小說不注重結構,比如她的題材面太窄,但這些都不是問題,我相信隨著她的閱讀和閱歷的積累,她會寫得越來越好。畢竟,一個人的寫作也會漸漸成長的。文西現在才剛剛起步,但她已經做得很棒了。
我在很多場合說過,我們湘西是個偏遠的地方,我們遠離文化中心,湘西的作家們要出來,必須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艱辛和努力。要有一股子湘西人的「哈」氣。我希望文西不要浪費她的才華,靜下心來學習和創作,拿出我們湘西人的「哈」氣來,寫出更多更好的詩歌和小說。她很年輕,今後的路還很長很長,她一定能得到繆斯的垂青。我們期待著。
是為序。
崔伯陵
甲午年七月二十日凌晨於寄溪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