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關於《平家物語》(節錄)
《平家物語》是一部「軍記物語」,即以戰爭為主要題材的歷史小說。其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地位,僅次於《源氏物語》,並列為日本二大物語經典之作。《源氏物語》成書於平安時代中期,約當西元十一世紀初頭,一般公認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寫實小說。現在已有林文月教授、豐子愷先生等人的不同漢譯本,對世界各地的漢語讀者並不陌生。至於《平家物語》,雖有周作人先生〔未完,申非補譯〕、王新禧等人的譯本;網路上也偶有零星的翻譯或介紹,但與《源氏物語》相比,在漢語圈內知之者並不太多。
《平家物語》的歷史背景是平安時代末期,即十二世紀後半,大約與中國南宋孝宗(一一六二-一一八九)與光宗(一一八九-一一九四)在位時重疊。但其成書則在數十年之後,才出現簡單的雛形。據常被引用的吉田兼好《徒然草》(一三三一前後)第二二六段載有一種說法:後鳥羽天皇讓位而為上皇時(一一九八-一二二一),比叡山天臺座主慈鎮和尚(原名慈圓,一一五五-一二二五)招致有一藝之長的人於門下。其中有退隱修佛的信濃國(一說下野國)前司藤原行長,頗能通曉典章制度與掌故。
此行長入道作平家之物語,授之與盲者生佛,使講唱之。其敘山門(比叡山)之事極為詳盡。於九郎判官(源義經)之事,似亦耳熟能詳而據實成說。至於蒲冠者(源範賴)之事則所知有限,故多有遺漏而未克記錄者。有關武士與弓馬之事,因生佛為東國之人,故可問之於武士而使書之。彼生佛天賦之聲調,仍為今日琵琶法師學習之典範也。
如果此說可信,則在十二、三世紀之交,平家故事經由琵琶法師的講唱,已開始在日本各地傳播開來,而且可以想像相當受到歡迎。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家物語》的形成過程中,無論在詞章的撰寫或講唱的腔法上,從一開始就與佛教徒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有人認為《平家物語》是「鎮魂」的文學。因為自保元(一一五六)、平治(一一五九)之亂以來,尤其在源平兩家逐鹿天下期間,枉死者不可勝數;又因為陸續發生了饑饉、地震等天災,世人總以為怨靈作祟所致,於是公家與民間時有安魂的儀式或法會。佛教界大慈大悲,以為責無旁貸,捨我其誰,便由盲人琵琶法師結合講史與聲明唱導的方式,彈唱源平兩家盛衰的故事,順便宣導「欣求淨土」的往生思想。一則濟度亡魂,祈其往生淨土;一則寓教於樂,以娛聽眾為生。所謂「平家琵琶」或「平曲」於焉產生。
然而,有如《三國志演義》或《水滸傳》的成書過程,其後平曲也經過了漫長的口授心傳的階段。不一定全有文字記錄。只不過在此期間,不斷吸收了俗間的傳說,又參考了當時陸續出現的相關日記、筆記等公私文字記錄,加以講唱者有意無意的改動或修飾,內容肯定越改越豐富,越講越引人。以後經過了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到了室町時代初期,有「沙門覺一」者,在《平家物語》後題跋云:
維時應安四年辛亥三月十五日,《平家物語》一部十二卷(附〈灌頂〉)。當流之師說、傳受之秘訣,一字不闕,令以口筆書寫之,讓與定一檢校訖。抑且愚質餘命既過七十,浮生後事難期。而大去之後,諸弟子中若有廢忘之輩,雖僅一句,其將引起爭論無疑。是以令書而留之,以備今後查證。(原文為擬漢文體,即和化漢文,略加改動)。
應安四年(一三七一)距上舉「行長入道作平家之物語」,已過了一百五十多年。覺一在平曲的發展史上,不但帶頭整理了《平家物語》的詞章文本,成為後來通行最廣的所謂「覺一本」原形,而且組織散漫的盲人琵琶法師為一同業團體,依各人的師承年資,分為檢校、別當、勾當、座頭四級,奠定了平曲以後長達兩百年盛況的基礎。有名的五山禪僧中嚴圓月(一三〇〇-一三七五)有漢詩〈與覺一〉云:「殷鑑昏昏不拂塵,衰周列國併成秦。白旗赤幟相攘敓,一曲琵琶愁殺人。」(《東海一漚集》)可知覺一等人彈唱的平曲在五山禪僧間也頗受歡迎。(按:白旗赤幟分別代表源氏與平家)。
其實在生佛之後,不久平曲就分為八坂流與一方流兩大派系。覺一屬於一方流,勢力較大,流傳最久。不過到了十五世紀中葉,覺一的徒孫輩也開始分道揚鑣,各立派系,互相競爭,自然導致了彈唱文本的差異。況且還有八坂流等平曲流派。此外更有專供閱讀用的許多所謂「讀本」系本子。因此,《平家物語》所傳異本之多,在日本的古典文學中前所未見。而學者之間,對於參與編寫的歷代作者〔群〕像,以及不同傳本在各階段演變的具體情形,雖然各有說法,似乎也言之成理,但多半止於猜測,迄無定論。不像《三國志演義》之有羅貫中,《水滸傳》之有施耐庵,蓋有文獻可徵也。
現在通行的《平家物語》系屬覺一本,共十二卷,附加〈灌頂卷〉,敘述平安時代末期,平家在與源氏逐鹿過程中由盛而衰而亡的故事。全書大致可以分成前後兩大半:第一卷到第六卷為前半,敘述平家興盛至極而漸露衰像;第七卷到第十二卷為後半,敘述平家屢遭慘敗而終至滅亡。敘述方法兼用編年體與紀傳體。凡是有關重要事件的呈現,則使用編年之法,即依年月日之先後,往往跨越章節以敘其來龍去脈。對重要角色或特殊人物的描寫,則採用紀傳之體,多以單一章節結束,而且時時利用倒敘之筆。《平家物語》所用文體合稱「和漢混淆體」,即兼採當代和文、和化漢文、漢文訓讀體、候文等,因時因地因人之宜而用之。各體競秀,文趣盎然。
物語所涉及的歷史時間,雖然始自長承元年(一三三二)平忠盛敕許初登「殿上之間」,終於建久十年(一一九九)源賴朝死去,長達約七十年之久,然而其敘述重心則從治承元年(一一七七)的「鹿谷密謀」(卷第一〈鹿谷〉)開始,經過治承四年源氏舉兵後之一連串戰役,到元曆二年(一一八五)平家一門亡於壇浦會戰為止,前後不到十年,卻佔了全書約九成的篇幅。因為源平兩家爭霸的幾次大小會戰,都發生在治承年間(一一七七-一一八四),所以早期又有《治承物語》之稱。
《平家物語》第一卷開宗明義〈祇園精舍〉章,就提出「諸行無常、盛者必衰」之理;並舉「六波羅入道前太政大臣平朝臣清盛公」為「驕奢者不得永恆,跋扈者終遭夷滅」的例證之一。平清盛(一一一八-一一八一)便是《平家物語》的主要人物。至少在前半部,卷第六〈入道死去〉章之前,專權跋扈,為所欲為;一門榮華無與倫比。然而泰極否生。自從平清盛嫡子重盛贖罪而死之後,死神就緊纏著平家不放。於是,有罹熱病而悶死者、有在會戰中陣亡者、有投水自盡者、有被捕而後梟首者。死法千變萬狀。到了平維盛的公子六代被斬之後,「平家的子孫便永遠斷絕了。」(卷第十二〈六代被斬〉)。使用一連串死亡的意象來誇飾平家的絕滅,也是《平家物語》書寫策略之一。
人生無常。有生必有死,誰能無死?是以死亦人生無常之常。但是對生而為人者,無論好人壞人,不管強者弱者,死總是被認為最大的不幸。誰能甘心一死了之?於是佛教唱導者出現了。尤其是淨土宗的說法,即使生前惡貫滿盈、苦海無邊,只須在死前之剎那具無上虔誠心,念佛一遍或十遍,就有阿彌陀佛與眾菩薩前來迎接,往生極樂淨土,而獲得贖罪而擺脫無常之悲。由此觀之,在全書最後的〈灌頂卷〉中,那位經過大風大浪,嘗盡人生一切哀樂榮辱的建禮門院,在寂寞的寂光院中,悟出六道輪迴之旨而向後白河法皇縷縷傾吐其一生之原委,終於在紫雲飄緲中,安安靜靜地被迎往極樂世界。此時,寂光院的鐘聲似乎遙遙呼應著祇園精舍的鐘聲:「諸行無常之響」。
無常是《平家物語》的中心主題。然而一部偉大的作品,經過多數作家的參與與長期的演變,在不偏離中心主題的原則之下,有心或無意之間,難免會衍生或附加新的旨趣、面貌或視野。最常被提到的是:時代的反映。平安時代是貴族治國的時代。但是到了末葉,約當十二世紀,地方武士階級崛起。貴族權勢旁落之後,先是源平兩家在朝廷分庭抗禮,平起平坐。但不旋踵間平家架空皇室,排除異己,獨攬國政;胡作非為,大失人心。最後源氏反敗為勝,取而代之,建立了幕府體制,在日本歷史上開始了長達六百多年的武家政治。《平家物語》所反映的正是此一大變革的大時代。在如此重大的政治與社會變革過程中,平清盛的所作所為儘管受人詬病,但其歷史意義並不下於建立幕府的源賴朝。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所謂戰爭的意涵。覺一本《平家物語》所寫的戰爭,從個人的對打、氏族間的爭鬥、地方的暴動,以至全國性的內亂,不一而足。但與其他前此或同代的戰爭書寫相較,卻有明顯的不同之處。仔細觀察書中的戰爭場面,自第四卷以後,逐卷數而增多。不過每臨大小戰役固然講究戰術的運用,至於戰爭場面的描述卻能簡則簡,而偏重不同人物的臨場表現與反應,藉以塑造人物的個別形象。因此,是勇者或懦夫,是君子或小人,是遠謀或短視,往往於此表露無遺。還有一個有趣的特色。戰鬥廝殺不免流血,但是覺一本《平家物語》的戰場卻見不到任何血跡。戰爭的過程有時被公式化或抽象化成:互射鳴鏑,吶喊開戰,經過廝殺後,勝方摘取敗者首級,然後遊街示眾,梟首獄門。彷彿例行公事。不霑一滴血。將血肉橫飛的場面交給讀者或聽者自己去想像。
或有人認為《平家物語》是剛、硬的文學,與《源氏物語》的柔、軟恰成對照,強調二者迥然不同。其實並不盡然。的確,兩個物語的主要舞台與人物:一是活躍於京都宮廷的封閉空間、不少為情所困的貴冑男女;一是奔馳於東西各國的廣大地區、無數赴湯蹈火的武士與僧兵。然而,站在日本文學發展史的觀點,兩大物語前後相隔二百多年,文學與時推移,其間自然不可能沒有鴻溝。只是一有鴻溝就有架橋者,讓傳統繼續走下去,所以即使在此剛硬的軍記物語中,也留下了不少平安時代宮廷式的精神風貌與風流韻事,而且明顯有跡可尋。市古貞次教授指出:
《平家物語》是平家的輓歌,是催人哀傷的死亡的文學。…是描寫無數人們含著眼淚而行動的「哀」的物語。平安時代的文學精神是「哀」。而一般認為《源氏物語》的基調便是「物之哀」,因此本書也可視為繼承了「哀」之傳統的作品。固然「哀」的內涵隨時在變,但也不能因而就忽視平安時代以來物語一脈相承的流風遺韻。(《平家物語‧解說》)
所謂「物之哀(物のあはれ)」是日本傳統的美學概念。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人情的本質。人類外則感於四季八節之推移,而內則困於七情六欲之搖蕩,自然而然產生一種人生的興味。此種興味本來應該是中立的,代表著和諧、平衡、優美、哀而不傷的境界,不過人「情主於傷痛」(劉勰《文心雕龍‧哀悼》),因而「物之哀」的概念,一開始就先天地內含著偏重於「哀」的傾向。在《平家物語》之中,死亡的故事連篇累牘,在感歎諸事無常之餘,在流不盡的閃閃淚光下,「哀」儼然變成了全書的主調了。
《平家物語》雖是一群男人所創的男性的軍記物語,但在書中卻置入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女人軼事,處處還看得到平安女流文學的遺跡。例如祇王、葵姬、小督、小宰相、千手姬、橫笛、建禮門院等,都是各有專章的人物。或善和歌,或操管絃。形象特出,各具個性,為全書帶來了點點鮮豔的異彩。然而正如某評家所言,《平家物語》在描寫男女愛情時,往往陷於單純化或類型化,對於苦惱背後的無奈與空虛,無暇也未能深入體會觀照,自然難與《源氏物語》的纖細緻密相比(高木市之助等《平家物語‧解說》)。或許可以說,《平家物語》的重點不在談「情」。就承襲平安王朝貴族文化而言,平家武士其實也不甘落後。文化只有演進、變容,不可能截然而斷。平家既然擁有天下,豈能永遠當鄉巴佬?於是也仰慕貴族的文化生活,而且在一門滅亡之前早已出現了不少文采風流的武士。和歌、琵琶、笛子等皆有名手,可見其在日本文化史上承前啟後的角色。
鄭清茂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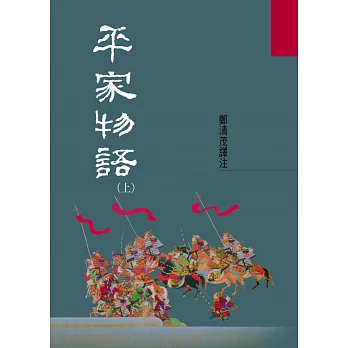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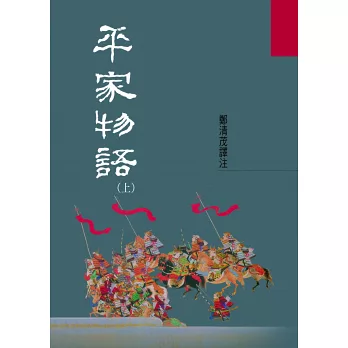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