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文學沒有時差,不論跨界
出於我對國族認同的興趣,在研究亞洲歷史過程中,時常在心裡浮現一種假想題,例如,二戰結束之前,台灣、東北(滿州國)與上海(租界)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連動關係;在黨國教育下被切為「漢奸」者,在當時的環境下,究竟是怎麼樣的人?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勾勒中,那些日語文化者(日本人與其殖民地子民)如何在期間移動,又有哪些認同?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讓人探討的時代,「國界」此時毫無意義,兩岸之間或因驅逐殖民者的民族主義而動—不論抗日或對抗歐美—或因豐富強化文化成果而行,怎麼想都是個很有張力、很有故事的舞台。
我那本關於亞洲國界與國族認同的書出版前,隨口向編輯聊起這個興趣方向,竟得到一個具體的回答:「劉吶鷗啊。」見我疑惑,他立刻補充:「是日治時期遊走兩岸的電影人。」
聽起來很有趣,而且電影文化比政治革命感覺起來更能衝破國界,我拿出手機搜尋,查了一下此人的背景後,把名字記了下來—也買了他相關出版品。因手上還有題目在做,劉吶鷗與他的一切在這之後被我擱置不理,除了他出身台南望族、被暗殺在上海市街外,我這金魚腦裡只留有他與李香蘭的八卦,再無其他。
再次聽到這個名字,是因為本書作者徐禎苓。劉吶鷗是徐禎苓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她閱讀日記、書寫心得,到中國當交換生,甚至為踏查「新感覺派」的蹤跡而旅行,都只為了讓這個活在一九二○年代的文化人與他的伙伴們的形貌、身世更為具體;而我們這些(滑手機看貼文的)旁觀者,從她的分享中,竟也跨越時空與這個陌生文人有了數位連結。當我知道禎苓甚至飛到日本,拜訪劉吶鷗小女兒時,也忍不住哇地叫了出來。而這追尋的過程,更完整、更細緻地被書寫下來,收攏在這本《時間不感症者》裡。
整本書的序章,自是從劉吶鷗開始,也從他與作者的故鄉台灣開始。徐禎苓敏銳地將這個主角置放在歷史的視野上:
劉吶鷗就像當時的文人一樣,搭船往來於中國、台灣和東京,買書、看電影、找朋友、上學。嚴格說起來,這生活沒什麼特別,可恰恰就落在一九二七年。人們創造了歷史,但歷史也挑人,劉吶鷗無以迴避地在旅途上見證了東亞的轉變。
而為了了解劉吶鷗與上海,準備赴陸當交換生的徐禎苓,恰恰好,在劉吶鷗前往上海(一九二六)的八十八年後,遇上一個與中國有關的社會運動,一個歷史需要轉動的當口。「中國,對於台灣人,一直以來就是個複雜又晦澀的符碼。」聽父母對她到現場又是緊張,在行政院前鎮壓行動後又是痛罵中國,徐禎苓忍不住感慨:
我的時差旅行無可避免疊上幾重參照,劉吶鷗的世代、父親母親的世代和解嚴世代,那將不會只是上海地景的更迭,也連帶輻輳幾世代的台灣人對於中國的想像,又或者台灣人在中國的境遇。
「時差旅行」正是這本書的關鍵詞,徐禎苓以一個台灣解嚴世代的目光,踏上一個因戒嚴與內戰而斷裂且片段想像的土地,追尋的是民國初年兩岸文化人的足跡,但面對的是已然強勢且具有絕對意識形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子民與環境,她必須在心裡與歷史對話,也不得不在現實中面對一切挑戰。我無法確知劉吶鷗在當時的上海是否自在,卻曉得我們這些台灣年輕世代在中國,都無法安然。
因此,劉吶鷗雖是這本書的緣由與線軸,卻非一切。徐禎苓在中國的「走讀」與見聞,更是生動有趣。我曾跑過兩岸藝文,多次赴陸旅行,徐禎苓筆下的許多地方我也都走過,但說實在,因為缺乏如她那般敏銳的眼睛與細緻感受,所以沒有什麼深刻地記憶,也不若他筆下有情。因此,讀這本《時間不感症者》的過程中,我彷彿也再次旅行了一趟,並在心裡與徐禎苓,以及她所對話的那些文化人,對話了一次。
最後一提,之所以推薦這本書,不單只是因為上述因緣,我和徐禎苓正是在她結束交換後,於在中國福州的一個藝文活動中認識的。這座城市也曾有許多民國文人的深刻烙印(包含她在書中提及的林徽音),與台灣/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也很是密切,或許因為如此,這裡的文化人對我們、對台灣,也較他處更為開放包容,也更強調台灣自由民主的珍貴。無論如何,所謂的中國,不論那個時代,哪段歷史都不會是一個絕對值,如果可以將自己的經歷作為出發,將這本書視為開始,或許我們都可以像劉吶鷗那樣有個開放、浪漫、自由的人生旅行。沒有國界的。
阿潑
本文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推薦序
她漂海去尋光—並致時間不感症者
讀《時間不感症者》的前兩天,我去看了鍾孟宏導演的電影《陽光普照》,電影結尾時,豔陽的光斑在樹葉縫隙之間滑動、最終垂落在女人臉頰上的畫面,強而有力地攫住了我的思緒,因此,當我讀著這本既像是旅遊隨筆又像是研究採集的散文集時,視線不自覺地自動追獵、捕捉著關於陽光的描寫段落,從而發覺:這部散文集裡竟然充溢著光的軌跡,例如寫落地上海之後、來到了某段期間將寓居於此的房間,時值肅秋,與我正寫著字的今日體式相似,日光被時間之刃漸次地截短,在光照透骨的異地公寓,蝸居頂樓的女孩凝視著眼前牆面上移動的光之軌跡,由此摸索著時間的流向:
從初秋到深秋、初冬到隆冬,強烈感受氣溫升降之外,我也慢慢抓到時序。譬如在九月約莫要七點才天黑,至十一月已遞前一小時;又譬如日頭滑動的軌跡,溫熱灼眼的日光吋吋移動,從室友的床鋪緩緩越過我的背脊,踱步到我的書桌,等光照完全棲在桌邊白牆,那刻約莫四點多。室友通常沒那麼早回來,我停下手邊動作,走到陽台小憩。……是百無聊賴的人也好,是住在頂樓的人也好,人們對於陽光的悸動,並不一定是很久沒看見陽光,有時恰恰相反,僅僅是因為發現陽光存在,那抹發現讓人突然很靠近自然。(〈頂樓的人〉)
這樣的描寫讓我不自覺地想起張愛玲,同樣是寫上海的公寓,同樣是公寓的頂樓,張愛玲將這各人各據偌大上海城中之一角一格的公寓生活寫得迷人無比: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厭倦了大都會的人們往往記掛著和平幽靜的鄉村,心心念念盼望著有一天能夠告老歸田,養蜂種菜,享點清福。殊不知在鄉下多買半斤臘肉便要引起許多閒言閒語,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層你就是站在窗前換衣服也不妨事!(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
張愛玲的公寓是一種面對生命蒼涼時仍要擺弄的一個優雅的手勢,亂世中更近乎某種個人主義式的抵抗;而時間不感症者的落地姿態,則是茫茫海上的自我安頓與豢養,因為前方有更巨大更耀眼的身影等待著自己舉步追隨,那人名喚:劉吶鷗。
我對劉吶鷗並不熟稔,但我明白上海這座城市對於心懷黃金時代的人有著多麼魅惑的引力。一如徐禎苓的上海只是劉吶鷗的上海,我的上海也只容著魯迅、蕭紅、郁達夫。我們分別以自己追隨的文學偶像指認這枚海上明鑽,在古老的城廓間尋找時光疾疾流去後遺落的各色卵石,石上刻寫了我們心愛的名字與臉容、小說與詩。但沉浸於舊時光中的我們,對於眼前依舊無聲流失的時間卻毫無察覺而周身麻木的—這樣的懷舊是否太不合時宜?就像新感覺派在離亂之世忠始終難尋覓一把合身的天鵝絨的座椅?
對此,這位年輕的時間不感症患者,尋求太陽移步的光痕代為解套:
我感受到天以各種方式:冷熱、光照、日夜、草木變化等,提醒人們年歲與時日。我們置於裡頭,若可能的話,感時應物,稟受種種非人為的變化,甚至與萬物共感;若可能的話,會點點感受人在世界的位置,在時間的光譜裡,並沒有想像來得厥偉。人就只是人,面對流歲、面對自然的一粒塵埃、一顆水沫。(〈頂樓的人〉)
面對戰爭離亂,家國淪亡,寫字的人在上海,能抓住的興許或許僅僅是掌心的一枝筆,桌前的一盞燈,鍋裡的一捧湯,營營亂叫的熱水器,肩頭上從天井灑落的午後秋陽的光斑……對應於己身將滅的無常,陽光普贈的是當下即證的生存體感。我們或因而知曉:光即時光。欲感知時間之奧祕,則需一路尋光,漂海過洋,遍訪蒐羅眼角留餘的逝者殘影,辯護般地指認自己之所以此時此刻流連同一街巷(甚至之所以生於此世)的依據,近乎某種靈視。
而所謂的「時間不感症」,或許僅僅是太容易對時間犯過敏罷了。
崔舜華
本文作者為詩人
推薦序
印證、考掘與邊界—徐禎苓的中國行旅
從美麗秋海棠到瘋狂老母雞,從華夏、中華、淪陷地、祖國、家鄉等定位與形象,到特意被強調、帶有對立感與區分感的「中國」──台灣與龐大對岸關係如此曖昧,一系列仍屬進行式的動態變化,受層層疊疊的權力、政治、文化場域所牽制、形塑。在文學中,中國行旅作為台灣散文的重要題材之一,也可以讀出那條歪斜痕跡。
早年的懷鄉散文,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的探親散文,乃至於記者的踏查報導、長期行旅者或移居者的深度探索,還有四九後的大陸移民與當代民間學者種種文史掌故寫作帶出的舊時代煙雲,總合成複數的「中國」。而彷彿散發出時間的麝香一般的「上海」,即是最大熱點。「上海」饒具諸般面向,可是,在文化想像中,存著一個塔尖上的名字。鍾文音《奢華的時光:我的上海華麗與蒼涼紀行》(二○○二)以「華麗」、「蒼涼」來定位「上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以張愛玲為潛文本;章緣《當張愛玲的鄰居—台灣留美客的京滬生活記》(二○○八),點名「台」、「美」交纏的基礎以及身在京滬作「客」的發言位置,雖然「京」「滬」都生活過,但是,對於台灣讀者來說,有哪個民國文學家的名字能比「張愛玲」更具威力?
徐禎苓的第二部散文《時間不感症者》,也可以放到上述脈絡中看。本書主攻中國行旅題材,作者受惠於兩岸學術交流體制,藉交換生身分,以上海(復旦大學)為根據地,輻射至華北、雲南等處。停留上海的時間比章緣短得多,可能比鍾文音來得長或集中一些。令人好奇的恐怕還是:「台灣│上海」書寫還有可能在前行著作磊壓、二十年來台灣人如此輕易就能往來台滬的熟悉感下,再寫出更新鮮、深刻的上海紀行嗎?
首先,徐禎苓的出發點,很罕見的,不是張愛玲。她的學術研究主要關懷為新感覺派作家,因此,出發點是跑到上海文壇去發展的台南人劉吶鷗。憑著劉吶鷗的日記、小說,以及與劉吶鷗同時代的老上海旅遊指南,就像朱天心《古都》中的敘事者拿著日治時代地圖漫遊當代台北,禎苓也拿著一九三○年代指南漫遊當代上海。任何一座有歷史、有故事可說的城市,即使普通遊人行走其間,很難不感受到今昔交映的魅力,更何況下過功夫、攜帶著文學幽靈一起上路?然而,那也不代表這僅僅是趟仿/訪舊之旅。旅者/寫作者/研究者/台灣人/女性/學生,挾帶多重身分,以考掘者之眼,印證所讀,在新廢墟中辨認過去的廢墟,在易代更新後的世界裡感應深埋的霞光,同時,對於商品化樣板化了的「文化上海」,欲拒還迎,天真信賴而後恍然懊惱……瑣碎卻真實。
任何再尋常的台灣與中國人的交會,都難以擺脫文化或族群身分意識的籠罩。自我表述(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為什麼來這裡?)、生活態度的加意選擇(特別守規矩、有禮貌,無論如何堅持排隊)、和新舊朋友談及兩岸話題時到哪裡就得喊停(對方提起六四或網路言論檢查時,真正的用意為何?),都可能涉及小小的政治糾葛,而更加證明身心邊界與現實邊界的存在。一個愛(老)上海、追尋(老)上海,而又具備基本台灣意識的台灣人,來到了當代上海,到底希望泯除界線,或隱隱維持界線?界線其實是做(doing)出來的,我們往往神入,對歷史掌故如數家珍,而又時時區分彼與此,不願被視為一體。那裡頭是對國族的執迷還是對現代性的執迷?
《時間不感症者》核心雖是上海,不過,交換生時光裡,禎苓還有幾次外遊。比如來到太原。寫司機話中有話,分明是占便宜,聽起來倒滿像人生哲學,點到為止,作者也不必分析,讀者都能咀嚼;之後,太原朋友談到新疆莎車暴動,贊同政府鎮壓,又談及六四,只說了故事,沒表達立場,卻壓低聲量提到某某老師幾次被「請喝咖啡」,點到為止,讀者同樣都能咀嚼。在這一類篇章裡,類似的處理手法,都可以看見作者的思量與巧慧。
書名來自劉吶鷗小說,對於時間的「不感」成了「症」,表示已積重成病;事實上,所有寫作者都是對於時間「有感」到成了「症」的一群。禎苓的中國行旅,屢屢藉由歷史資料與文學書寫作為介質,見所未見,於未見中重構欲見或應見,都在在證明了那個「中國」、那個「上海」的名存實銷,僅留夢痕。即使如此,仍要一再追索,這是對時間的「不感」還是「有感」呢?或者,以時間之名就可以解釋一切嗎?這是否太過浪漫?那些抹除記憶的暴力不仍然作用著嗎?
楊佳嫻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副教授、詩人、散文家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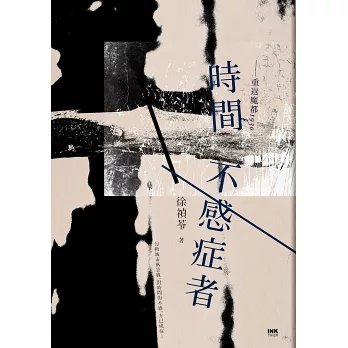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