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物之告別式--父母撒手那一刻來到以後
從來 ,頌揚母愛、父愛的道德文章很多,父母對子女的愛也的確比任何感情都無私,但我們這些為人子女的,我們這些說不上孝順,也說不上不孝,只是本本分分對待父母的子女,我們對父母親的感情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呢?老實說,我不太願意問自己這個問題,因為它涉及了我能對自己誠實到什麼程度、能面對自己的脆弱到什麼程度,尤其,敢把自己揭穿到什麼程度。再說,即使我們暗地裡認了自己對父母的感情裡帶有什麼樣的瘡瘡疤疤,有什麼碰觸不得的傷口、怨懟,我們是否成熟得足以把這一切都承擔下來,而不推說這全是因為父母自己如何如何造成的?(是啊,我們不都自以為很有理由說自己心裡的千百種糾結,根源在父母!)就因為這樣,我們總是有意無意告訴自己別去想這個問題,我們只需要確定自己沒有不愛他們、確定自己對父母所做的總在倫常之內,便可以心安理得的把日子過下去,以此塗銷我們其實不知道怎麼愛他們,或是我們始終覺得他們不知道怎麼愛我們的部分,當作我們從小至今並沒有時不時感到匱乏,有所渴求,愛與被愛的渴求,或者甚至在他們那方也是這樣。
幸或不幸的是,被壓抑的這一切總有一個時候會排山倒海的撲來,整個將我們捲入狂潮,迫使人正視父母之於我們的意含,那關乎愛恨、怨結、恩情、過犯、痛悔、憤懣,而不是道德倫理的意含;讓人悵然的是,這一刻往往是在父母撒手的那日來到,在這個幽深深的死亡大黑洞面前,丟失了部分血肉的心被攪進了情緒的漩渦中,其中「摻雜了憤怒、壓抑、無盡悲傷、不真實感、反叛、悔恨和莫名的解脫感……」,比利時女作家莉迪亞.阜蘭這麼形容她失親那一剎那的心情。
「莫名的解脫感」?看到這幾個字時真是愣怔了一下,但細想,也很難說完全不是這樣。那我們解脫了的是什麼呢?是包袱?誰也不敢大逆不道地說父母是包袱,然而,從他們的位置投射出來的一切:他們立下的或好或壞的榜樣、我們繼承自他們的或好或壞的性格,還有他們對我們的羈絆、驅策、寄望、失落,我們偷偷企盼於他們的等等、等等,不都早已被我們化為包袱實實扛在肩上了嗎?有些時候,我們真的以為自己被壓得不能喘息。也許真如莉迪亞.阜蘭所說,在父母棄世後,有那麼一刻會萌生出一種莫名的解脫感,羽翼頓然一輕,天地我獨翔。但片時之後,虛幻的自由讓人虛脫,一轉頭又見到父母親身後的遺物,那沉甸甸的包袱的重量便通通回來了,而且這次是這麼地具體有形,佔空間,有體積,硬梆梆。
遺物,這些村上春樹稱之為曾經和亡故之人「一起行動的影子」,我們該拿它們怎麼辦?附加它們本身不見得有的意義,把對待這些遺物的態度,當作是我們對待故去親人的態度?或是單純把它們當作舊物、廢物來處理,想丟就丟,不帶感情?但事情向來不是這麼簡單的二分法。即使是先此後彼地採取了這種二分抉擇的東尼瀧谷(他先是試圖讓亡妻的七號洋裝和鞋子在另一個女孩身上活過來,不久醒悟「不過是陳舊的衣服罷了」,即叫二手衣店來拿走,多少錢都無所謂,兩年後喪父,他更無顧忌地把遺物當舊物),最終還是不免「(在父親收藏的)唱片的山完全消失之後,東尼瀧谷這回真的變成孤伶伶孓然一身了。」村上最後這淡淡的一筆還是點破了故去親人的遺物是他們與我們在人世最後的一絲牽繫。但〈東尼瀧谷〉畢竟只是村上快筆虛寫物情,回到真實人生,在打理親人遺物時,物與不物間,是讓人心情無定向擺盪的一整片灰濛濛地帶,有種種情緒說不出。
也就這樣,初讀這兩本薄薄的《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情書遺產》很難不帶著情緒進去,又帶著情緒出來。開頭這端的情緒一半是自己的,自己帶著戒慎恐懼之心走進這個深怕會引爆什麼的主題裡,另一半則源自於作者,作者以理性客觀地審視喪親之痛、不刻意煽動情緒的筆調一點一點安撫了前半的心防。作者身為心理分析家,好像深知該往何處扎針,針尖輕輕一點就有細小的血珠滲出,微微酸楚,但不痛。於是我們出神地看著她把針左右上下移動,遍處巡查病灶。我們滿懷信任地等著她下針,等著自己隱藏在某處的暗疾就要得到滌清、除滅,幾乎要忘了這裡躺在診療床上的其實是她自己。
但這麼說並不是意味這本書把喪親情緒寫得過於普遍化、一般化,甚至說規格化,以致人人能移情其中,對號入座;而應該是說,作者幾近全面寫到了內心層層次次的感受,即使我們有幸不曾經歷,我們也可能在其中照見某時的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牽絆,尤其是她精簡扼要地描寫了喪親之後,在面對不得不的日常瑣事時引發的種種困頓、窘促,我們總能認同她的哀嘆,像是在最後一線生死之隔即將打破之際跟母親、父親告別的景況,還有為什麼她斤斤計較著父母沒有遺囑交代怎麼處理遺物,以致她必須殫精竭慮地翻探父母的箱櫃。何況,她繼承的遠不是幾只箱櫃,而是一整間屋子,一整間帶著父母兩人生命史印記的屋子。
看著作者一一追溯這些物品背後隱藏的私歷史、大歷史,我們好像忽然懂了為什麼許多童話故事都會有夜半時分家裡的東西自行活起來、動起來、說起話來的想像。誰真的敢說白日裡靜靜在一側旁觀人世的物品沒有感應人心的力量。而且,就像每個人的生命都會不斷衍生出神經突觸與其他生命做有機連結一樣,每件帶著生命史印記的物品也都會連結到另一個人的生命。莉迪亞.阜蘭在清理父母遺物之間,幾次不意撞見了自己、自己童年的遺跡、祖輩與孫輩之間的祥和天倫,以及自己與父母的糾結,甚而她還撞見了父母的父母,以及他們在她父母身上所留下的懷想與傷疤;家中幾代人盤錯的情感,甚至她父母跨越的那一整個時代的乖舛全都膠葛在幾件不起眼的小物件、小紙頭裡,沉重得讓人想別過臉不看。但也讓人意識到,原來,這世界還是依循著「物質不滅」的定律運行,凡存在必留痕跡。遺物,從這個角度來看形同「歷史證據」。
但遺物,也是「留情」的同義詞,這在這兩本書中處處得見,譬如有兩樣東西所拉出的感情,特別會讓人看得心柔軟了起來。一是作者的「母系遺產」,包括她家中幾代女人留下的手工刺繡、織品,以及母親數十年來親手精心為自己縫製的無數華美服飾。讀到這些段落,不免又想到村上〈東尼瀧谷〉中的那個看到新衣服不買就「單純的單純的無法忍受」的妻子。衣服之於女人簡直像基因一樣,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在其中表露無遺;莉迪亞.阜蘭也從母親一整間的衣服中,看見了母親和她自己的生命勃發。寬慰的是,她讓母親的這些衣服最後都有了妥善的歸處,以獨特的方式向她母親的才華致敬。
再是,作者繼承的種種父母遺物中,最教人詫異的莫過情書,她並據以寫成《情書遺產》一書。這些共七百五十封的情書是她父母初識時相隔兩個國家唯一的聯繫,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兩人平均一週互相回覆一次,如此持續三年。我們都能體會戀愛中的人是怎麼看待情書的,但大概沒有多少人「有幸」讀到自己的父母互訴衷曲的情書。「有幸」在這裡顯得弔詭,即使親如父母,在沒有他們應允的情況下擅入他們的私密世界,心裡多少有負擔;但如果有幸獲得這種奇妙的經驗,怕是會比收到情人寫來的情書更加悸動吧,因為正如莉迪亞.阜蘭在書末所說:「我在裡面看到的,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不只是兩個人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人如何結為連理,裡面還有某種宇宙起源論的成分,一種開基史,一面每個人都想在裡頭認出自己的鏡子:渴望自己乃因愛而生。」但其實我們並真的不需要這樣的情書遺產,因為我們知道,在那一日到來以後,天下父母最珍惜的,也務必要我們珍惜的,就是這個在愛中孕育的遺物:我們自己。
邱瑞鑾(文字工作者,譯有十餘部法國當代小說。另著有圖書館讀書生活記事《布朗修哪裡去了?》)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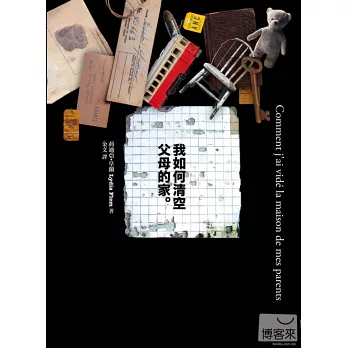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