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通靈少女之恆春古調-讀周芬伶《花東婦好》
寫這篇文章的八月中旬,就那麼巧的,我剛頂著烈日從禮那里部落回來。
這讓人足足曬脫一層皮的魯凱排灣部落,是八八風災後遷村而來,具體位於屏東縣瑪家鄉涼山瀑布附近,林廣財〈涼山情歌〉不就這麼唱的:「屏東縣是懷念的故鄉,瑪家鄉涼山村的小姐我愛你。」走了一步,眼淚掉下來的,不是林班工人,而是車行暈吐的我。那潮州車站舊圓環前的燒冷冰還在胃裡翻騰,眼前晃動的是曬到紺紅半生熟的遊客,黑得油光閃閃的端盤子排灣姑娘,而為我們導覽百合國小的魯凱族青年小凱,那膚色已經遠遠超越老滷湯,呈現一種深沉的炭石黑,完全吸光的那種。生平第一次,我覺得我以前一個字也沒讀懂周芬伶,她的耐熱耐曬,她的屏東潮州,那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與如同被詛咒了的悲劇家族。她的母系銀河——五魁寮河、力力、赤山、萬金、大武山、平埔馬卡道族,檳榔樹與香蕉林,遺傳自母系的深目高顴,菱角嘴,藝術天分和黑色叛逆的血液,神奇的浪人與狂人的組合。這裡面,一定有些什麼,有些我從未明白的事。
什麼樣的書,可以足足寫了十年?《花東婦好》接續了今年初《濕地》而下,多麼大氣明迷,音聲朗朗的四個字。七○年代河南安陽殷墟花園東方出土的婦好墓葬,兵氣加瘋氣的女子,三千年前美貌武勇兼備的美少女戰士,連結一八七一年宮古島漂流來台遇害的琉球王妃愛沙,日治時代東港女畫家盧寶惜/品方白色恐怖受難史,以詛咒與救贖為脈絡,將串起怎樣的一個南方且驃悍的故事?
從企圖心與說故事的結構與技巧上來看,《花東婦好》絕對是周芬伶近期最佳之作。就女性小說家寫台灣歷史的角度,也補足了歷年少見的南方觀點。作者自己倒是有不得不寫的理由;「人人都有自己的疾病史與創傷史」。從二○一一年《雜種》〈婦好〉一文開了頭,三千年前一怪咖(或稱酷妹。女巫兼戰神,既是武丁的寵妃,又封有領地,十九歲就帶一萬三千兵馬征討鬼方,左右各執一銅鉞,一人能敵百人)。這故事成了周芬伶一塊心病,「想把婦好的故事寫成一部小說,一個甲骨文與怪女子的故事」。
《花東婦好》這個長篇,橫跨兩岸三地數個時空,除了屏東潮州的人文地理,還延伸出去四○年代留日藝術史、瘧疾疫病防治、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政治氛圍、大陸骨董收購史。琉球漂民遇害的牡丹社事件與三千年前殷墟婦好墓則作為詛咒的遠因,相互對應,體製驚人。這書的寫法重重疊疊,章節繁複,前面沒寫清楚的,後面換人稱補強。人物雖多,倒不複沓,收放自如,極為好看。它等於一次性的把周芬伶多年寫作關注的主題總綰起來,政治、歷史、性別、藝術與文字,連女女戀的性別挑戰(品方與高橋)也沒落下。甘耀明《邦查女孩》伐木史寫的還是半虛半實,史料上的故事,周芬伶《花東婦好》可真是近身肉搏,是自己的,也是自己理念的延伸。
《花東婦好》是一部魔幻兼寫實的女人生命史,奇特的是以詛咒與救贖串聯全書。主軸是盧寶惜及潮州夫家柯氏一族,這原漢雜處,閩客相鬥的沒落小鎮,正是周芬伶生身之地。寫了三十幾年,周芬伶似乎第一次下定決心正視母系的原罪與歷史。這黑色的血液,悲劇的源頭,是和父系福佬族群迥然不同的山海世界。兩邊都是大家族,人多濟濟,祖母各有雙份,但「漢人、平埔加排灣」的混融基因,則源自於她的外曾祖父。
周芬伶父系曾祖是河南遷至福建的漢人移民,母系外曾祖父則姓洪,舊籍車城(古名柴城)。柴城原為排灣族所有,排灣族稱此地為Kabeyawan(漢人音譯為「龜壁灣」),為抵抗清兵占領,構築木柵作為防禦,故有柴城之稱。漢人通譯與地方官在此霸占原民妻女與財物無數,周芬伶外曾祖父日據時代即是專辦原民米糧交割的,如山大王一般,見稍有姿色的原住民婦女便強占為妻,因此後人血統極為混雜。
周芬伶《絕美》〈我的紅河〉,《母系銀河》的〈關鍵詞:密碼〉、〈父家與母家〉,《汝色》〈與沉重的黑〉、〈與蜻蛉故鄉〉都曾反覆述說過母系的背景。《浪子駭女》卷四〈玫瑰叛變〉李姓曾祖染指番女並殺其夫而受「我的靈魂將糾纏你們一千年」的詛咒;《影子情人》〈影子母親〉裡素素尋訪卡將的故鄉楓港,方知洪姓曾祖當年娶排灣平埔二妾,打造了一個母系為主的女兒國。這些文本都曾不同程度的透露了楓港、車城、歸來、潮州、泗林這一條周芬伶母系(屬於大武山與原民森林)的歷史星圖。這麼多原住民血統「假藜仔」的姨婆,「深凹且憂鬱的眼,赤足長衫,辮子盤在頭頂,生命特別美麗卻脆弱」,在《醜醜》、《小華麗在華麗小鎮》、《妹妹向左轉》裡,也都影影綽綽的出現過。
母系愛美不羈,纖細狂暴,富藝術天分,但也同時瘋癲脆弱且背負原罪,是因為「我們身上流著黑色的血,那是前人洗也洗不清的罪孽」。而這體會,也反映在周芬伶自己「與父系的理性格格不入」的認知上,〈關鍵詞:密碼〉一文就說:「我的心有一片曠野,在山與海之間,我不知在其間行走多少年,總是邊走邊唱,那是曠野中寂寞的高音」。「我要去尋找那片曠野和海洋,那裡有個包黑頭巾穿黑長衫的女人,她的臉望向海那邊,她在看什麼呢?……她的苦楚中一定也有我的」。
一曲平埔族的悲歌〈思想起〉,道盡當時女人的苦楚,這基本是山地怨女的哀歌,而不是漢人的。《花東婦好》〈萬年寶惜〉裡,詳細描述此一情景,「她們成群結隊走在山海之間,唱著帶有哭音的歌曲,楓港、牡丹、滿州、獅子鄉皆是如此。」思想起,落山風,恆春古調,鬼哭狼嚎,女人從海邊走進山裡,要做人細姨了,心中忐忑:「唉喔枋寮那過去仔依嘟是楓港/唉喔喂/希望阿哥仔相痛疼/唉喔喂/細姨仔娶來是人人愛/唉喔喂/哎喲放捨大某仔尚可憐/唉喔喂……」。
《花東婦好》裡,山城女孩英秀就是這樣十二歲從車城被轉賣到海邊東港盧家為僕的。這也是《花東婦好》一書的主場景。盧家在東港是殷實人家,寶惜有五個美貌姑姑,品香、品秀、品玉、品月、品方,人稱東港五君子。英秀出身卑微,漢人大扁臉,在盧家一屋子時髦洋裝美麗少女中不知所措,寶惜只大英秀四歲,西洋混血,鬈髮膚白淺瞳如金絲貓,二人身分懸殊,卻結下姐妹情誼。寶惜母親玉郡為大某,銀妃是細姨(如周芬伶大小祖母)。嫡母出走,庶母當家,寶惜與弟弟寶寬受盡薄待(寶寬又如周芬伶父親翻版,一生抑鬱)。
寶惜與姑姑品方習油畫膠彩,柯純學雕塑,同赴東京美術學校留學。品方與女老師高橋親密異常,柯純則不避忌血緣亂倫,迷戀舞蹈家堂姊柯清清。一九四三年在回台的高千穗丸上柯純被魚雷擊沉殞命(這些留日畫家如黃清埕、女友桂香、陳海英等俱有所本,盧寶惜就是陳進的影射)。寶惜帶孕嫁入潮州柯家,這個帶有原罪與詛咒的家族。柯家曾祖柯土水,好色狠毒,祖居車城,發跡後移居潮州。當年在八瑤灣事件中搶奪了愛沙等人財物,後轉任地方官,搶奪原民財物與美女,娶妾無數(十足周芬伶曾外祖父寫照)。祖父任日本官員保鑣,娶日本妻。黑色血液開出毒花異草,柯純外表混血漂亮,個性卻狂亂異常。柯家因受了愛沙詛咒,男丁於戰禍與瘧疾中紛紛死去,幾成「寡婦樓」。寶惜入門即寡,命運多舛,繼品方以台共被捕後,為了避禍,入獄前將與山地醫師余久義生的女兒香儀改名小曼託付給英秀,英秀遂成小曼養母。寶惜與柯純的孩子取名柯純真,純真後與女友生下綠色,由寶惜撫養長大。
小曼愛上保釣政治犯高準,生下高捷,這宅男網路小說家後來遠赴河南殷墟,追索甲骨文字與古董挖掘史,並打算以婦好故事寫成小說(也因此衍生出周寧、骨董王和成明、成雅各這幾個跑龍套的腳色)。於是故事三股擰成一股。商朝皇后婦好、琉球王妃愛沙,以及東港盧家千金寶惜,三人皆貌美如花,體有異香,卻可惜「美人無美命」,青春殞命。這美麗而夭亡的悲劇,家族、女性與文字的宿命,是詛咒也是救贖。用一句話來概括全書四百餘頁的話,那就是——女人困鎖於詛咒中,終究因使用文字而得自由。
聲稱自己「沒有歷史癖,只有文字戀」的周芬伶,這回猶如文字火燒田(賴香吟語)一般的《花東婦好》,就像白鶴將自己的羽毛混織金線一般,密密層層,原漢混融的家族歷史,巧妙織進了由婦好、愛沙,以及寶惜/品方三方共構的女性生命史。婦好和愛沙都是巫女兼王妃,前者被大妃替身黑魔法害死,後者則自殺前詛咒柯家斷子絕孫。寶惜嫁進柯家,最終她與姑姑品方也因留學日本陸續被白色恐怖株連,都死於被捕與自殺。姑姪二人在屏東女中任教之際,於三地門排灣部落寫生,不但結識排灣醫師余久義與魯凱護士夏玫瑰,也留下了不朽的畫作。
這故事的尾聲是,婦好花樹圍繞,咒願詛葬,長眠千年,終未受驚擾;愛沙的頭顱最後與身體歸一,送回琉球安葬,化解了怨念;寶惜的通靈人孫女綠色,能見到亡者,因找到品方姑婆祖的日記與畫作,終於還原歷史,洗刷冤屈,為品方與寶惜兩人舉辦了畫展。這盧家百年史,就結束在小曼在東港終於找到母親寶惜的老家,看見屏東女中展出的母親和品方的畫作,並遠赴哥倫比亞,尋獲親生父親余久義捐贈當地政府的香儀樓。曾經相戀的高捷和綠色,驚覺彼此原來是表姐弟,祖母同是傳奇中的寶惜。
通靈少女,恆春古調。這麼一個有關墓葬與詛咒,有關通靈,有關深山部落,以及透過文字得到救贖的故事。構築了這麼紛繁的人事,跨越三度時空如蟻穴連結,重重疊疊如迷宮,作者的中心思想是,「如果生命是一本書,我們都活在一個詛咒中,它是原罪的另一種自我安慰的說法,東方人沒有原罪概念,於是創造了詛咒。而所有的原罪與詛咒,追求的不過是救贖。」人總想去除框架,以獲得自由,然而真正的自由是不存在的。甲骨破片,婦好墓葬,那是神的文字,也是文字的神,瞬間即永恆。它彷彿告訴了我們,亙古以前就有一個女力時代,女人能文能武,撐起了半邊天,也承擔了不該她承擔的原罪。《花東婦好》〈閒花〉中,甚且將安陽殷墟與恆春半島對比。武丁與婦好所生活的河南安陽,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與台灣的長濱文化相當,與車城龜山生活狀況更為接近,都是小丘與半山腰,下接平原,同樣缺海鮮,口味偏鹹而嗆。女人的命運,步步驚心,彷彿演了一齣穿越劇。
近幾年讀周芬伶文字,透明貼身到了極致,幾有不忍之情。中年已過,生死離苦,命運的霜雪,瞬間掩至。《濕地》的「番外」諸篇,固然傷悲滿眼,卻也見出她如婦好一般高舉巨鉞號令萬方的決心。她十年磨一劍,霸氣挑戰那未曾寫出的家族原罪與女性/文字的宿命,但真實人生裡,她還是那初出道時的絕美「沉靜」,講話永遠慢吞吞,囁嚅著,落半拍。她一方面是非常靈心藝術的,同時又是物質至上的戀物癖。自稱「身軀乾枯,靈魂充盈」,玉器古玩,青瓷水晶加香奈兒包包2.55,無一不精。
這讓我想起,婦好若在今日,上陣前夕是準備華服彩妝假睫毛,還是霍霍然磨刀劍斧鉞呢?女巫兼戰神,不但打仗神勇,陣仗華美,還學富五車,掌醫藥占卜,身兼史官,又能引領時尚,擁有骨頭細雕的玉簪無數。她的死亡,象徵女性世代凋亡,此後殷商母系國度從此沒落,由崇尚理性的周朝逐漸取而代之。
生命實難,腦的結構如蟻穴般令人瘋狂錯亂,我們的語言與文字,或也只是腦部的異常放電吧!透過寫小說的亞斯伯格男高捷與通靈少女綠色的對話,周芬伶說出了自己的病狂與執念:「只有寫字或唸著文字才能忘記活著的痛楚。」「詛咒是有力量的,巫也一直沒有消失,它只是轉化了。」
如周芬伶所說,我們的腦袋給我們的歡樂是如此短暫的,痛苦卻如此深長。所謂巫者,是靈感者,也是腦部異常放電的人。因此我們都是綠色通靈人,兩行中可以看出另一行,眼中能看到他人的心思。因為聰敏,所以稍縱即逝,異常脆弱。藝術與文學,是彼岸花,亦是沙羅麗,魔魅之花,永不凋零。
如果生命是一本書,我們都活在一個詛咒中,寫之不盡,至死方休。《花東婦好》這一闕通靈少女的恆春古調,告訴我們詛咒是有力量的,巫也一直沒有消失,它只是轉化了而已。
張瑞芬
二○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本文作者為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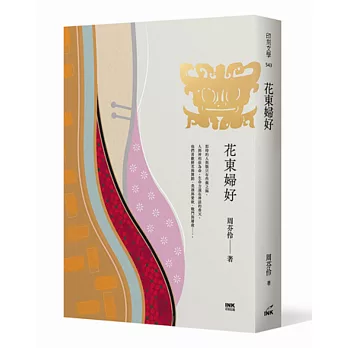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