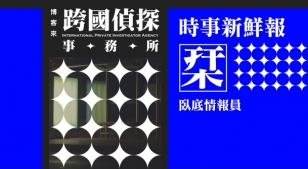後記(節錄)
這篇小說雖以「魔神仔」為主題,卻很重視「巨人」意象。相對於矮矮小小的魔神仔,或許會讓讀者覺得有些突兀吧?其實這意象是有緣由的。我很喜歡石黑一雄《被埋葬的記憶》,這本小說的英文標題沒有記憶,而是「The Buried Giant」,這個「Giant」,可以被解讀成巨人。到底「Giant」是什麼呢?或許每個讀者都有不同的見解,但我則根據我的解讀,將「The Buried Giant」當成巨人,把其意象借用到這個故事中。
「南方澳真的有好多東西消失了。」
這是佑娥在故事中說過的話。在本作出版的現在,小說裡提到的那座大橋也已於二○一九年十月斷裂,又一項南方澳的事物消失了;從消失的猴猴族開始,不斷重複的喪失——這一切,都是「被牽走的巨人」。
講點題外話……不,或許也不算題外吧?畢竟與創作理想有關。總之,這篇小說是我對「後外地文學」的嘗試。
什麼是後外地文學?其實這是我瞎掰出來的創作理念——對,沒什麼了不起,只是硬要講得很酷炫而已;所謂的後外地文學,是對外地文學的回應,然而什麼是外地文學?最簡單的理解,大概就是殖民地文學吧。這是由日本時代文學研究者島田謹二提出的,他指出外地文學有三元素:
一、異國情調。
二、寫實主義。
三、鄉愁。
什麼是異國情調?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外地文學的預設作者,是那些在臺日人,他們生活在臺灣、已有臺灣生命經驗,這些人創作出來具臺灣風貌、以臺灣為主題的作品,即是外地文學。對內地人來說,這種臺灣風景就相當於異國的幻夢吧!那是浪漫、美麗、充滿綺想的。雖然對在臺日人來說,他們可能只是書寫生命經驗,也就是寫實主義。總之,外地文學是殖民地文學,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把它視作地方主義文學。
在當代的臺灣文學史研究上,外地文學飽受批判。
為什麼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異國情調」使臺灣成為被凝視的對象——相對於「內地」的「外地」,這難道不是被想像出來的嗎?舉個例子,說到原住民,許多漢人都有愛喝酒、開朗、體能很好之類的刻板印象,但這些想像也有可能不符現實。主張原住民就是那樣,當成事實在傳播,結果就是表面上在談原住民,原住民卻是缺席的……異國情調也是如此。異國必然是本國的凝視,換言之,即是他者;那以異國情調為前提書寫的臺灣,有沒有可能反而使真正的臺灣缺席呢?
這是外地文學的危險。明明在寫臺灣故事,卻讓臺灣失去主體,這在殖民體制之下更加嚴重。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有些好奇,既然外地文學如此惡名昭彰,為何後外地文學要回應它?
這是因為——「異國」確實是浪漫的。
有個審美上的弔詭。出國旅行時,宗教場所往往是重要的觀光景點,我們也著迷於那幻彩的裝飾、神祕的符號、介於神聖與恐怖間的怪異塑像;但對國內的傳統宗教場所與活動,主流意見卻傾向那是惡俗的。像是看不起廟會,覺得鞭炮聲太吵等等,但要是在國外被捲入熱鬧的大型宗教活動,再吵都能接受吧?
那畢竟是異國啊!
這種弔詭,可能肇因於我們太習慣這個環境,產生審美疲乏,以致無法將臺灣視為美的對象。對外國人來說,臺灣廟宇當然是美的——這就是異國情調;另一方面,身為都市人的我們也失去與傳統宗教的連結,高速的現代化改變了生活,傳統反而變得格格不入,我們不再抱持關心——與此同時,我們對歷史也幾乎不抱持關心了。
現在,我們或許正站在一個重要的時代交岔口。
我不想說怎麼做才是正確的。但毫無疑問,我們的每一個決定,都會決定臺灣未來的樣貌;然而略過臺灣史,我們要怎麼界定臺灣呢?畢竟臺灣的族群多元而複雜,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歷史,或自己版本的歷史。如果不同族群要產生共同的臺灣想像,至少也要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但要是當代已喪失對歷史的關心,我們要如何談論臺灣?身為小說創作者,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是:我們怎麼引起讀者對臺灣史的興趣?
我的看法是浪漫化—─
把過去的臺灣當成異國來描寫,刻意賦予幻想怪奇,以呈現臺灣之美;如果我們能在通俗作品中燃起讀者對臺灣史的好奇,自然就有利於談論何謂臺灣,而後外地文學,就是我所提出的方法論。
參考外地文學三元素,我也提出後外地文學三元素,如下:
一、異國情調
二、實際地景
三、鄉愁
我所說的異國情調,與島田謹二的異國情調不同,是有意識地賦予幻想之美;而這份幻想之美,是奠基於時間帶來的距離感——正如外地文學的外地,是相較於中心的邊陲,如果沒有空間上的距離,異國便不存在。後外地文學則是透過時間上的距離形成異國,所謂時間上的距離,並非僅僅書寫過去某個時間點,而是意識到讀者是從當代的角度觀看該時間點。
以拙作〈潮靈夜話〉(收錄於《華麗島軼聞:鍵》,九歌出版)為例,在書寫一九三○年代的同時,特別著力於當時地景,就是企圖透過「已經不存在的風景」或「不可能的風景」來營造幻想性;現在仙洞旁邊的防波堤,已非昔貌,而社寮島上的千疊敷,也不可能有著如鏡般的海面。但這種不可思議的幻境,是奠基在讀者可能親臨基隆的仙洞與社寮島,這個當代實景與悠久時空的落差,允許幻想被覆蓋到實際地景上,真實的地理空間也成為通往歷史的門扉,那份歷史是美麗、綺想的、宛如異國的歷史。
這也是我將實際地景視為後外地文學重要元素的原因。實際地景具備身體經驗的基礎,得以成為有力的想像參照點。又如〈鱷魚之夢〉(收錄於《筷:怪談競演奇物語》,獨步出版),故事發生在被水庫淹沒的學校與村莊,但當主角抵達沉入水底的廢校時,那座學校居然完好無缺——這是不可能的場景,因為該學校已成廢墟。如果是虛構的地景,這一幕其實是「可能」的;但正是建立在實際地景上,才因不可能而夢幻。此一夢幻之所以成立,正是讀者身處的時空,成為視點的中心。
外地文學以內地為中心,後外地文學則是以當代為中心,預設中心的存在,才使異國幻想成為可能。
至於鄉愁——這是書寫後外地文學的重要動機。在現代,臺灣人對臺灣還沒有共同的想像。就算有,也很容易成為剝削式的想像。但對臺灣人來說,那個尚未出現的臺灣想像,才是理想的故鄉,不是嗎?期待這樣一個想像出現,是我書寫後外地文學的殷殷盼望。
讀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質疑,這套理論真的有必要回應外地文學嗎?說到底,此一理論的主張,不過就是根據實際地景書寫幻想,引發讀者對地方史的興趣,作為討論「何謂臺灣」的資本。即使不回應外地文學,此主張依然成立。但我是這麼想的。有意識地編造幻想——難道沒有危險嗎?畢竟歷史是無法自我主張、自我維護的。在對歷史毫無敬意的凝視下,幻想反而會扭曲歷史。選擇回應惡名昭彰的外地文學,正是一種自我提醒;在臺灣的殖民帳還沒算乾淨,甚至對臺灣想像尚未形成共識的現在,異國情調是需要格外謹慎的。
大眾小說能有助於認識「臺灣性」?
坦白說,我自己也覺得太樂觀。但要說這是徹底徒勞無功的,倒也不盡然;就算我提出的理論不堪一擊,只要我們有著共同的鄉愁,那後外地文學就像是拋磚引玉,我期待著那塊美玉能發出懾人的光輝。
在歸鄉之前,我會繼續寫作下去。
最後請容我致謝。小說中的沖繩史觀,受限於我自身知識,雖有友人宥任協助,仍有未能全面釐清之處,還請見諒;此外,由於臺語並非我的母語,本文之臺語文正字,皆由小鶴協助翻譯而成,在此感謝以上二位。也感謝我童年舊友盧博士非自願的友情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