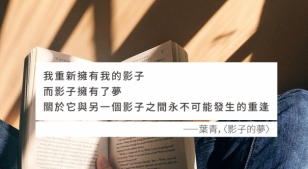
文/蔡琳森2017年11月07日
80年代初,我的影像經驗始於傳統的映像管電視,顆粒粗大,電子束打到熒光粉上的一瞬,影像自一縷光的麇集裡暈散開來,讓人瞳孔不住顫慄,雀躍地跟著盛綻了。螢屏呈迷人的淺弧,表面帶有溫熱,蓄著靜電密布,若以手掌或臉頰輕貼上去,只感到一陣麻麻糊糊的搔癢,予人一種自現實向著虛幻窺望之邊界感。 more「只要眼睛看到、耳朵聽到,大腦就會相信。」
-史上最偉大魔術師、脫逃術師及特技表演者 哈利.胡迪尼 ( Harry Houdini )
2012年台灣國家地理頻道熱映節目【腦力大挑戰】精華收錄
整合了神經學、心理學、眼科學的各路人馬,這個熱門電視節目打造了一支破解團隊,並大膽借用了兩位知名科學家:認知專家 - 丹賽門,以及記憶專家 - 伊莉莎白洛夫特斯。企圖藉由它們「充沛」的腦力來破解大腦最匪夷所思的各種現象;節目更首度揭露全球知名的魔術師,包含大衛考柏菲、阿波羅羅賓斯,以及色彩學專家博洛多等人的「騙人把戲」都一一現形。
本書共分作三個單元,「看見」、「思考」、「存在感」:透過這三個單元,讀者會發現為什麼迷人的視覺幻象及有趣的實驗會如此欺瞞了我們的腦袋!? 並且發現眼睛的生理結構竟然對我們的視覺有巨大的影響!我們人類,甚至會去憑空想像許多不曾存在的情節,來填補已經存在我們腦海中的錯誤記憶!
在每一個章節中,科學家們將引導讀者先透過一連串感知與想像的實驗來發現我們的大腦如何運作,並且造成錯覺;接著再以最淺顯易懂的語言,替讀者解惑並說明背後運作的科學與原理。
這是一本震撼力十足、充滿機智與洞見的書,帶領讀者透視大腦巧妙操縱的幻術,並透過最豐富先進的知識,引導讀者重新檢視這些生活中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每件事,是所有希望自我探索的讀者必讀的絕妙好書!
「我預見未來人類之於機器人,會像狗之於人類。機器人的世代就要來臨了。」
-克勞特.雪龍(Claude Shannon)美國數學家、資訊理論的創始人
作者簡介
麥可斯.威尼 (Michael S. Sweeney)
畢業於內布拉斯加-林肯大學,並在俄亥俄大學新聞學院取得博士資格。曾追隨國家地理的羅伯特巴洛得博士前往鐵達尼號遺骸進行探險考察隊的隨行採訪,斯威尼的著作包含了《終極求生指南》、《和平:符號的自傳》、《當上帝不再眷顧我們》以及《頭腦:完整的心靈》
導言
大腦操縱師
我是個職業幻象師,不用吊鋼絲或玩弄攝影機,就可以在空中飛行。我可以變出降雪,讓自由女神像和里爾噴射機消失,也曾把自己切成兩半。每一場表演中,我都會把13名自願的觀眾變不見。觀眾放心地把他們的感知交到我手上,知道我會把它扭曲成各種有趣的模樣,讓他們心悅臣服地欣賞我長達九十分鐘奇蹟式的表演。我利用故事、音樂和心理學創造出幻象,喚起觀眾心中的情緒,讓他們嘆為觀止。這類魔術帶給觀眾的,不是困惑,而是驚奇。有人稱魔術師為表演界的科學家。舞台就是魔術師的實驗室,我們經過反覆試驗,了解了大腦內部神秘的運作。我們發現,只要用一些技巧和誤導,就能讓一名觀眾適時將注意力放在正確的地方,讓我們創造出魔術幻象。事實上,幻象誕生於大腦裡,而非舞台上。很多因子,包括文化造成的偏見和信念,都會影響人的感知,而有技巧的魔術師就會藉此創造出表面的奇蹟。置身紐約、巴黎或洛杉磯戲院的觀眾,跟其他文化中相信巫師和巫醫的民眾,對這些表演的認知就大不相同。
以下是個很有名的故事。法國魔術師胡迪(Jean-Eugene Robert-Houdin)被許多人視為現代魔術之父〔也因此韋斯(Ehrich Weiss)才會把自己重新取名為胡迪尼〕,他曾應法國當局要求,前往受法屬阿爾及利亞平息一場政變。當時有一群名為馬拉伯特人(Marabouts)的所謂聖者,詭計多端,許多阿爾及利亞人都相信他們擁有超能力。這群馬拉伯特人用各式花樣招來信徒,唆使同胞叛變、脫離法國。法國政府派胡迪前往阿爾及利亞,要他「以魔術智取」馬拉伯特人。
胡迪攜著一個小小的金屬盒,來到阿爾及利亞。他把盒子放在地上,挑戰最高大有力的馬拉伯特人,要他把箱子舉起來。於是一名身形巨大強壯、彷彿舉重選手般的馬拉伯特人接受了挑戰。他滿臉自信地抱著箱子,表情卻變得異樣、困惑,甚至尷尬不已。他完全舉不起箱子,儘管胡迪那瘦子幾分鐘前才拿著同一個箱子。
挑戰者滿身是汗,但儘管他使出吃奶的力氣,仍徒勞無功。一股前所未有的疼痛震動他全身,在他體內哀號,他直覺就想放下箱子,但雙手卻像黏在冷凍鋼筋的舌頭一樣,無法將箱子脫手。接著疼痛突然消失了,他摔倒在地,倍感羞辱但身體完好無傷。此時胡迪走了過去,不費吹灰之力就舉起了箱子。胡迪得一分,馬拉伯特人零分。簡而言之,後來阿爾及利亞人放棄了叛變,胡迪則被全國人民視為英雄。
胡迪所以能讓人舉不起這只箱子,秘訣在於埋在地下的一塊電磁鐵(聰明的胡迪在前一晚就把電磁鐵藏在那兒了)。當他打開電流,箱子就被釘在地上,提高電流則讓挑戰者感受到從未經歷過的電擊。胡迪挑戰了阿爾及利亞人的感知。有些原本以為馬拉伯特人真的擁有魔法的觀眾,都因此清醒過來。有些觀眾則仍相信馬拉伯特人的能力,但以為那名法國人的功力更高。胡迪聰明地改變了挑戰者的肌肉感知,以及旁觀者的視覺感知,也打消了他們原本想叛變的意願。
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而言,胡迪的故事乍聽之下也許沒那麼新奇有趣。然而有些國家的居民對魔法深信不疑,我在為那些當地人表演魔術時,得小心解釋自己其實只是個藝人、幻象師,利用視覺和物理法則,以及轉移觀眾注意力的方式,達到表演的效果,而不是擁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但有時我還是會碰到一些麻煩。
我還記得自己曾被幾名當地魔術師挑戰,他們認為我的表演是要給他們難看。我還得極力解釋,說我的表演有別於他們聲稱的表演,而且也沒有任何要冒犯他們的意思。但我仍不只一次需要僱用保鑣,因為當地魔術師不願相信我的表演純粹是種娛樂,決意要以魔術對決。我於是了解,文化差異的確會如此影響人的感知。
然而我操弄的感知,主要是在生物和心理層面上的。人類大腦是地球上最複雜的器官,那才是魔術表演的真正舞台。
手部的動作無法快過視覺,但可以快過感知。如果大腦知道該尋找什麼,眼睛就會看到什麼。舉例來說,只要能捕捉觀眾的注意力,就能讓魔術達到最大的效果。懂得如何操弄觀眾的注意力,是一名魔術師最需具備的技巧之一。
如果我可以引起你的注意力,讓你專注在特定的地方,你很有可能就不會注意到眼前發生的事。假設我對一名狂熱的棒球球迷說:「你等會兒就會看到某個你最喜歡的球員」,並且將球員帶到他跟前,那麼我就算真的叫助手牽一隻大象走進屋裡,甚至進入那球迷的視線中,他也很可能不會注意到那隻大象!這人的注意力會完全專注在球員身上,而看不到球員看到的景象!大腦一次只能注意一件事,你專注的不只是視覺,還包括注意力和思緒。在魔術表演中,你甚至會試著自我詮釋表演本身,讓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
魔術師想順利轉移觀眾注意力,就要巧妙運用心理技巧,操弄觀眾大腦的不同部位。只要能順利轉移注意力,觀眾就不會發現自己錯過什麼,會被蒙在鼓裡,沉浸在魔術裡。如果我拿一只信封,舔舔封口處、封起來,那麼觀眾就會假設信封封起來了,無法塞進其他東西。搞不好信封的另一邊根本就是打開著的,但因為我不經意地展示信封,然後封起來,觀眾就會假設我沒在信封上動什麼手腳。但如果我拿起信封說:「這是一個普通的信封,貨真價實。」我就會讓人開始注意信封,讓觀眾專注在信封上,並心生懷疑。
如今科學家開始發現一些現象,加以分析,但魔術師在好幾個世紀前就已經發現這些現象了。比方說,某些最能欺騙觀眾的手法,都牽涉到科學家所謂的「改變視盲」(change blindness),也就是觀眾面對某些幻覺時,注意力倘若專注在特定範圍或作業上,就會忽略視線裡一些很明顯的改變。有時你越靠近看,看到的就會越少。這就是魔術好玩的地方。
此外,有些直接了當的視覺幻影,也是在欺騙眼睛,換句話說,是在欺騙大腦。例如說,魔術師在好幾百年前就發現如果他們用黑布當作舞台背景,觀眾就看不到舞台上的其他黑色物體。魔術師稱之為黑色藝術。我小時候第一次看到《艾德.蘇利文秀》(The Ed Sullivan Show)裡那隻有義大利口音的老鼠時,就對這種現象感到既有趣又困惑。這隻叫做吉喬鼠(Topo Gigio)的玩偶,完全不同於我以前看過的任何玩偶:牠的身體完全沒有任何看得見的支撐。牠可以用自己的兩隻腳爪站起來,而且還常常爬上蘇利文的袖子上,親他的臉頰道晚安。吉喬鼠就像一隻活生生的卡通人物。
當時我並不知道,吉喬鼠的確是有人操縱的,觀眾所以沒察覺,是因為操縱的人全身衣著都是黑色的,戴了黑色兜帽和黑色手套。我直到六年級時在圖書館借了一本魔術相關的書,才了解這一點。玩偶師讓觀眾看到活生生的吉喬鼠,但無論是攝影機或現場觀眾,都完全沒捕捉到玩偶師的身影。
這一類的視覺幻象很好理解。但這本書及配套的電視節目〈大腦實驗室〉,最迷人的特色之一,就是讓我們得以探索一些魔術師知道、也利用過,但卻不完全了解的幻象和大腦作業。本書解釋了一些特定感官操作的運作原理,閱讀過這些內容後,我更了解我們這些幻象師究竟都在做些什麼,也更知道該如何使用道具箱裡的一些工具。
身為一名幻象師,我為觀眾創造出一些他們從未目睹的神奇景象(也就是演員口中的「第一次的幻覺」),讓觀眾能重新捕捉那驚奇感。但對我的觀眾而言這些絕非幻覺,他們打從心裡感到敬佩、驚奇,完全被迷住了。我們已經好久不曾體驗這種感覺,尤其現在人們又擁有這麼多以指尖操作的美妙科技。我們靠著手提電腦、平板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就能創造出近乎奇蹟的一切。然而我讓觀眾在一、兩個小時內脫離科技,重新體驗驚奇感,這種感覺真的很棒。這就是我會成為幻象師的原因,驅使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走上舞台。
這本書是非常有用,也非常有趣的工具,可以增加你對覺知的認識,讓你更了解一些神奇的現象。你不但將學會更仔細地看,也會看到更多、體會更多。能參與這項計畫是我的榮幸,也讓我證實了許多過去透過工作發現、但無法清楚表達的論點,並學習到許多有用而迷人的知識。我很高興能與讀者在這個旅程中同行。
By大衛考柏菲 (David Copper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