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導言
不是單純的「出版一本書而已」
《陳夫人》在台灣歷史上,不只是一本小說或一齣戲劇,她代表的就是二十世紀中期以前,在台灣所有受過日本教育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心中共同完美女性的典型。
但有趣的是,「陳夫人」之所以能受台日兩地讀者與觀眾的歡迎,靠的不只是她日本人的特殊身分,作者更強調她是虔誠的基督徒,願意犧牲自己原有的特權,堅持用愛來包容與接納台日兩地人民各自特有的陰暗面。她始終相信愛就是光,光能照亮一切,並去除所有的黑暗,也因此能贏得旁人的尊重與憐惜。
著有《台灣--苦悶的歷史》的台灣旅日學者王育德,在他晚年所寫的《王育德自傳》裡,就提到自己一九四四年因戰局影響,中斷了在東京的學業而回台,在故鄉台南的親戚「黃家」,暗戀一位日台混血的美少女「惠美」的經過。
王育德在書中不但說到「我在東京時,惠美就讀於青山學院大學。她是一位嘴唇豐滿,也就是現在所謂體態豐盈、嬌繞型的可愛大姑娘。我喜歡上她。」在形容「惠美」的媽媽時,更提到「夫人芳子即是庄司總一《陳夫人》中的主角。」以及「芳子夫人更是理想中的日本女性,我覺得將這個人稱為母親,再適合不過了。惠美也具有知識份子的氣息,長相可愛,體格又好。」
雖然王育德在自傳裡,「惠美」只是一個化名,但王育德熱情地寫出自己年輕時在被戰火波及的南台灣,因深愛著這位在測候所工作,活潑美麗的台日混血少女,專程從嘉義翻山越嶺,前往她疏開(避難)的南化山區,途中還必須經過一段名叫「揀死猴崎」的地方,就是台語形容連猴子都會摔死的險峻山路,這樣不惜一死的冒險犯難,就只是為了單純地見佳人一眼。
這段因緣最後雖因王育德與「惠美」的信仰不同而告吹,但從王育德的自傳裡就能看出,《陳夫人》在日治時代的台籍知識份子之間,早已是人盡皆知的小說人物。小說中那位聰明善良的台日混血少女,更成為當時台日兩地男性的夢中情人。
《陳夫人》作者庄司總一幼年時隨行醫的父親來台,畢業於日治時代台南一中,人生的三分之一歲月都在台灣渡過,因而這本書裡所描寫的台灣,真實度絕對高於其他日文小說。
庄司總一就讀慶應大學時代,就用「阿久見謙」的筆名,在《三田文學》發表過不少小說和評論。《陳夫人》內文分為兩部,第一部「夫婦」於一九四○年十一月由通文閣(東京)出版,這是庄司總一首次用本名發表的小說,上市後立刻轟動日台兩地文壇,並榮獲新潮獎候選作品,以及名作家佐藤春夫的讚賞,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本以台灣為背景的暢銷小說。
一夕之間在文壇洛陽紙貴的《陳夫人》,在藝壇也頗受青睞。由森本薰和田中澄江改編成劇本,久保田萬太郎負責製作和導演的話劇《陳夫人》,也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由話劇團「文學座」公演而獲得好評。
一九四二年七月,庄司總一完成了《陳夫人》的第二部「親子」,仍交由通文閣(東京)出版,不但連續印行十二刷,並在一九四三年八月獲得大東亞文學獎次獎(首獎從缺),因此《陳夫人》不只是在台日兩地,連朝鮮、滿州與中國沿海各省及南洋各大城市,都擁有廣大的讀者。本書就是第一部「夫婦」與第二部「親子」的合定本。
七十年來,《陳夫人》在日本由不同出版社、在不同年代,又有了不同版本,台日兩地文學家與學者的評介推薦不絕如縷,可見《陳夫人》是一本質量俱佳的小說。可惜隨著歲月消逝,日文版在日本也多已絕版。
更遺憾的是戰後由於政權更迭,這本以日文忠實反應台灣在日治時期日台兩族人民間互動的小說,只因得了當時台灣總督府頒贈的「大東亞文學獎」,竟被誣名化為附和二戰時日軍侵略的「皇民文學」,在白色恐怖的戒嚴時代,這本書始終沒有中文版,只在曾受日本教育卻逐漸凋零的台灣知識份子間流傳。
解嚴之後,一方面憲法所明定的出版自由得以實現,另一方面在台灣能直接閱讀日文小說的讀者更少了。翻譯家黃玉燕女士因此受台灣文壇前輩,也就是《台灣文學史綱》作者葉石濤先生所託,將《陳夫人》一書翻譯成中文,由文英社出版。
文英社是以出版學術書籍為主,因此印量有限,流通也不廣。十多年來,很多人經常從書介或推薦中久聞其名,卻又難見其書。黃女士為了傳承文化,於是在經作者女兒同意後,將此一中譯本重新修訂,交給文經社出版。我們心想,這是讀者的福音。既然如此,就不是單純的「出版一本書而已」,而是肩負有傳承的使命。
吳榮斌
譯者序
「愛」能拆毀一切隔斷的牆
從事日本文學翻譯工作,一晃已近三十年,但是翻譯庄司總一的這本長篇小說《陳夫人》,仍是一件想不到的緣遇。
由於這部小說是以日治時代的台灣背景呈現的舞台,所以如今讀起來仍倍覺親切、感動。雖然是出於一位日本作家的創作,但孕育這部作品的泥土、空氣、陽光、人物,全都是來自這一塊土地,把讀者重新帶進當時台灣特殊的時空,與書中的人物、角色一同呼吸、哭笑、掙扎。
這種來自作品直接的感動,是因為作者庄司總一,曾在台灣這塊土地接受小學到中學的教育,他的體驗真實,讓這部小說不是憑想像虛構,而是他真實的記憶與理想,字裡行間都流著庄司總一溫熱的血液、青春時代的憧憬和成長歷程的影子。
我之所以會著手翻譯這部長篇小說,完全是來自前輩作家葉石濤先生的鼓勵,他向我推薦了三本日治時代的優秀長篇小說,分別是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與這本庄司總一《陳夫人》。我在獲得庄司總一長女山本悅子的翻譯許可書後,就著手翻譯本書。
.
本書原文在一九四二年曾得過第一屆大東亞文學獎次獎(首獎從缺),這篇小說是描寫嫁給台南有錢人陳家長男陳清文的日本籍妻子安子,起伏多變的後半輩子。根據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的介紹:
「安子因信仰而與清文結合,不顧父母的反對,一意渡海到了風俗習慣、生活感情等方面,都與日本迥然不同的台灣。安子和這個家族集團保持接觸,想以陳家長媳的身分盡力融入這個集團中。
她的先生清文則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為了自己的理想主義者個性而不容於現實社會,他也看破了要當公務員的念頭,到長老派教會所經營的學校當一名教師。然而,時代的激烈變化卻不讓他有安住之地。
清文之所以放棄進入官界,原因就是成績比他差的多的同班同學,只憑自己是日本人的緣故,就成為他的上司,使他發現了一個無法跨越的鴻溝。
其他像是當清文偶爾穿上台灣服裝,到日本人的教會參加聚會,卻在大門口被趕出來;或有些特權階級為了開設高爾夫球場,竟要把台灣人的墳墓挖出,並對每一個墳墓課上二十圓的遷移費用,像這種事在殖民地是極為平常的現象。
清文和安子的這些煩惱,也就傳給女兒清子了。同學們不叫她『清子桑』(日本同學之間互相稱名),而叫她『陳桑』(日本同學對台灣同學則稱姓),對這一點她就感到極度的自卑感。另外清子對穿上台灣裝出現的父親清文,心裡不禁湧起憤怒般。那麼,作者要對這些問題如何回答呢?
『--愛,安子在心裡小聲地說。』作者庄司總一想用這句話替代回答。只要殖民地體制不改變,他們會永遠被鎖在裡面。只有在心裡小聲地說出「愛」,這才是無論作者、身為主角的清文和安子,都可以做到的事。」
.
就如大家的第一印象,二戰時《陳夫人》得到的「大東亞文學獎」,與「大東亞共榮圈」的戰時宣傳,當然脫不了關係,因此本書很自然被捲入「皇民文學」的範疇裡;再加上作者庄司總一是日本人,因此戰後在台灣飽受輕視,往往祇在評論家批判行文時提及作者、書名,但書的實際內容則煙沒不見。但作家楊照在評論本書時則說:
「讀遲來的《陳夫人》中譯本,我們大概會驚訝於這部小說裡,對於殖民同化前途、皇民歸順宣傳上一廂情願的部分,如此之少。庄司總一藉由一個私奔嫁入台灣富豪大戶人家的日本女子的經歷,寫出了在殖民處境裡台灣人種種不同的反應。
受到自然主義寫實精神的規範,庄司總一其實並沒有在行文中擅加太多明白的價值判斷,對自己身為日本人、身為殖民者的偏見固然無法真正自覺地排除,卻也謹守分寸不太過份干擾情節、人物的自主發展。」
文學評論家彭瑞金也指出:「這部作品裡的主角陳清文,既是學有所成的留學生,又是家世不俗的世家子弟,女主角安子,卻是日本的鄉下女子。不過,作者卻讓安子以德以容,逐一征服了陳家所有的成員,她由局外人逐漸成為家族穩定的力量,成為家族的重心。
即使她的丈夫陳清文,不論學識、地位、家世、財富、容貌……都較她優越、優秀,結果卻出現清文向安子的文化認同,而不是安子向陳家文化認同。或許它誠實地說明了當時的日本文化強勢現象,不僅僅陳家的男人會愛上面貌並不姣美的日本女子,或者說台灣舊家族的教養的確有其陳腐、落伍、卑劣的質素,不若日本民間生活文化貼切生活現實。
譬如說,安子貴為陳家的大少奶奶,處理生活衣食起居的能力,就要優於她所有的妯娌,必要時,她也能下田勞動,這大概就是舊世家文化中一旦成為世家媳婦便喪失的能力。」
.
最後要向讀者們說明的是,葉石濤先生推薦的三本日文長篇小說: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與這本庄司總一《陳夫人》,我都已經翻譯完成。
會將《陳夫人》這本書交給文經社出版,除了是因本書能從殖民、原住民、性別、民族等各方面切入,包括了日治時期文學家書寫的所有議題,深深影響了後來的台灣文學,在文學史上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另外書中所提到基督徒的「愛」,更是其他日治時代長篇小說裡罕見的題材。
文經社之前已出版過《孤女尋親記》、《苦兒流浪記》與《小天使海蒂》等飽涵基督大愛的西洋經典長篇小說,因此我放心的將《陳夫人》交給他們處理。我深信:「愛」是串聯我與作者、出版者與讀者間的唯一橋樑。
黃玉燕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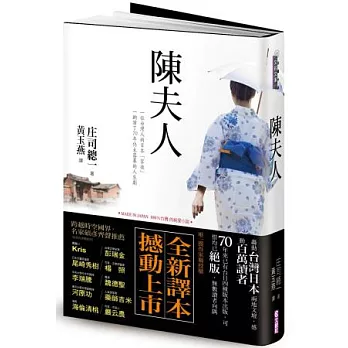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