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趟夜間之旅開始
星光滿天的夜空
透著無與倫比的靜謐。
我家後院天文臺的涼爽寂靜有項特色,那就是微弱而粗嘎的機械運轉嗡嗡聲,像一群鬱悶的蜜蜂,在天文望遠鏡轉動馬達,找尋新星時,輕輕飄送。不過,我聽到的不只有這種嗡嗡聲,還有乾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但這並不是風的傑作。夜行動物讓樹林充滿生氣,包括老鼠、鹿、浣熊、臭鼬、狐狸和貓頭鷹,我全都親眼見過。長時間處於黑暗中,讓我的雙眼能敏銳察覺周遭的動靜,而我的鼻子習慣了鄉間清淨的空氣,即使是一絲異味也能發覺。
在我的頭頂上是一片星空,包含成千上萬顆星星。傍晚天氣晴朗,而現在夜已深沉,鄰人皆已入睡,燈火也已熄滅,黑暗就像一頭困獸。在數小時之前,南方天際還有微弱的白光,那其實是光害,從地方屋舍、街燈、城市等處流洩而出,不過到了現在,即使光害也沉寂了下來,只剩下深沉的夜,和無垠的宇宙及其中的種種奧秘。但我漸漸發覺,真正的奧秘,其實存在於我的內心。
八歲那年,我第一次透過望遠鏡看天空。在我像同輩許多人一樣,進入狂亂的青春期之後,是天文學支持著我。在美國,大家都是在科技與社會變動中成長,我和多數同儕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是在夜間多了項活動,那就是觀星。望遠鏡對我而言就像鞋子一樣平常,也一樣實用,可說是必需品。我就這樣度過了高中時期,進了大學後更是依然故我,但高中時期很難解釋自己為何懷抱這股熱情。
後來我突然放棄了。
成年之後,我大多刻意忽視想抬頭看天空的衝動,只是不斷向前看,如同受到重力吸引一般,僅專注於事業、家庭、子女和貸款。我發現渺小生物的生活軌跡,和大型天體的運行一樣驚人,也適用相同法則,會一直繼續,直到某天突然中斷。
而打斷我的,是某天電視上播出的畫面。我無法說明那個九月清晨發生的事件,但我知道:在仰望星空時,我得到了慰藉。
自人類出現以來,星辰幾乎沒有改變過,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是過去而非現在的星星。這些天體散發的光芒要傳送到地球,所需的時間並不一致,在瞬間散發的光芒早已向我們傳送,只是我們尚未見到。當然,這片永恆不變的星空,其實只是假象,就像安全的假象,或是仔細規劃和估量生活後,認為日子就會過得一如預期一樣,但心想並不一定會事成。在人類大幅改變時,星星也確實會有小幅度的變化。
二○○一年秋季,我輾轉重拾起年輕時的嗜好。一切開始於一趟夜間之旅。那晚我和兩名稚女一同出遊,她們年輕的雙眼流露出一種特有的新鮮感,我的大女兒首先揭開了序幕。
「爸爸,你看天空好晴朗喔。」
當時我正要把車停進車庫裡,車上滿是沉重的購物袋,全是當晚採購的戰利品,我和往常一樣,迅速把車開進車庫,懶得抬頭看一眼。何必抬頭看呢?但是為了某種原因,我還是減緩了車速,搖下車窗,清新的空氣湧入,我也感受到那種純然的澄淨。
當晚我和兩個女兒躺在草坪上,指著天空向她們解說各個星座,沒想到我居然還記得這些星座的輪廓和名稱。那年秋天,我和其他人一樣,滿心困惑憤怒,為了子女和國家憂心,在曼哈頓工作的同社區朋友和鄰居訴說的種種事情,讓我迷惘心煩。但是那天晚上,在凝望著銀河系群星時,我頓時領悟,我們都是這片星空的一份子,在此之前,我從未瞭解這一點。
在我居住的康乃迪克州,十月的天空通常最晴朗,隨著夜幕逐漸低垂,秋季星空閃著微光登上舞台。夏天的燠熱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涼爽的空氣,從加拿大吹送至康州,像一股冷冽的山泉流過肌膚,洗去一切煩雜,讓感覺更敏銳。樹葉變色,雲朵轉厚,像一團團棉球,夜裡各個星座在我頭上的天空閃爍,像守衛著變幻的哨兵。
和女兒一起觀星的那晚,天鵝座(Cygnus),也就是北十字星(Northern Cross),迎接著我的歸來。十字的頭尾,是明亮的超巨星天津四(Deneb)及美麗的雙子星輦道增七(Albireo),這兩顆星高掛天空,建構出我重返天文界的入口。天鷹座(Aquila)中的牛郎星(Altair)位於天津四南方,是北十字星中最明亮的一顆星,也是夜空中亮度排名第十九名的星星。天鷹座可說是天鵝座的縮小版,這隻鷹勉強張開雙翅,如果不是因為牛郎星本身亮度驚人,甚至更勝天津四,天鷹座可能幾乎沒有人注意,只除了一件事,就是牛郎星是指示織女星(Vega)所在位置的線索。
織女星是夏、秋夜空中最明亮的一顆星,在西邊天際主導著退場儀式。織女星也是組成V字大裂口的三顆星之一,與天津四分佔V字兩臂頂端,而牛郎星則獨自位於V字尖端,像個在監視的警察。
這便是我年少時著名的夏季大三角。
我在1970年代初期長大成人,青春期的我以這個熟悉的標記為路標,在夜空中遨遊。就像將軍策略性佔領城鎮、橋樑一般,從織女一號(Vega I)出發,直至天琴座(Lyra)中的小平行四邊形,而有兩個目標就在這裡,那就是環狀星雲(Ring Nebula)和著名的雙星(double-double)。
環狀星雲是宇宙暴力的證明。地球上我們周遭的環境,大多是在暴力下成形,天體的情況也是一樣。地殼碎片組成星雲小型透明的光環,環繞恆星所在地區,殘留著恆星生前的記憶。許久以前,環狀星雲中央的恆星開始發出藍光,在苟延殘喘之際,星體內部燃燒更多氫氣,氫氣減少導致星體外部膨脹,使得一層層氣體脫離,就像佛羅里達州的渡假遊客一件件除去身上的衣服,直到所有氣體層和氫氣消失,徒留一幅駭人的景象:一圈星雲,就像雪茄熄滅前餘留的氤氳煙霧,昭示著許久以前,曾有一顆恆星在這裡發光發熱。
不過天琴座裡並不全是這種陰鬱景象。每年夏、秋夜裡,全球各地的觀星族都可透過望遠鏡,欣賞環狀星雲北方的宇宙之舞,演出的主角是雙星,也就是聚星系統(multiple star system),不僅能騙過你的眼睛一、兩次,而是三次。以肉眼觀看,這顆星似乎和其他微明的星星一樣,但透過雙筒望遠鏡,就會發現這顆星其實是雙子星,而如果提高望遠鏡倍率,便能看清真正的關鍵:這顆星其實包含了兩個小型的雙星系統,在觀星人眼中,就像是珠寶商黑色天鵝絨墊上的閃亮鑽石。這些雙星系統便是雙子星,兩顆星踏著複雜漫長的華爾茲舞步,相互環繞,透過雙筒或天文望遠鏡,最能看清這曼妙的舞姿。不過,在那個十月夜裡,我抬頭仰望天空時卻發現,我根本沒有望遠鏡。
二十五年前,我為了籌措大學某個學期的學費,賣掉了十幾歲時擁有的那架望遠鏡。那架綠色的發現者(Discoverer)60釐米孔徑折射望遠鏡,是席爾斯(Sears)百貨裡最高檔的貨色,是我父親在我12歲那年買給我的禮物。對他來說,這份禮不但昂貴,無疑也十分愚蠢,身為工模具製造工人,這個所費不貲的儀器除了代表對家人的愛以外,在他眼中根本毫無用處。
他問我:「你不是已經有一架望遠鏡了嗎?」
是沒錯啦,不過那是便宜貨。
「現在你又想買第二架?」
他皺起眉頭,不能理解為什麼需要兩個同樣的東西。他在大蕭條時期的肯塔基州長大,小時候只有一套西裝、一條領帶、一雙上學穿的鞋和一雙做活兒穿的鞋,還有幾件工作褲和下田穿的衣服;顯然天文望遠鏡是不必要的奢侈品。如果我要的是小工具或甚至棒球手套,他都能理解,但是天文望遠鏡有什麼用?
「爸,我真的需要,這架的倍率更高。」
倍率,真是一項誘人的因素。
「用這架我才能看到更多星星。」
我父親用大蕭條時代長大的人常用的衡量方法,慢慢考慮這件事,評估整件事的利弊得失。可是我實在沒耐心;我知道如果想快點得到另一架望遠鏡,就必須儘快解決這件事,也就是說,我得求助於母親。
要找到她並不難,她通常都在她的「辦公室」裡,她都是這麼稱她的臥房。母親大多時候都待在臥房裡,坐在床上用張小桌子寫作,那張小桌子看起來就像是馬拉放在浴缸邊的小辦公桌(譯註:馬拉(Jean Paul Marat)是法國大革命領導人之一,因為身患疾病,所以一天中常有數小時躺在浴缸裡,邊接受治療邊處理公務。)我母親很少下床,這倒不是因為她沒辦法下床,根據我猜測,應該是她太投入內心的世界,以致於對臥房外的俗世不感興趣。她的許多朋友都對這點非常好奇,其中包括她的醫生;這位醫生身材高大壯碩,十年來每個月和我母親會診兩次。他很喜歡和我母親對話,兩個人常常就這樣陷入神秘之中。
她說:「他是獅子座,個性很古怪,問題很多。」
我母親是占星學家,床頭桌邊堆了一落筆記本,裡頭盡是她寫的短文和文章,還有她幫朋友家人算命的結果,每個人的生日都清楚標示,繪製成命盤,裡頭的符號我都認得,是古代記錄行星及其在黃道面運轉情形的速記符號,不過,我母親主要是依據她的想像建構黃道面,行星的位置大多和天文學家指出的位置不同,我常常和母親爭論這點。
「媽,木星不在牡羊座,是在巨蟹座啦,你要看天空。」
「我有啊。」
她輕叩著一本藍色書皮的書,書名是《美國曆書》(The American Ephemeris),裡頭記載著占星圖表,她便是根據這些資料幫孩子算命。她宣稱知道孩子的命運,但或許那只是所有家長對孩子所具有的直覺,是一種奇特的預知能力。
「你想要某樣東西,對吧?」
就算不是算命師也看得出這點。
我說:「我想要一架更好的望遠鏡。」
「喔?你知道嗎……」
我想她接下來要講的,一定是她常說的那句名言,和有沒有錢無關,而是和占星學有關。幾個世紀以來,天文學家與占星學家之間的戰火從未平息,天文學家藉由指出占星學內容不正確,以證明科學的真實性;這場戰役一直持續至今,在我家最明顯。
「……占星學家是第一批天文學家,就是迦勒底人(Chaldean)。」
「媽,要科學不要迷信。」
她微微笑了笑說:「無論如何,星星永遠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從你的命盤就知道,所以我也只能接受這點了。我會和你爸說的。」
幾個星期後,新望遠鏡來了,馬上架在我家最顯眼的地方,也就是飯廳。大多數人的飯廳,都是以全家福照片或畫作佈置,但我的家人卻是在我所能買到最巨大的一張月球圖凝視下用餐,這幅圖直徑將近1.8公尺長,巧妙地釘在兩扇窗之間。
我的父母不太在意傳統,甚至似乎還滿喜歡這張圖帶來的詭異感。除此之外,月球也是當紅話題,僅僅幾個月前,我還和家人一起熬夜,看電視上轉播阿姆斯壯的消息,畫面全是以拙劣的銀板照相法記錄下的黑白影像,拍攝他爬下登月小艇的樣子。現在,月球已成為我們家的重心。
我不確定像我父親這麼實際的人,對於月球這個話題有什麼看法。或許他知道我們國家正在探索新領域,並對此覺得寬慰,也或許與月球這個古老世界相關的種種怪誕隱喻,像是「做春秋大夢」(Wishing on the moon)、「空中大餅」、「讓月光迷昏了頭」(Moon swoon) 等,讓他覺得惴惴不安。每到週末,他總會想辦法要我和他一起進行地下室工程,全面整修我家樓下的空間,改建成《妙家庭》(Brady Bunch)經典70年代版的起居室,木質壁板、同質地的吧檯、凳子及粗毛呢地氈,很適合舉行派對,只不過,我們家根本很少玩樂。
他說:「要不要來幫我鋪席特洛克(Sheetrock)石膏板?」
「抱歉,老爸,我要去天文館。」
每個週末,我都跑去運動或到本地的博物館,而不願意從事對生活有用的事務,如換機油或學做木工。我下午最常流連在博物館裡,首先,這裡有播放天文影片,雖然幾個月來每週播放的影片都相同,但我毫不在意。影片內容是星象解說,隨著半圓形屋頂的燈光逐漸轉暗,我所居住的賓州荷蘭村的地景映射在紙板做成的假地平線上,我就是在這裡練習辨認星座。這座天文館對我而言就像家一樣。
晚間,看完了天文影片,我會拿出望遠鏡觀星,直到父母逼我進屋,這時候通常都已經過了11點,在週末還會拖得更晚。上了高中,我常熬夜到很晚,有時甚至到破曉時分,然後才拖著腳步去上排在第一堂的拉丁文課,趁機補眠。
當然,我的老師都知道我熱愛天文學,常在晚上觀星,記錄木星的天氣模式,有幾位老師會因此饒過我。多數人都認為,觀星雖然是個奇怪的嗜好,但也沒有壞處,不過有些人卻覺得這是不切實際的人所做的消遣,或許還證實了我父親最大的夢魘,那就是占星學和天文學有關,確實屬於同一門學科,而我會一輩子在群星之間追求浪漫,終日沉浸在幻想中。
甚至連我的朋友也有相同看法,到了週末情況更糟,接踵而來的派對常常持續到深夜,我常以天文學為由拒絕參加,就像在保護某個秘密,不想讓愛吃醋的女友發現。只要夜空晴朗,我就不想出去,其他人因此開始嘲弄。
「你都在外面看什麼啊?在偷看辣妹嗎?」
而如果我據實以告,結果會比我想像得還要荒謬。我告訴他們,我在瞭解夜空,這種說法必定會引來一陣狂笑。
「你是說姊妹會的那些女生吧,她們就住在你家後面。」
那是本地的一所大學。
「講得好像你真的和那些辣妹一起整晚看星星一樣。」
到底有沒有人相信我,還是只是因為我的嗜好很好笑,所以他們能夠容忍,我永遠不得而知。但只要我保有這個嗜好,便始終是鄰里間的名人,就像個個性古怪的大叔,怪雖怪卻懂得投球。
「好啊,宇宙先生,那你告訴我阿波羅號的旗子在哪裡?」
這是常見的誤解。不懂天文學的人常以為即使用最小的儀器,也能有驚人的收穫;只花區區幾百美元,就能看到太空人,觀察翻滾中小行星的地表,或探進即使全世界最大的望遠鏡也難以看到的區域。
這當然不是事實。
我告訴他們:「我沒辦法。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阿波羅在哪裡著陸。」
當然,我也是在吹牛。在1970年,我可以將頭幾次阿波羅任務著陸的區域,縮小到方圓80公里的範圍內,就像是從太空中找出曼哈頓區,但卻無法實際看到時代廣場上的某棟建築物。
在天文界,大小確實非常重要。所有業餘天文學家及多數專業天文學家,心裡不斷妥協,在現有儀器和想要儀器之間取捨。我從小就穩坐在這個陣營裡:擁有不再夢寐以求的東西,想要無法擁有的東西。在誘惑之下,我做了一點改變,取得了想要的東西:我想要的愈來愈多,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開始和擁有更大型望遠鏡的人交朋友,在天文臺當義工,參加學術會議,總而言之,我想盡辦法接觸更大型的儀器。
而今,數十年過後,我和女兒一起仰望夜空,試著解釋環狀星雲,而不只是將望遠鏡對準環狀星雲,由著她們自己去觀察,我發現自己仍然焦急不安,就像是個被人拋棄的女孩子,仍在為十年前的陳年舊事而氣惱。我童年時期的望遠鏡,被一名伐木工人買走,他住在明尼蘇達州北部,在該州最暗的地區擁有一棟小屋,就位在安大略省南邊,接近邊界水域(Boundary Waters),而他想要一架望遠鏡(我的望遠鏡),我在5分鐘之內漲價三次,希望他能打消念頭。
不過,他並沒有打退堂鼓。
這個人用厚厚一疊鈔票,買走了我的過去,包括我在接目鏡上度過的無數時光,以及其他一切。或許是因為出於絕望,我決定把手上所有和天文相關的東西都送給他,包括書籍、舊而珍貴的星象圖、濾光鏡、測量儀、多的接目鏡等配件工具,而透過這次徹底的金融交易,我進入了新的境界,來到回憶的國度。孑然一身,不再受物慾所苦。
將近25年來,我始終抱持著這種想法。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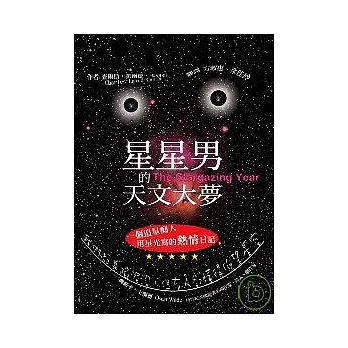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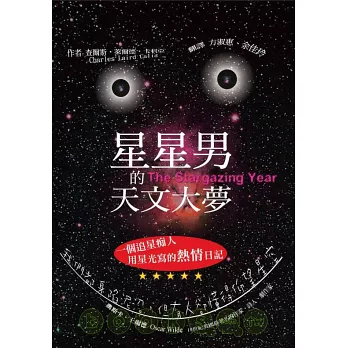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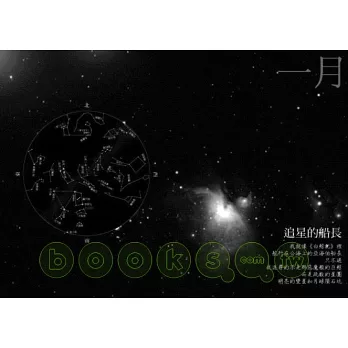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