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明在腦的創意中向前邁進
科學家在最近這一百年來的成就非凡是毋庸置疑的,它讓我們和五百年前地理大發現後走向現代化的人,面對的是天差地別的世界。廿一世紀的我們可以飛向天際,可以步上月球,可以將探索車送到火星,也可以利用哈伯望遠鏡看到最遙遠的星雲變動;在奈米的新天地中,我們可以製造出比毛髮更細小百倍的機件,而它們的運作能量可以被應用到我們用肉眼看不到的機械平台上,對機器和智慧兩個傳統的概念,給予新的含義。
在生命科學的領域,人類基因體定序完成在二○○三年,距DNA雙螺旋模式的提出才不過五十年,其相關領域的研發工作帶動整個生醫研究的突飛猛進,不但對疾病的診斷與治療有相當不一樣的概念架構,對人生命品質的管理與提升也有了全新的詮釋。最具體的成果:五百年前,人類壽命不超過五十歲,現在在科學文明發達的國家平均已經可以達到七十五歲(女性比男性多出四至五歲),但是在沒有科學文明的落後地區,人的平均壽命則仍停留在五十歲左右,再次印證了一項事實,即科學所帶來的知識,已經可以超越自然生態中的生物限制!五百年前的人所想像的神仙魔力也不過是飛天、下海、入土、隱身、縮地神功等,對現代人而言,簡直是雕蟲小技的能耐而已。
那千里眼、順風耳呢?哈!更是微不足道!看過最新版的Google Earth嗎?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影像,都可以即時顯現在我眼前的電腦螢幕上,尤其在網路的超級聯結下,世界各地的各類知識資料庫,也能在彈指之間即時進入遊覽與觀賞。透過網路以及更有效率的儲存與搜尋引擎,人人都可以變成為時空行者,隨時隨地遊走在歷史的片段之中。隨著電訊傳播技術的革新,人們手中的掌中機代表的是行動辦公室、行動教室、行動電影院、行動遊樂園、行動商場及百貨公司。這個資訊化社會所呈現的種種前所未見的能量是很驚人的,它們正全面的在改變人們生活的方式,並且也重新界定新社會文明的藍圖。
也許我們就會開始感到不安了。為什麼在整個科技文明進化這麼快的時候,我們在心智科學的進展卻如此緩慢呢?尤其是人們到現在對學習的看法和五百年前的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仍然是以外顯的行為當作學習的指標,然後千年來的教學方式也是一成不變,總是我教、你學,我說、你背,我出題、你作答,然後根據你記憶的程度打成績,老師對學生一視同仁,卻一再忽略他們之間心智能量及學習型態的個別差異。而且,研究學習的教育學者總是不願意打開人腦裡的黑盒子,好像我們真的可以忽略那個錯綜複雜的神經體系,而達到有效教和學的目的。其實,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已經有效的把行為主義所加的桎梏解開,而且也在解開行為主義迷思的過程中,發現了腦的運作方式和形成認知的條件是息息相關的。科學家終於願意面對那個黑盒子,也有信心把它打開,然後重新思考腦和學習之間的關聯!
當然,要釐清腦和認知與學習的關係,需要四個領域的知識,是神經科學家在分子層次的發現所累積的新知識,使我們對傳遞物質如何在生化的變異中影響學習有很多新的看法;第二是神經生長的生理條件,尤其是大腦皮質的神經分叉是如何形成各種不同的學習型態,這其中,有關灰質和白質的功能區辨如何影響短、長期記憶之建立等;第三,先天基因的藍圖和後天環境變化的交互作用,有哪些普遍性原則?有哪些特殊性條件?對神經生長及聯結的可塑性有何規範?最後,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平台上,由於腦造影技術的精進,以及電生理測量在時間解析度的提升,使得認知作業對應在腦中運作歷程的時、空表現,有更細膩而精確的呈現,可以進一步讓我們了解學習在腦中的迴路如何完成,以及學習失敗的成因。
這是一門跨領域的新興科學,對人類心智發展的研究會有巨大的貢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特地成立了四個新的國家型學習研究中心,就是針對腦與心智的結合而設的,因此,每一個中心都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醫學院做其後盾,為的就是要把認知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和學習異常的臨床診斷與治療結合在一齊,推動心智與腦的教育研究計畫。目前,英國的幾個著名大學和法國的高等研究院也都成立了類似的研究中心,而且以種種獎勵的方式,鼓勵在職教師進修。美國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率先成立Brain/Mind Education的研究所,培養高級研發人才,並且在去年五月為在職老師及教育行政人員開了一個為期一週的短期研習課程,原先只規劃三百人的座位,竟然來了將近一千人,讓波士頓附近的旅館統統擠爆了!這是教育界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學習熱潮。
《樂在學習的腦》一書的作者之一布雷克摩爾(Sarah-Jayne Blakemore)就是哈佛大學短期研習班的講師之一,這本書是她上課的入門教科書,對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方法和內容都有相當深入淺出的介紹,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尤其對只修過傳統心理學導論的老師們,更是一本非常“user friendly”的書,值得全台灣的教師們人手一冊,仔細體會人腦的奧秘,並清楚理解神經可塑性的含義。教育改革是時代變遷的必然產物,但所有的改革方案必須根據有證據支持(evidence-based)的理論,千萬不要再淪為個人意見的口號。這才是現代科學文明的精神所在!
推薦者簡介
曾志朗教授,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心理學博士,曾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九九○年返國,先後擔任中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陽明大學副校長、校長,教育部長及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等職。一九九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二○○四年當選美國心理協會(APS)院士。著有《用心動腦話科學》、《人人都是科學人》、《科學向腦看》等書。
試讀大腦科學破除了我們對學習的直覺
若說教育研究沒有也無法從教育界本身的資源和科學思考中,提出最好的方法來解決教育上的議題,這樣的暗示可能有點危險。若是問到神經科學能夠提供教育什麼訊息時,時常被提到的就是,思考大腦科學如何挑戰在學習與教學上一些習以為常的看法。
大腦會「背著你」運作
馬上想到的第一個主題,也就是沒有意識的學習,這個主題會在本書後頭提到。
你知道嗎?即便在你沒有集中注意力,或根本沒有留意到某個訊息的情況下,大腦仍舊可以獲取該訊息。大腦這種「背著人」做事的天分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且已經對教學理論造成影響。我們將會在第10章探討大腦這種內隱的(implicitly)訊息處理的能力。
老化的腦還是能學
不久之前,認為成年人的大腦是無法改變的看法仍很普遍。腦科學家過去有著一個強烈的假設,認為在出生後的幾年間,大腦便具備了一生所需的腦細胞,成年之後就開始快速喪失大腦細胞,並且在學習、記憶和表現上逐漸退化。然而,開始有研究結果告訴我們這種看法太悲觀;成年人的大腦是很有彈性的,最起碼在某些區域內,例如海馬迴(hippocampus),會長出新細胞和新連結。儘管處理新訊息的效率會隨年齡的增長而越來越差,但是學習是不受年齡限制的。
大腦的可塑性(plasticity)─持續適應環境變化的能力─完全看大腦的使用多寡。可塑性的相關研究告訴我們,大腦設定好因應人生全程的學習和適應環境;成年之後重新再接受教育是可行的,而且非常值得一試。另一方面,研究上也告訴我們,從生理的角度來看,開始接受正式教育的時間並沒有越早越好的必要性;相反的,可以將起步晚,重新思考為剛好及時配合大腦和認知的發展。當然,老化的大腦會變得比較缺乏適應的能力;且隨著人們的舊經驗越來越多,就更需要費時學習新事物了。
認知心理學怎麼說?
跨學科領域之間的交流,需要一個中介者以防某種學科領域佔有特別的優勢。當大腦科學與教育展開交流時,認知心理學理所當然的扮演了這個角色。我們相信大腦科學能夠透過認知心理學更快速的對教學與學習的相關研究產生影響。
雖然心理學是大腦科學一個重要的中介者,同時心理學本身也能對教育有所啟發;我們強烈感受到,現在是探索大腦科學對教育意涵的大好時機。布魯爾(John Bruer)是最常直言不諱批評大腦研究在教育上的應用尚未成熟的人,他曾經說過,神經科學與教育之間的鴻溝得要由認知心理學來填補。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們必然會再三提到認知心理學的相關實驗結果。
儘管如此,本書的目標是探索大腦的世界。所以我們會試著把焦點放在大腦研究的結果上,並且將這些研究結果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作連結。
我們非常瞭解此書無法將所有與學習相關的大腦科學做詳盡的回顧─因為我們無法將所有的東西都納入書中。因此,在每一章的內容裡,我們專挑一些該領域最具潛力、有發展性的研究。你會發現某些實驗要用好幾頁的篇幅描述,而其他同樣重要的研究卻只有簡短的提到,或根本沒有提起。這只是因為我們必須做選擇,而且我們認為讀者會對那些還沒有被廣泛報導的新近實驗較感興趣。當然,我們也會常常提到自己實驗室或周遭同事所做的研究成果。
改造大腦景觀
大腦,就像身軀一樣,每個人不盡相同,但也幾乎沒有什麼是不能改善或改變的。在我們的周遭世界中,有許多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後天的培養如何促使先天的本質得以發揮或增進。馬上可以聯想到的幾個例子,像是配戴眼鏡來改善視力、添加營養以促進生長,還有牙齒矯正醫師可以矯正不整齊的牙齒。大腦也同樣可以透過後天的培養而獲得增進;只要牙齒矯正醫師能夠改善你的牙齒,教師就能夠改善你的大腦。
教育可以被視為一種大腦「造景」的工作,就某種意義來說教師就像園丁。當然,園丁無法在缺乏適當土壤的情況下培育玫瑰;然而,一個好的園丁要能讓現有的植物得到更好的培育。如同園藝工作般,園丁對於什麼是最令人喜愛的植物總有著不同的想法,並且還會隨著文化的差異和流行而改變。總而言之,園丁的工作還包括將已具備的條件發揮到最佳的狀態,以及可能創造出令人驚嘆的、有影響力的新設計。在本書中我們會不斷的看到用這個比喻來描述透過教學與學習塑造大腦是什麼意思。
大腦如何運作?
大腦是全世界最複雜的系統之一,儘管我們對大腦有越來越多的認識,但要完全瞭解它的運作卻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這還是一個謎團,有待全世界幾千個科學家解開。不過,我們確實知道大腦的部分真相(請見圖1.5)。
成人的腦大約三磅重(1.4公斤),約有一千億(1011)個腦細胞(或稱神經元〔neuron〕─請見圖1.6),這是個龐大的數目。神經元以或短或長的纖維與其他神經元聯繫,大腦內的細胞間則有將近1015個連結。一千億個細胞如此龐大的數量,是很難想像的。一百萬是一千的一千倍,舉例來說,就像是一個非常大的城市所擁有的人口數。而十億則是一千的一百萬倍。因此,人類大腦內神經連結的數量比起將近六十億的全球人口總數還要多上許多。
在探討一些相關功能,像是「恐懼經驗」、「字詞學習」、「加法的運算」或「心像運動」,我們從來沒有提到個體的神經細胞。然而,這些都是大腦組織區塊內百萬神經元所負責的認知功能。
神經元是如何做這些事情的呢?如同體內其他的細胞,神經元的運作像是個小小的電池般。細胞內和細胞外具有不同的電壓(將近0.1伏特的差異),細胞內呈現微弱的負壓。一旦神經元激發便會產生脈衝,稱之為動作電位(action potential)。此時,鈉離子會穿過細胞膜的細孔而湧入,快速的將細胞膜的電壓改變。這使得化學物質(又稱為神經傳導物〔neurotransmitters〕)從一個神經元的軸突終端釋放出來。這些化學物質會穿透突觸間隙(synaptic gap)並且由另一個神經元樹突上的受器(receptors)所接收。如圖1.8所示。這就是大腦溝通所使用的「語言」,而動作電位使得大腦產生「活動」。
幾乎所有的感官訊息都會從一側的身體傳送到對側的大腦。所以當你的左手臂被觸碰時,這個訊息會傳到右腦做處理;當你看到右手邊的物體時,這個訊息會被送到左側的視覺皮質區(visual cortex)進行處理。除了嗅覺以外,其他所有的感官皆是以如此的方式處理訊息,就連動作也是如此─右腦的運動皮質區掌控著左手臂的動作。然而並非腦中所有的結構都以這樣的方式處理訊息,例如小腦就是控制同一側身體的動作,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完全瞭解其中的原因。
我們如何研究大腦?
我們在此介紹一下幾種用來研究大腦的技術,倘若你想知道更多細節,你可以參考本書的〈附錄一:研究大腦使用的工具〉,我們針對目前用來研究大腦的不同技術有更詳細的描述。
現今已經有許多工具可以用來研究大腦。電生理(electrophysiology)的研究是用來記錄動物腦中單一神經元在進行某項作業時的活動。這項技術可以直接測量到神經活動。但在人類身上測量神經活動是困難的,而且紀錄人腦神經元活動(例如進行頭顱切開手術時)的研究也非常少。然而,這些研究只透過「接觸」微小且特定的大腦表層,便能夠將記憶和動作相關的細節表露無遺,實在令人讚嘆。
幸運的是,有許多非侵入性的方式可以用來觀測在人類特定腦區中,成千上萬個與某項行為有關且連結在一起的神經元,在大腦內所產生的電活動。腦電波儀(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和腦磁波儀(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是測量腦中電和磁性的活動,只要將電極放在頭顱上便可測量到。
血流量也是大腦活動的一個指標,被應用在大腦造影技術上。血液會流向神經活動頻繁的大腦區域,以補充氧氣和葡萄糖。正子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和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則是透過特殊的大腦掃描機器偵測血流的變化。
神經心理學是研究大腦損傷之後在行為上所造成的後果,因此可以找出特定腦區正常的功能是什麼。現在又有一種暫時阻斷大腦功能的技術,稱為穿顱磁刺激術(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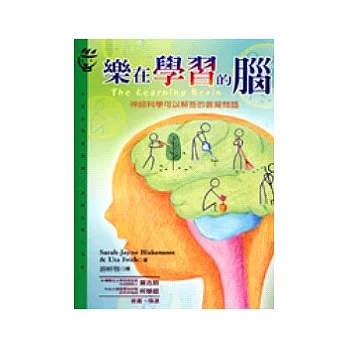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