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1
央卓小姐原邀請寫序的並非我。
一些藏傳佛教信徒每當出版有關西藏議題的書籍時,第一個總是先想到請達賴喇嘛尊者賜序或贈言,希望獲得尊者無上的祝福與加持,以表示對尊者的虔信之心,央卓小姐亦是抱持同樣的想法。但在基金會尚未將她的訊息轉達到尊者私人辦公室前,她改變心意,轉而請我寫序。
原先懷著若能獲得尊者賜序,將是無比光榮想法的她說:「請尊者為我這樣微不足道的小小人物寫序,深思後十分汗顏,尊者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應佔用他老人家寶貴的時間。」這是她為尊者設想的一份心意。
認識央卓已屆十年,她擁有非常豐富的西藏常識與知識,包括西藏佛學。想起她學藏文的因緣也是妙不可言。她敬重的一些西藏法師雖學富五車,辯經無礙,但當她有次發問一個藏文的拼音時,每位法師竟拼出不同的組合,更令她訝異的是沒有一個是正確的,這個發現把她嚇壞了。於是為了「拯救西藏文化」大業,曾為老師的她發願:「我要學好藏文,將來教育西藏下一代。」
於是她進入寺院開始學習,經過數年的埋頭苦學,終於累積了豐盛的基礎。尚未教育西藏下一代,她反倒在台灣開設藏文班,教授台灣人藏文,積極編寫藏文教材,並以此為終生使命。找到一生的志業,自是沉浸在樂趣無窮的境界中。
央卓小姐天性有一股幽默感,愛發問及辯論,更喜愛開玩笑,與西藏人的個性十分相契,難怪她能結交到眾多的藏人好友。回顧她這十年往返流亡社區與寺院的生活,可說精彩無比,引生諸多有趣的情節;一般人覺得理所當然、芝麻綠豆小事,她總能發現其中的樂趣,一碰到問題,她便追查到底,不清楚來龍去脈絕不罷休。她用這種做學問的研究精神,將所學、所看、所聽、所體會的全用筆記錄下來,我想更會深深地刻在她心底。
對於任何一個為傳揚西藏文化或宣揚西藏精神的人來說,都是西藏人的好朋友,我樂見所有為西藏傳達聲音的管道在台灣出現。以前台灣社會對藏傳佛教或是對西藏總存諸多錯謬印象,那是由於昔日資訊不發達。現今藏傳佛教在台灣深耕,來往印度流亡社區的台灣人也越來越多,台藏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密,如同達賴喇嘛尊者所說:「唯有了解,才能合作,唯有了解,才有寬容。」
今日央卓將她的西藏記錄,集結出版,她希望台灣人看到真實的西藏寺院生活,另一種出家人的修行方式,另一種文化風情。全書以她一貫幽默口吻及流暢的文筆,寫來生動活潑,妙趣橫生,對想了解西藏風俗文化、寺院生活的讀者來說,可衍生讀書的無比樂趣與收穫。
有時與她談起一些瑣碎小事,原無吸引人之處,但經她細細解說,竟得到其中意趣。她有天生的說故事本領,能夠帶領聽者走入故事情節,彷彿親臨其境。如「夜半驚魂記」這篇文章,寫的是她第一次碰到印度竹竿小偷半夜到寺院偷錢財的事,隔天當她轉述給西藏法師聽時,儘管她說得口若懸河,師父們卻氣定神閒完全不當一回事;第二次她又遇到類似的情景,以為又是小偷來了,卻是寺院清查沒有去參加法會的僧眾,只不過這回寺院的老師沒有查到偷懶的學僧,反倒是被一位長髮的台灣女鬼嚇到。這本書中多半是這種有趣又貼切點出西藏人個性的內容,看時總不由得發出會心一笑。
此書不但豐富有趣,央卓在求證上也花了很多功夫,有些遺忘或記錄不詳細的地方,她一定詢問相關的人員,絕不馬虎隨意。有次我接到她的電話,問我西藏男士穿秋巴(藏服)的方法。她不是不了解,只是要一再確認她的認知是無誤的而已。
央卓所寫的是真實的嗎?讀者也許會如此質疑,但對央卓來說,此書絕對是唯一真實,純屬她個人的美好歷程。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董事長:跋熱.達瓦才仁
於2010.9.2 西藏民主日
推薦序2
懷抱著強烈且清淨的利他心的台灣央卓拉,對於西藏佛法及文化有著極大的興趣;且不光是興趣而已,為了進一步了解,央卓實際上也放棄了原有的工作,多年來不顧印度惡劣的生活條件與迥異的風俗習慣,不斷地追尋,雖不時遇到困難,仍更加努力朝她的目標前進。
由於對西藏語文、文化及佛法的強烈希求心,央卓特地來到聖地印度學習。不是只有一次,而是很多次,更特別的是她到南印度的甘丹寺北學院,花了許多時間與我們寺院建立了非常緊密且特別的關係。原本只是對佛法有興趣的她,也開始親自到老師們的跟前,向善知識學習佛法。
首先我想先介紹一下央卓是如何開始與北學院結緣的。
二○○一年時,北學院的桑杰烏竹格西為了改善寺院僧眾的學習與生活條件,也為了將釋尊所教導的珍貴佛法弘揚至國外,在這樣清淨的動機下,他自願率領七位老格西到台灣弘法。剛到台灣時,在語言、生活習慣上遇到極大的困難,因此北學院請求達賴喇嘛基金會的董事長給予幫助,基金會便介紹了對西藏佛法有興趣的央卓給八位老格西。在三個月期間,央卓作為台灣信眾與八位格西之間的溝通橋樑,對於格西們的弘法行程有極大的助益。
那時央卓的藏文程度並不太好,但她仍盡全力地用肢體語言來表達,格西們弘法、修法的行程都在央卓的幫忙下順利完成,對此八位格西都很感激她、讚美她。
二○○一年底,八位格西回到北學院,央卓也一起來到我們的寺院。那時正好是法王達賴喇嘛到北學院來主持大殿的開光大典,央卓也跟著大眾一起聽經,並得到拜見法王的殊勝機會。
從那時起,她對西藏的佛法、文化、詩詞、文法等興趣日增廣大,不光是住在南印度學習,也到北印度等地學習藏文。
北學院在台灣成立了第一個海外的佛學會,央卓也竭盡心力給予各種幫忙,並擔任第一屆的會長。
經過幾年的學習,央卓對藏文的聽說讀寫已能掌握,但她仍不滿意,再度數次來到北學院,並開始五部大論的學習。住在我們學院期間,她拜了不少老師,在這幾位老師的跟前努力學習佛法。
央卓對佛法的學習不僅只於信仰而已,她會去探索其原因,思惟其理由。她不光是聽聞佛法,還會追根究柢其道理。鈍根者不懂思惟,只知純然的相信;而利根者卻會用智慧來仔細思惟觀察,因此像央卓這樣的利根行者,對佛法所生起的信心是極為堅固的。她曾受教於我,對這位特別的學生,我的觀察是:這種如利劍般的思惟模式是央卓天生的個性習氣,而非後天的造作。
西藏人已流亡印度五十年,流亡藏人的各個面相,尤其是各寺院的生活、僧眾的學習狀況,在這本書中都有詳實且清楚的介紹。透過央卓所寫的這本書,對藏傳佛教與西藏文化乃至流亡藏人的性格習慣有興趣者,相信此書如同一扇窗,翻開此書如同開啟瞭解西藏人民生活與價值觀的一扇窗。我相信也希望這本書對於讀者瞭解西藏文化、僧眾教育有著極大的幫助。
以清淨的動機所行的善行,不管是做何事,都是佛法的修行。行善不僅是為了此世,更是為了來生。祈願諸位珍惜暇滿人身,努力培養善根,迅速證得無上的佛果位。
甘丹寺北學院
住持 索南卻佩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推薦序3
諸位讀者:
21世紀的今天,人類越發關注內心的安寧。因此,各個宗教對這個世界負有重要的責任,特別是佛教,對此擁有貢獻與服務的特殊能力。
因為佛教徒能以無數正理之量與科學的方式闡釋一切事物,由此發展出深邃廣大的聽聞與思惟的智慧。使內心自然的產生喜悅、欣羨、自信與利他的慈悲心而呈現出無以言喻的平靜與祥和。
但是,當今世界對於佛法的圓滿大小乘及顯密教法,能全然無誤的聽聞與思惟,並繼承印度那爛陀大學法脈傳承的,除了藏傳佛教在印度的三大寺之外,其他地方是甚為困難的。因此,真心修學佛法的諸賢哲,應特別關注印度三大寺的學習與傳承方式。
本書是有關於個人的經歷,以幽默的文筆、易懂的方式簡略地介紹了三大寺。我祈願這本書能為大眾帶來利益!
色拉寺.伽學院 雪歌仁波切
推薦序4
我並不認識央卓小姐,我認識的是她母親蔡壁文老師,她為人忠厚善良,單憑蔡老師的關係,我就沒有理由拒絕為央卓小姐寫序推薦。但是我對藏傳佛教了解很少,原以為此書涉及藏傳佛法的修持,那我就無法越俎代庖來介紹。經過華滋出版社的解釋和說明,並透過郵寄過來的目錄和多篇文稿內容,我才發現這本書很有看頭。央卓小姐是淡江大學中文系的高材生,她以流利的文筆,紀錄了印度藏傳佛教三大寺院、以及西藏僧侶的生活方式。
我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一位生長在台灣繁華世界的年輕女性,不遠千里迢迢去到印度,較為簡陋的陌生國家,雖然文化、語言、生活習慣都不相同,她卻沒有絲毫厭惡生活上的不便利,相反的,她懂得欣賞學習、用心傾聽、誠意了解,還與藏人生活融成一體,甚至幫助格西弘法,這個女孩實在太特別了。
是什麼原因,讓她對西藏文化產生如許興趣?也許是宿世善法因緣所致。又是什麼力量,讓她能將所見所聞集結成書,那必然是這種文化對她產生了莫大的吸引力!書中,她觀察入微、幽默風趣,深入西藏風俗、藏傳佛教的修持。讀者可以隨著她腳步,進入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領略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前華梵大學校長釋念一
謹識于聞性精舍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前言
影片中常見的,風塵僕僕的藏人一路做大禮拜到拉薩朝聖;在煙霧遼繞、充滿酥油味的小經堂中,裹著絳紅色厚呢氈僧袍的僧人們手持鈴和杵,修持著莫測高深的密法;金碧輝煌的唐卡上繪著三頭六臂、齜牙咧嘴顯現忿怒形象的護法神像……。一切都讓人覺得神秘得不得了,這也是我以前對西藏的印象——神秘而虔誠的國度。
因此,第一次在印度接觸到西藏師父時,我十分害怕,畢竟他們可是會用人類的頭蓋骨、小腿脛骨當法器的;而且在我幼稚的心靈中,高僧大德們都有他心通,一眼就可看穿我的壞念頭,更別說是轉世再來的仁波切,法力一定更高強了吧。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偷偷觀察著我所能接觸到的西藏僧人,咦,怎麼會和台灣正襟危座、低眉斂目的僧人形象差這麼多啊?第一次到印度時,三大寺都去了,也在寺院裡小住了一兩個月。當時出現在我眼前的西藏僧眾,大大顛覆了傳統出家人在我心中神聖超脫的印象;從小耳濡目染便對出家人產生的尊敬之情,也被隨地吐痰、小便、穿著夾腳拖鞋、走路像流氓的紅袍僧人們,給徹徹底底的破壞了。
當我看到戴著墨鏡、騎著重型機車的彪形大漢,不,彪形大僧,腦袋彷彿被打了一棒!大殿的法會中,三千位僧眾你推我擠的不好好排隊,紀律師的長鞭揮舞之下,則如風行草偃般,站立的僧人們一波波的隨著長鞭所到之處高低起伏著。差點也被鞭子波及的我嚇壞了,我想,那一鞭揮來被打到的僧人們應該很害怕吧,仔細一看,不,一點也不怕,他們臉上都帶著笑,還再推擠著呢!一樣都是佛陀的出家弟子眾,漢藏之間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啊!
就是這些顛覆傳統印象的外在形相,漸漸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對這些毫無外在威儀可言的藏僧們一探究竟。
不是為了學習佛法而來,也不是為了聽經,更不是為了學習藏文或學畫唐卡,只是抱著自助旅行心情的我,住在寺院裡無事可做時,看了《西藏七年》與《流亡中的自在》這兩本書,不可遏抑的嚎啕大哭起來。
這些西藏師父為何要到印度來?佛教起源於印度,但是早已在藏人稱為「聖地」的印度徹底絕跡了。然而今天,西藏各寺院紛紛在印度各地建起宏偉的大殿、數以千計的僧舍,為的是將佛法弘揚回印度嗎?不是的,這都是出自於毛澤東的恩澤——藏人被迫流亡異鄉;眾多西藏人追隨法王達賴喇嘛的腳步,流亡至印度及世界各地。
佛教在西元七世紀、藏王松贊干布在位時,傳入西藏。八世紀藏王赤松德贊在位之時,更迎請印度高僧寂護論師與蓮花生大士到西藏傳法,將佛經從梵文翻譯為藏文,並建立了第一座寺院——桑耶寺,以及產生了第一批剃度出家的七位藏僧。
經歷了朗達瑪的滅佛運動,到十世紀後半,佛教在西藏開始復興,是為「後弘期」的開端。西藏譯師重新翻譯佛經,並邀請阿底峽尊者等許多印度大師入藏。除了寧瑪派之外,其他三派:薩迦、嘎舉、格魯,都是在後弘期之後才陸續發展的。
佛教在西藏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之後,演變成四大教派,而所有的派別和傳承,均能直接追溯至釋迦牟尼佛時期,而且每一個西藏教派的創始人,也都與印度佛教的個別傳承有淵源。例如:「嘎舉」意為「言傳」,表示傳承清淨無誤、一脈相承,嘎舉派傳承祖師,是大成就者印度瑜伽士帝洛巴和他的弟子那洛巴。由於西藏佛法在傳承祖師、翻譯的經典等,都與漢地系統的「漢傳佛教」有所不同,因此我們稱之為「藏傳佛教」。
若稱藏傳佛教為「密宗」,這是以偏蓋全的說法,西藏四大教派的僧團教育體系都要修學顯教的經論,換句話說,藏傳佛教是顯密並重的修學,在順序上,更是先學顯教再學密法。因此,若看到紅衣僧人便稱之為密宗,是不太對的。
寧瑪派,是藏傳佛教中歷史最久遠的一個教派。「寧瑪」,意為「古老」或「舊的」,該派重密輕顯。相反的,年紀最輕的教派——格魯派,則重顯輕密。目前在格魯派的三大寺中,要修學約二十年的顯教經論,之後再進入密法學院,學習一年的密法。常有人問我:「喔,妳是信密宗的啊?」我都不知該回答是或不是。
在中華歷史上稱這四大教派為紅教、花教、白教、黃教,據悉,是因舊派寧瑪派修行者多戴紅帽之故,便稱之為紅教;而改革陋習的新派格魯派皆戴黃帽以示與舊派不同之故,便稱之為黃教;而嘎舉派祖師密勒日巴等人多穿著白色的瑜伽士裝束之故,便俗稱為白教。這種流行於華人圈的錯誤稱法,在西藏可是從未聽過,因此若問一位紅衣僧人:「你是紅教還是白教?」可是會讓西藏師父傻眼的。
第一次住在南印的寺院裡,有一天去拜見一位年輕的仁波切,他的佛龕正中央供奉著一大兩小黃澄澄的佛像,那是宗喀巴師徒三尊,其他還有一些迥異於漢傳的佛像,我不認識,但我認得的釋迦牟尼佛不但很小一尊,而且被放在最邊邊的位置。我詫異極了,佛教創始者——導師釋迦牟尼佛怎會被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呢?為何宗大師可以享有主尊之位呢?我立刻向這位第一次見面的仁波切提出疑問,年輕的仁波切看來從未想過這個問題,他想了一下回答說:「大概是購置佛像的時候就大小不一,所以就按照大小高低來排囉。」我看了一下佛龕的擺設:「應該不是這個原因吧!」仁波切吶吶地說:「其實我也不知道原因。」
我發現三大寺的僧人房中若供有佛像,要不是宗大師師徒三尊,要不就是手拿智慧劍的文殊菩薩,反倒是釋迦牟尼佛較為少見。南卓仁波切說:「雖然釋尊開示了佛法,但若沒有上師的教導,我們就無從學習佛法;若沒有宗大師,我們格魯派的教法也無從開展弘揚。」難怪師父們房中大多會有達賴喇嘛尊者的法照及自己經教師的照片,因為上師最大!若無上師,我們無從得到佛法的知見與修持,所以在藏傳佛教中,上師、本尊、佛、菩薩……,位階是這樣子排的。
宗喀巴大師——格魯派的創始人。當時藏傳佛教各派戒律廢弛、教風敗壞,上位的僧人享有特權,因此宗大師的教風改革,從整頓戒律入手。西元1409年,宗大師在拉薩興建了甘丹寺,之後又相繼建立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
三大寺均位於拉薩,六百年來學風鼎盛。甘丹寺由宗大師親自創建,故稱為三大寺的母寺,擁有二個學院——強孜察倉(北學院)和夏孜察倉(東學院),僧眾有三千三百人。
哲蚌寺由宗大師的弟子於1416年所創建,「哲蚌」意為「堆積稻米」。還記得我查字典得知哲蚌寺的字意時,快笑翻了!哲蚌寺共有四個學院——洛色林察倉、果芒察倉、德漾察倉和密宗察倉。據悉哲蚌寺有七千七百位僧眾,但實際上曾多達一萬多人。(察倉意為僧院)
色拉寺則分為三個學院——伽察倉、媚察倉與密宗察倉,僧眾人數為五千五百人,實際上並不止這個數目。色拉寺是宗大師的弟子大慈法王於1419年所創建,大慈法王曾被明成祖封為「大國師」。
「1959」是我學會的第一組複雜的藏文數字,因為常聽!1959年是西藏人難以忘懷的一年,是近代西藏歷史上血淚斑斑的一年,許多人事物都從這年開始變了調,遠離了有著晴空萬里、豐美草原、牛羊成群的家鄉,踏上了不歸路,再也回不去了。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尊者離開拉薩開始流亡之路,隨後大批的藏人也先後逃抵印度,印度政府敞開雙手迎接這一群又一群倉皇逃難、衣衫襤褸、走了數十天甚至兩三個月的西藏人。四大教派的僧人全被安置在北印度的跋薩監獄裡繼續學習佛法,大批的難民則被派至印度北方以修築公路為生,數以千計的難民好不容易逃離了被染紅的雪域,卻死於異鄉的氣候不適、水土不服與各種傳染病。
在印度政府的慷慨相助之下,經過艱辛的努力,八萬多名西藏難民逐步定居,在北印、南印、尼泊爾、不丹形成一個個藏人村落。時至今日,每年仍有兩千多名藏人翻越喜瑪拉雅山來到印度,拜見達賴喇嘛尊者——藏人永遠的精神領袖。
1960年底,在南印靠近赤道的「貝羅溝比」成立了藏人定居點,六百多位藏人來到叢林中開始開墾,與大象、毒蛇搏鬥。1969年10月,原本安置在跋薩的僧眾開始依據所屬教派安置,第一批三百人被派到「貝羅溝比」,這就是色拉寺的僧人。色拉伽及色拉媚兩個學院的僧人們,在這充斥野象、野豬的森林裡,蓋起了寺院。四十年後的今天,色拉寺有五千多位僧眾。
1969年11月,第二批僧人三百多名被安置到南印的「盟古芝」,這個藏人定居點是在1966年底由兩千一百多位藏人辛苦建立的,這裡的氣候更為炎熱,這批僧眾在此重建了甘丹寺與哲蚌寺。兩寺距離約莫十五分鐘的車程,兩寺的中間及四週圍繞著好幾個藏人村與一望無際的農田,樹木早在當年就被砍伐光了,只有不時會來破壞農田的猛象和山豬見證當年這裡是個草木茂密的森林。時至今日,位於南印的甘丹寺有三千多位僧人;哲蚌寺則有六千多位僧眾。
在跋薩監獄裡住了十年的僧人被派往南印定居、成立寺院時,僧人住帳篷,每天闢地、做磚頭,堪蘇仁波切告訴我:當年印度政府發工資每天五毛盧比。從雪域西藏來到南印酷熱的環境下做工,不少藏人、僧人死亡。我看到現年六十歲以上的西藏人總是特別尊敬與不捨,因為他們當年不是在中共的勞改營裡種菜、學修理機器;就是在南印製磚、蓋房子、開墾田地,沒一天吃飽過。
流亡中的西藏僧人胼手胝足在印度建立起兩百多座寺院,四大教派在印度欣欣向榮。在印度定居的西藏難民已超過十三萬人,經過五十年的努力,人人都可安居樂業。西藏人雖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寄人籬下,但在印度看不到一個藏人乞丐,反之,在自己的國土上,印度乞丐隨處可見。教育亦然,藏人流亡社區的教育,從零開始已做到全面普及,而印度,還有許許多多的文盲
位於拉薩的三大寺仍然存在——被破壞後又原址重建,那為何還有人要翻山越嶺,不畏被抓、被關、被凍傷雙腿截肢的下場,奮力前往印度?西藏「回歸祖國的懷抱」後,僧尼被迫還俗,後來雖開放了,但寺院仍有名額限制,換言之,想出家得排隊等待。這還不打緊,想當僧人就要宣誓效忠祖國,要把破壞祖國團結的達賴喇嘛的照片丟在地上吐口水、用腳踩。家中再也無法高掛法王的照片,信仰是生活的中心、是一切價值觀的全部的西藏人受不了了,父母將小孩託人帶往印度。至今可見,藏人流亡社區的學校裡,許多學生都是爸媽留在西藏的「孤兒」。藏人三五結伴偷渡來到印度,第一件事就是到達蘭薩拉覲見法王,「我還以為達蘭薩拉是個大都市,心中想像法王住的地方像拉薩的布達拉宮一樣宏偉,沒想到……。」不只一位師父這樣跟我說過,看到只有兩條小路的達薩小鎮的西藏師父們,都難掩失望、震驚之情。覲見法王後僧人們依照自己的教派及親戚所屬的寺院,進入新建於印度的寺院中研讀修行。
我所接觸的僧人,便是這麼一群遠離家鄉、揮別親人、來到語言不通的異地,與炎熱的氣候搏鬥,再也吃不到家鄉美味的糌粑與犛牛肉乾的「難民」。是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護照,在國際上的身份是「難民」。
南卓仁波切八十多歲的老父親,當年是三大寺的僧人,在中共僧尼一律還俗的規定下被迫還俗。這幾年一直想前往印度聽法王講經,順便看看十多年未見的兒子,但中共就是不放行。八十多歲的老人家還能怎麼起義造反嗎?中國政府不發給簽證的心態令人無法理解。重聽的老父親在電話中永遠和仁波切雞同鴨講,永遠都是那一句話:「我知道『格西東郭』需要很多錢,我一直都在為你存錢,你別擔心啊!」
六十九歲的老格西從南印跑了好多趟到德里,在德里等啊等的,等到的永遠是「過幾天再來」這句話,中國辦事處就是不發給簽證,魂牽夢繫的家鄉一別就是五十年。洛桑師父待在青海的媽媽眼睛快瞎了,一直想再見兒子一面,洛桑師父每兩個月就去辦事處申請簽證,但就是不讓去!
他們不是什麼破壞祖國的反共鬥士,也不是堅持西藏獨立的藏獨份子,都只是想見見親人而已。連自己的家鄉也回不去,連自己的爸媽也見不著,這世上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令人難過的事?
但這些可愛又可敬的師父們,沒人跟我罵過中國共產黨,沒人抱怨過人民解放軍,說起這些國破家亡的事都是一派雲淡風輕,連在牢中被中共打成微跛的拉巴老師,都不曾說過一句中國人的不是,一句也沒有。地位高超、赫赫有名的戚烏昶仁波切還不經意的跟我說他會修車子,「我在勞改營裡學的嘛,我修了好幾年的車子啊!」這是什麼樣的修行氣度?是一種什麼樣的人生價值觀?西藏人,真的讓我很好奇!
十一年來,來去印度八次,每次約四至六個月。接觸的大多為紅衣僧人,這些外在毫無威儀、愛開玩笑、從不主動開示佛法的僧人,顛覆了我心目中對出家人的刻板印象,跟他們相處就如同朋友一般,自在極了。即使是仁波切或德高望重的老格西,也沒人端著個架子,更無人動不動就把佛法掛在嘴邊開示,不管對方想不想聽。
極度樂觀、高度的幽默感、謙虛的態度、應該生氣卻不生氣,還可哈哈大笑……,這些特質普遍展現在西藏人身上。濃厚的好奇心驅使我想知道:這是民族天性,亦或個人修為,還是佛法的影響……。為何這群沒有自己土地、流亡他鄉的西藏人,能展現出這樣的人生態度?這十一年來,來來去去印度,住在南印的三大寺內或北印的達蘭薩拉,當回到台灣,便照顧短期來台弘法的西藏師父們。長期學習藏文,以及數度照顧僧眾並安排弘法行程、兼當翻譯的經歷下,我的藏文口語日益進步的同時,雖越來越了解西藏僧眾的想法,但我還是要說:與藏人相處,處處是驚奇!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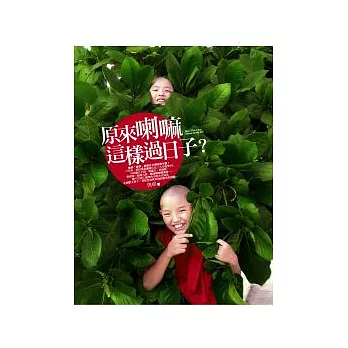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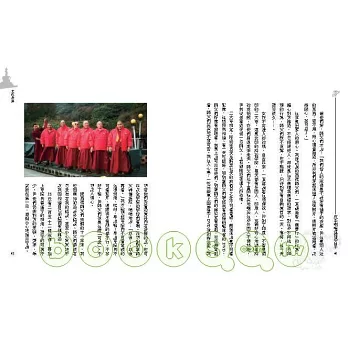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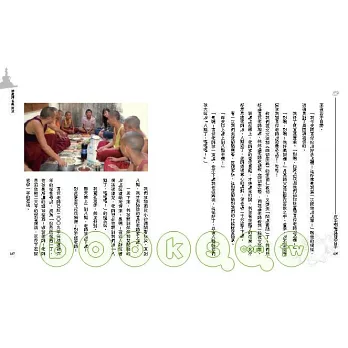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