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在通往綿羊夢的路上
後來,在路上,我們沉默了下來,我們陷入了各自的夢中。
夢裡,我們照例走進那座空無一人的小學,照例提起那年毫無預警的遺棄:「幾天前還發誓說『我愛妳』,『我愛妳』……結果呢?第二天居然就跟班上那個誰在一起了……」妳說,那時候站在補習班頂樓,心想或許就這樣死去也不會有人在乎吧。
那樣迄今無從釋懷的惘然。我望著妳低垂的臉,單薄的光照底下浮動著單薄的頸子,有一片刻,以為妳就要流下淚來了,冷不防,妳拉起我的手朝前奔去——我驚醒過來,看見妳睡得正熟,臉上跳動著這個冬季疲軟的日照,像路的兩旁永遠有被切割跳動的暗影,像冷藏櫃裡的蛋糕始終失去彈性。此時此刻,車子一寸寸駛進暗下去淡下去的世界,灰濛濛、冰涼涼,像我們介於夢與現實的意識,像我們的愛需要經常定義——「我需要很多很多的愛。」這是蘇偉貞的句子——十七歲,我們以為懂了,以為愛是義無反顧,未料一眨眼,竟成「愛的很多很多」……
愛情成了謎中之謎,我們伸出手任由小貓輕舔,帶有一絲絲陌生的刺癢,一絲絲——濕潤。濕潤是車窗上的一朵雲,一束雨,它們很快墜入更為遙遠的地界,很快我們便發現:整輛公車上只剩下我們倆,而司機透過後照鏡問:
「第一次來嗎?」
我搖搖頭。
「剛戀愛?」
我點點頭。
「很冷唷?」
我把妳的手握得更緊更緊。妳終究還是睡著了。眼睫偶爾輕顫那麼一下,靜謐的臉龐難以想像日常之慧黠。我忽而想起,這些時光以來的自己:從一九九九年迄今,從那個昏暗的小套房到十三樓俯瞰一望無際的鐵皮棚架,這之中究竟有什麼變得不一樣了呢?好幾個傍晚,我們看望光影一點一滴變短,不發一語、不知所措、不明所以,說不上來的空慌與寂寥……似乎生命至此也只是生活本身,而我們甘之如飴,並且世故,甚至生出一無所感的倦態──「說也奇怪,他每次總會寫到他的青春焦慮。」這是一位學生對我的觀察,約莫是責怪我對青春的眷戀實在太多太多了吧。而事實是,當我重新檢視這些年來的散文篇章,就連自己也深感詫異:有很大部分竟耽溺於青春之惘然,愛之瞬忽──
又一朵雲越過我們的上頭了。車外的冷風何時才會停止呢?
「沒事的。」一切都會變好起來的。多麼像一句不痛不癢的台詞。夕照覆蓋上我們的身體,妳的喉嚨發出淡藍色光痕,窗外嗚嗚風聲是舞台劇裡的音效,冷不防妳拋出這麼一句:
「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是不是覺得煩了?」
「是不是……」
我說「噓」,妳聽——那株茄苳樹沙沙沙沙,風穿過妳的髮梢的片刻,樹葉說話說得極其凌亂——妳聽——我挪了挪被妳壓麻的肩膀,揣度還未頓悟的那些:掙扎,不甘,不認命,「我看不開」——禪宗公案裡,師父將弟子按入水中,說:「汝求真諦如空氣時,便知何為真諦矣。」
那麼,屬於我們的真諦又是什麼?為什麼在面對這本散文集的當下,我竟不知從何說起?我的腦袋裡竟填充著關於論文的全部?為什麼我整個人像被抽空了那樣?
你啊,妳說,我們出來玩耶,你想這些幹麼?
然後,車子就這麼停下來了。雲朵很快流入無光的冰藍底,身旁林立的看板全失去了指引作用。真的好冷好冷啊。風毫無遮攔地鑽入我們的胸口,妳縮著頸子尖叫,拚了命搓揉雙手取暖,卻終究徒勞。「這裡就是了嗎?」我問。「還沒,還要再上去!」妳叫著——想起上一次,妳是和妳的前愛人來此遊玩——因而在等待民宿業者前來接送我們的空檔,像要覆蓋從前的記憶似的,我拉起妳跑到路中央,一面聆聽引擎隨時迫近的驚恐,一面測光、構圖、拍照……
昏黃的燈光映在雙黃線上,山裡的空氣夾雜著獨特的青草味,整條公路上,除了偶爾颯行而過的車子,也就是我們的嬉鬧了。我看著妳的笑臉,妳黑密的髮,以及妳亟欲消瘦的小肚肚,那一刻,我們多麼親愛。在入冬以來最強的寒流裡,我們躺在公路上,側耳傾聽引擎聲轟轟作響,彷彿路面生出心跳,彷彿聽見最最細微的訴說──我們肩並肩,手握著手,準備殉情的戀人似的:「如果能夠這麼一了百了,也沒什麼不好。」我想起妳說的話,無關乎情感,無關乎強弱與否,純粹的活著,如斯而已。
快樂之於我們,到底是來得太少太少了。
(那一刻,我腦海中浮現幾週前橫躺於馬路上的那個女孩。那是一個日照溫暖的下午,她俯趴於地,似乎牙齒什麼的迸至柏油路面來了,濕亮亮的光澤在日照底下格外紅潤,但她的手腳卻完好如初,連同那頂毛帽在風中輕輕顫著、顫著)
又一輛車子奔行而過。
此時此刻,我們真正成為公路電影裡,那些恆常可見的沉默者了。並非天氣之冷峻,而是置身於公路之中,對於四周景色之深闊,不免興起自身渺小之嘆。那總使我想起經常搞混的《在路上》——它並非《大亨小傳》費茲傑羅(Fitzgerald)的小說,而是凱魯亞克(Keroua)的作品——這位大學二年級即遭到退學命運的作者,以其瀕臨背德與備受爭議的文字,陳述美國「垮掉的一代」如何橫越公路以至墨西哥,藉以尋找自我。
我們又打算尋找什麼?
「你看你,少嚴肅了。」妳張開雙臂,大字仰躺。
(我真的太嚴肅了嗎?)
聲音緩緩流出我們的耳朵。光度越來越暗,暗得連妳都看不清楚的瞬間,我想起這一趟漫長的旅程:出發的當下沒有任何設想,抵達之後沒有過度的激情,繼續的追尋與再追尋,一如路總是要繼續下去的,一如那個令人抱持無限想像的草原:奔跑;靜立的枯木;雲——想起出發前,我們還信誓旦旦要在冷天的草原裡吃上一盤剉冰,或著抱著從山坡上滾下來,哪裡知道,此刻我們還在公路底蜿蜒。
我們又沉入各自的夢中了。
車子一寸一寸駛進無光的所在,一寸一寸駛進曝亮的路燈底。許多年後,當我們想起這一刻,我們還會記得彼此嗎?我們的愛依然繼續?妳還是對我叨念:「要是你早點畢業的話……」妳還是以為我習慣一個人,習慣拒妳於千里之外嗎?「怎麼那麼久都還沒有到啊?」妳在半夢半醒:「到了嘛?」參差的細葉杉不時晃動,雲層低垂,妳是否又夢見了那段無從忘懷的遺棄?夢裡的我們是否還盪著鞦韆?是否有成群的綿羊等著我們?暗影幢幢。灰濛濛。冰涼涼。現在妳看來多麼像個孩子。
也就是一個過彎的當口,我感覺到我們就要跌出座位了。
「我們現在究竟在哪裡?」
我抓住妳的臂膀,看著妳,良久良久說:在路上。
我們在通往綿羊夢的路上。
張耀仁 二○一二年二月台北中和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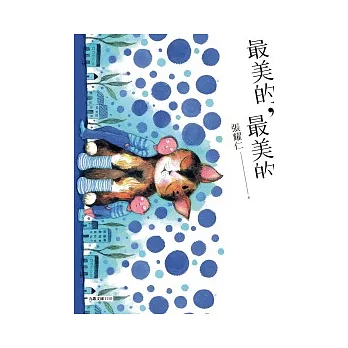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