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許多嚴肅的議題並不需要長篇大論,只需要傾聽一個故事。主角或許是一件手工編織的衣裙、一位鐵道偶遇的旅人,甚至一畦家庭菜園,這些故事所敘說的內容可能並不深奧,卻帶給人無盡的深思,進而透出事物背後的靈魂及其所蘊含的深意。部落原住民與現代都市文化的格格不入甚至相斥衝突,是數十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也是許多原住民運動努力的課題。作為一個非原住民的讀者,若沒有長期深入的關注,是沒辦法對這些議題作出評論的。但是,透過故事的傳述,就算只是描述性的,不偏及任何評判的,也多少能夠理解原住民在經歷都市文化的洗禮時所遇過的困難以及不被理解的痛。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這本散文集,集結排灣族女阿(女烏)利格拉樂‧阿(女烏)於1994年到1996年間發表在報刊上的短篇文章。卷一〈原住民的母親〉著重刻劃原住民女性遭受的種種境遇,還有她們面對都市文化的時候如何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堅強生存,從而體現自身價值的狀況。卷二〈山居手札〉則是阿(女烏)回歸部落後的生活紀錄,包含了阿(女烏)參與原住民運動的心得與對社會環境的觀察。
阿(女烏)母親是排灣族人,父親為外省籍老兵,她從小在眷村長大。在那個時代,原住民還是備受歧視的一群人,「山地人」、「番仔」的標記如影隨形,從小遭受各種不平等待遇的阿(女烏)曾經非常厭惡自己的血統,並且拒絕承認自己是原住民。外省父親去世以後,阿(女烏)跟母親一起搬回排灣族部落居住,至此才開始慢慢體會到身為原住民的價值,並開始來回奔走於部落之間進行田野調查,尤其著重在原住民女性生命歷程的挖掘與未來定位的追尋。阿(女烏)常說自己生為排灣女子,又嫁作泰雅族媳婦,自身經歷讓她擁有一雙跨族群的眼睛,看遍了原住民女性的苦與樂,並藉著一支筆寫出一個又一個的真實故事,串起了原住民女性相似的命運。
整本書傳達出一個訊息:原住民在傳統文化與都市生活的夾擊下如同迷路的幼兒,他們遠離祖靈的庇佑,為的是尋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但同時他們又擁有一顆希冀回歸部落的心,嚮往血液裡的那份悸動。這種喪失自我的感覺,或許才是最令人痛心的隱憂。如同本書書名《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指的就是一個阿美族婆婆擔憂阿美族傳統的紡織技藝將無從傳承,只因他從小就把女兒送到平地念書,女兒長大以後卻再也不願回來。能怪誰呢?明明是自己親手斬斷了這條文化生命線,現在想要反悔卻也來不及了。許多部落文化就這樣逐漸消失,徒留心急的哀嘆。
相較於卷一以溫婉柔和的口吻娓娓述說原住民女性的生命物語,卷二雖名為〈山居手札〉,實為阿(女烏)對整個社會環境的觀察筆記。生長於眷村的阿(女烏)並沒有忘記自己身上有一半的外省血統,透過父親落寞的身影,她觀察到除了原住民以外,還有一群人生活在歷史的悲劇之下,他們其實也是需要關心的弱勢族群。老兵的故事並不新鮮,但親身經歷過的人總是特別能表達出那種無語問蒼天的無力感。在兩岸開放交流的今天,這塊歷史的傷疤即便不能完全抹消,或許也能逐漸走出哀痛吧。
阿(女烏)長年從事田野調查並致力於原住民運動,培養出極為銳利的觀察力。這麼多年來,即便政府機關與社會大眾已經開始關注原住民議題並積極做出某些行動,但若沒有從根本去理解原住民的思維方式,只是從外表做做樣子,所謂的原住民運動也不過是空口說白話而已。卷二末尾幾個短篇,尖銳的點出這種粉飾太平的現象,同時也批判了原住民本身,尤其是年輕一代原住民缺乏改變的熱情,天助自助者,若不從自己開始做起,又怎能幫助整個族群奪回應有的尊嚴呢。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出版於1996年,距今已有17年。這中間台灣社會對於族群問題,不管是部落與平地、外省與本省,早已經歷了許多磨合,也慢慢地達到了某些目標。書中描寫的許多偏見或誤解的現象已經逐漸消失,也還有許多深層的問題仍然無解。阿(女烏)的文句,或許帶了點心焦,又隱隱透露出不滿,但字裡行間散發的那份溫柔卻堅韌的情感,卻持續傳達出她對整個族群的關懷,以及盼望族人從我做起的殷切期許。就如同本文開頭所言,透過說故事這種直接又簡單的方式,往往更能貼近人心,也更能刻畫在人的記憶裡,不會被輕易忘記。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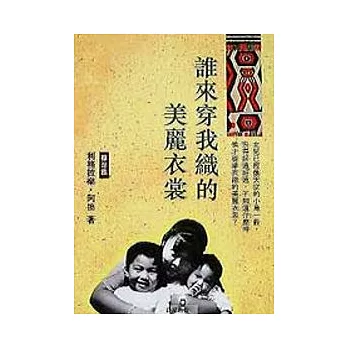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