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永夜
南方朔
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猶太意第緒語作家埃利.維瑟爾所寫的這本《夜》,是他畢生四十餘著作的第一本。它最早出版於一九五八年,距今已將半個世紀。但儘管隔了那麼久遠的時空,今日讀來,仍能感受到那種漆黑如夜、冷冷的恐怖。
對於這樣的一本小書,我們在讀的時候,不要想,也不要哭,就讓自己無感覺的讀下去,最後一定會被書裡散發出來的寒意所包圍,靈魂也會被深深感動,原來人性的黑暗與殘酷,可以一至於斯。但也只有在這種人不如蟲豸的極限環境,或許我們才可以去重新定義生命。
有關納粹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大浩劫」(Holocaust)的著作早已車載斗量,例如自傳性的紀實著作像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安妮的日記》,義大利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回憶錄《如果這是一個人》,或者文學創作如一九六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猶太女詩人薩克絲(Nelly Sachs)以及法國猶太詩人塞南(Paul Celan),這些都已讓人耳熟能詳。但與上述那些著作相比,維瑟爾的《夜》所描述的可怕情況,可以說更為過之。因為他所經歷的,乃是納粹屠殺猶太人過程裡最瘋狂恐怖的那一段。這種獨特的經歷,遂使得《夜》在與其他著作相比時,顯得格外的不同。
我們都知道,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緊接著到了一九三四年八月三日,他又在興登堡總統逝世後兼任總統,於是,一個全權在握的專制領袖正式誕生,有系統有步驟地對猶太人之迫害遂告正式展開。他由褫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和身分權開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展開,進一步將迫害具體化。希特勒從一九三三年起,就在蓋世太保首腦海德利希(Reinhard Heydrich)協助下,陸續在全歐各地設置集中營。這也就是說,早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所謂的「汪湖會議」(Grossen Wannsee Konferenz)正式提出消滅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方案」前,大規模的集體屠殺早就開始了。整個「大浩劫」最先是在靠近蘇聯的所謂「東線」開始,而後再向德國本土及「西線」擴延。在「最後解決方案」這個名詞出現前,單單在「東線」即已屠殺猶太人一至二百萬人。而有了「最後解決方案」後,當然消滅猶太人的工作格外加速。及至一九四二年夏天海德利希在從捷克返回柏林的途中,遭到捷克愛國者伏擊重傷,一星期後死亡,屠殺工作由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接替,於是又有了更嚴厲的所謂「海德利希計畫」,屠殺工作更為加速。尤其是一九四二年秋,德軍開始一連串失利,包括在阿拉曼戰役中敗於英軍,美軍登陸北非,蘇聯在列寧格勒戰役裡俘虜了德軍好幾師,一九四四年一月的第一個星期,蘇聯紅軍已打進了波蘭,這一連串發展,都使得希特勒警覺到戰爭可能失敗,消滅猶太人的工作必須加快腳步。
於是,維瑟爾他們一家人的不幸,就在這樣的局勢變化下開始到來。
維瑟爾乃是外西凡尼亞(Transylvanie)的錫蓋特(Sighet)人。外西凡尼亞這個地區原屬奧匈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奧匈帝國瓦解,改歸羅馬尼亞。到了二次大戰,它又被切為二,有五分之三仍歸羅馬尼亞,另外五分之二則歸匈牙利。維瑟爾即屬於匈牙利這一邊。當時匈牙利領袖為霍希上將(Admiral Nicholas Horthy),他有極強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於自己治下的十五萬猶太人,始終拒絕交給納粹消滅,因而維瑟爾家鄉的猶太人在那個其他國家猶太人都大量被屠殺的時刻,還能偏安一角。由《夜》這本書一開始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他們那種苟存下的幸福。
然而,希特勒對霍希上將拒絕合作的不滿,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三月爆發。於是德軍開進了匈牙利,罷黜霍希上將,另立傀儡政府。外西凡尼亞地區十五萬猶太人的惡運即告到來。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初剛過完復活節即被納粹接管,而後送往設於波蘭、最惡名昭彰的奧許維茲—波克瑙集中營。他的母親和妹妹就死在這裡,他的兩個姊姊倖存,而他和父親最後又因為俄軍快要來到,被運到另一個同樣惡名昭彰、設在德國威瑪附近的布肯瓦德集中營。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他的父親命喪於此,兩個多月以後,即四月十三日,布肯瓦德集中營被美軍解放,維瑟爾終於得救。
因此,當我們了解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後來讀或重讀這本著作,即可知道維瑟爾的集中營經驗雖然只有將近一年,但這段經驗卻至為獨特!
第一,他所遇到的,乃是納粹失敗前最後的瘋狂,他們也是納粹要毀滅的最後一批人。因而在集中營以及轉運的過程裡,一切的野蠻殘暴也更加的赤裸裸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第二,自從蓋世太保頭目海德利希死後,接棒的希姆萊即決定將匈牙利、波蘭、捷克、奧地利等國的猶太人送往殺人效率最高的奧許維茲—波克瑙集中營,以及布肯瓦德集中營處理。奧許維茲—波克瑙集中營建於一九四○年,它原來要規劃成石油化學基地,而後變成殺人工廠;布肯瓦德集中營建於一九三七年,乃是殺人醫學研究中心。它們從一九四三年起都在納粹工程師卡姆勒少將(Heinz Kammler)規劃下,更有效率地殺人燒人。維瑟爾從家鄉一路輾轉歷經這兩個最可怕的集中營,最後還能苟存性命,這必然意謂著他看過、經過的慘絕人寰,的確少有人能與其相比。
因此,《夜》可以說是所有「大浩劫」倖存者所寫的著作裡最慘的一部。「大浩劫」的殘酷由於超過了人類的經驗,因而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的語言文字都已不再夠用,任何倖存者的回憶,無論寫得多麼具體,都會留下可能超過正文的「無語問蒼天」的可怕空白,而正是這種空白,才更讓人覺得恐怖。波蘭猶太詩人戈比爾蒂格(Mordechai Gebirtig)曾如此寫過他們那時的恐懼,但仍不足以道其萬一:
我們無法入眠,張著耳朵傾聽
恐怖的思緒滑過心頭
今夜我們之中的某人將是什麼命運?
誰會是明天將死去的人?
我們不敢入眠的瑟縮著
在這個門窗嘎嘎作響的時刻。
我們的心會忽然涼成一團
當飢餓的老鼠窸窣著穿過地面!&
在《夜》裡,維瑟爾寫盡了他們的恐懼與被凌虐。他們有如蟲豸般被踩死,在那樣的時刻,人們只剩下詛咒上帝,而人性則在極限環境下蒸發,回到了野蠻狀態。人被逼著必須奔跑,否則就是死亡,一群人就居然能在大雪中跑了幾天幾夜。人犯了什麼錯,要去生受這比蛆蟲還不如的折磨?當人活得有如骷髏,人性和親情又將如何安身?
我不帶一點感情的讀著這本書,讀著讀著,在酷熱的夏季,心裡卻愈來愈寒冷如永夜。人類對同為人類的鄰居,真的會做出這樣的事嗎?直到今天全世界都還有人拒絕相信「大浩劫」,這些人不是支持納粹,而是他們真的不敢相信,不敢面對人的邪惡可以達到如此程度!
讀《夜》,除了那痛入骨髓的寒意外,對於外西凡尼亞的猶太人在一九四四年前偏安一角所產生的麻木以及苦中作樂下的樂觀,我也格外有痛感。近代德國最偉大的音樂指揮家奧圖.克倫培勒(Otto Klemperer)的堂兄弟維克多.克倫培勒(Victor Klemperer)因為娶了正統德意志人而得以倖免於難,他後來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一書裡指出,由於納粹一開始的所想所說所為都太可怕離譜,它反而在許多人的心裡產生一種荒誕的樂觀感,認為「不會怎樣啦」(knif),「絕對不會怎樣啦」(kakfif)。因而許多人可逃卻未逃,最後在樂觀的幻想裡一步步走進了再也無法回頭的永夜。當我讀《夜》的第一章,寫他們一九四四年復活節結束前的愚騃樂觀時,真想擲筆三歎!
我不帶一點感情的讀這本書,愈讀愈冷,最後潸然淚下,為人性而哭,為歷史而哭。看著人類過去曾犯下的可怕罪惡及所造成的可怕受苦,我們又怎能不更堅持我們抵抗邪惡的最後良心呢?
是為序兼導讀!
代序
經常有許多外國記者來探望我。我對他們心存警惕,既想與他們無話不談,又深怕因為不了解對方看待法國的心態,而落人口實。在這樣的場合,我從不忘謹言慎行。
那天上午,這位年輕的猶太通訊記者為《特拉維夫報》訪問我。我和他一見如故,拘謹不久後就轉入私人話題,最後,我提到德軍占領法國時期的回憶。通常感動我們最深的,並非我們直接參與的事物。我告訴他,在這段慘淡歲月裡,沒有任何景象比奧斯特里茲火車站上,滿載猶太兒童的車廂更刻骨銘心……我並未親眼目睹,是妻子滿懷恐懼地描述給我聽,當時我們仍對納粹大屠殺一無所知。畢竟誰能想像得到!從母親懷裡奪走稚兒,這情景已經遠遠超出我們所能想像的範圍了。這一天,我相信是自己有生以來初次接觸神祕的不公平,這個新發現意味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西方人於十八世紀編織了夢想,深信這個夢想在一七八九年破曉而出,經歷啟蒙運動和科學發現而愈形堅固,直至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然而對我而言,這個夢想卻在擠滿幼童的火車前幻滅殆盡;而且,我萬萬也沒料到他們將成為瓦斯房和焚化爐的燃料。
我自覺應該向這位記者透露如上內容。我歎息道:「我不斷想起這些孩子!」他告訴我:「我是其中一位。」他也是其中一位!他眼睜睜看著母親、可愛的妹妹和除了父親之外的多數家人消失在吞噬活人的焚化爐裡。至於他的父親,這位記者日復一日看著父親受盡折磨、病危終至死亡;何等的死亡!當時的情況就描述在這本書裡,我留待讀者──應該與《安妮的日記》的讀者群一樣眾多──自行發掘其中細節,還有小男孩如何奇蹟式歷劫歸來。
我想肯定的是,看過其他眾多的指證、可怖的罪行之後,此書的見證仍顯得與眾不同。這些外西凡尼亞錫蓋特市的猶太人原本有時間逃脫厄運,卻只能盲目以對,並以令人無法想像的消極態度任其宰割,對於歷劫歸來的證人的警告與懇求充耳不聞;這名證人舉證歷歷,卻無人採信,甚至被視為瘋子──光以上這些就足以構成無與倫比的傑作。
然而吸引我的另有他處。書中擔任敘事的小男孩實為上帝的選民,打從意識覺醒開始,他只為上帝而活,鑽研《猶太法典》(Talmud),意欲探索神祕主義卡巴拉,並且相信永恆的存在。我們從未好好思量以下這件較不被注意的惡行的後果,而且對於擁有信仰的我們而言,最痛心的也莫過於此:在倏然發現邪惡之最的小男孩的靈魂裡,上帝已死。
試著想像他如何經歷這一切。他看著從焚化爐冒出的一圈圈黑煙逐漸消散,在那裡,他的小妹與母親跟隨成千上萬人的步履撲向死亡:「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個夜晚;集中營的初夜讓我的一生變成漫漫長夜,並且重重鎖上,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煙霧,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些小孩的臉龐,他們的身體在靜謐的藍空下變成一縷輕煙,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火燄,它將一輩子蠶食我的信仰,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些寂寥的夜晚,它們讓我永久喪失生存的欲念,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瞬間,它們扼殺我的上帝和我的靈魂,讓我的夢想化成荒漠。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即使我注定活得跟上帝一樣蒼老,我永遠也忘不了。」
我終於知道這位猶太年輕人吸引我注意的第一眼是什麼:他像死而復活的拉撒路【1】,卻被迫在陰暗的斷崖邊不停流浪,匍匐在飽受褻瀆的死屍裡。尼采的吶喊「上帝已死」幾乎具體表現在他的身上。在這個男孩的眼裡,至愛的上帝,溫柔與慈悲的上帝,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早在崇拜純種血統──所有偶像崇拜裡最貪婪者──的祭典裡消失無蹤。有多少謙恭卑微的猶太人因而喪生?在比無數恐怖日子更恐怖的那一天,這個男孩看著營裡另一名孩子被處絞刑(沒錯!):一位有張悲傷天使臉孔的孩子。他聽到背後有人呻吟著:
「上帝在哪兒?祂在哪裡?上帝到底在哪兒?」
我內心發出聲響:「祂在哪兒?祂就在這裡,吊在這個絞架上。」&
在猶太年的最後一天,男孩參加新年的盛大彌撒,成千上萬的囚奴吶喊著:「聖哉上帝之名!」不久以前,他也曾卑躬屈膝、畢恭畢敬、滿懷熱情,不過如今,他起而反抗;一個受盡超越心靈所能想像的屈辱的生命體,質問又盲又聾的聖靈:「現在,我不再苦苦哀求,我失去呻吟的能力,但變得更加堅強。我雙目圓睜,踽踽獨行,我要控訴上帝;我在這個世上極度孤獨,既無上帝亦無同類,缺愛也乏憐,除了灰燼之外什麼也不是,不過卻比我曾經長久相繫的萬能上帝更加強大。今天的彌撒典禮上,我只是冷漠的旁觀者。」
而相信上帝就是愛的我,該如何回答這位年輕人?他碧藍的明眸裡掩映著天使般的悲傷,而這股悲傷也曾出現在絞架上那位小男孩的臉上。我該跟他說些什麼?提起他的另一個猶太手足,那位容貌可能與他神似、用十字架征服全世界的受難者?我該告訴他,他眼中的絆腳石卻是我心中的基石?告訴他十字架與人類受難的關聯,這些或許能讓他找回迷失的信仰?錫安山在焚化爐和死人堆裡重新屹立,猶太國因為數百萬人的犧牲而復活,對此,我們並未流過一滴血、一行淚。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澤。如果上帝是上帝,仲裁普羅大眾是非者依然非祂莫屬。我本該這麼告訴猶太男孩,不過,我只能一邊流淚一邊親吻他。
──弗杭思瓦.莫里亞克【2】
【1】譯注:拉撒路(Lazarus),聖經中的一個乞丐。
【2】編按:弗杭思瓦.莫里亞克(Fran?ois Mauriac, 1885-1970),法國作家,一九五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鼓勵維瑟爾將集中營的慘痛經驗寫成書,並多次親自走訪、書信往來與電話聯繫出版社,終於由「子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付梓,也就是此書《夜》(La Nuit)。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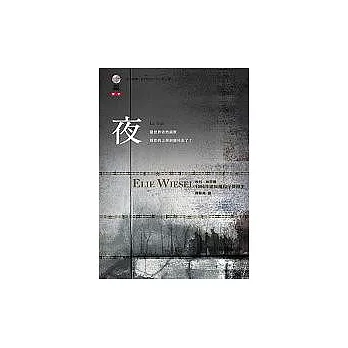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