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如果時代是場電影,噪音就是它最好的配樂
五月,香港SoHo區的一家小酒館,一個春風沉醉的夜晚。仍在籌備之中的《陽光時務》iPad雜誌,想開設一個結合影音的音樂欄目,也想打破規矩,推一首創刊曲,取代發刊詞。於是,向達明一派的黃耀明請教。
生於香港,明哥從小深受西方流行音樂恩澤。如今反觀,眼見處處禁區,處處娛樂,音樂順耳、平滑卻軟弱、屈服。他正在讀張鐵志的《時代的噪音》,感覺新鮮,這些流行與反叛合作,音樂與社運無間的傳奇,在西方已是常識,在中文世界卻未見細緻梳理,也越來越被人遺忘。噪音,不僅象徵一種反抗精神,也是音樂生命力的激流所在。他建議,不如,這個欄目就叫「愛上噪音」吧。
其實,對於一般沒有經歷動蕩波折與浪漫疼痛,成長於沉悶的九○年代的大陸年輕世代,對音樂的印象和想像,大部分沒有超出小虎隊的年少青澀,四大天王的扮酷扮深情,再來就是卡拉OK流行歌曲的集體陶醉。即使少年老成,也鮮有機會逃脫枷鎖,即使青春逃跑,也難以找到叛逆的航程。承上啟下,無處呻吟。彷彿那些激盪過人心的音樂,從未出世。直到有一天,聽到一些不一樣的音樂。
第一次聽到周雲蓬的〈中國孩子〉,聽到左小祖咒的〈苦鬼〉,那種震顫是來自內心深處的釋放感。那被欺瞞被壓抑的,也在這種震顫中得到些許救贖。
從這些不與主旋律兼容但依然悅耳動聽的音樂,順藤摸瓜,原來,曾經有過那麼多出眾的樂隊、歌手,曾經做過那麼多不一樣的音樂。九○年代,噪音都被鎖進抽屜,打入鐵牢,人民被洗耳,進而被洗腦。如今,他們默默作著自己的噪音,唱著自己的心曲,雖千萬人不知,獨自彈而從容。
對於香港和台灣的年輕人,他們要比大陸的年輕一代幸運,但也遭遇另外的壓抑,比如商業化和全球化帶來的冷漠,比如大陸經濟和政治的衝擊帶來的畏懼。
好的音樂,從來不只一個層次,就像自由。不同層次的疊加、交流、共存,才是永不沉悶的音樂,才有永不沉淪的自由。
西方的流行音樂史,按照明哥的說法,就是一次又一次青春騷動的出走。每一次出走,都是一次跨越,都是世代和社會在做自我更新。西方流行音樂影響和介入社會的歷史,其實都還是熱騰騰的當代史,Madonna和Lady GaGa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在各地仍引起不少的騷動,還有被取消的危險。
沒有一支重要的歐美樂隊是從水泥地裡蹦出來的,他們都從各類「時代的噪音」中獲得滋養與激發,找到自己的層次,衝撞出另外的層次。流行音樂,原是反抗慣性的製度和舊有的倫理,加持人心對自由的嚮往。即使商業即使消費,也要突破也要挑戰,Never being boring.
今年是英女皇登基60週年,而早在1977年龐克興起的時候,英國的Sex Pistols就唱出了反建制的God Save the Queen,改編了英國的國歌,批判英國君主制度。而過了35年,加拿大的Neil Young在剛出版的新唱片,亦重新翻唱,繼續跟英國的君主制度開玩笑。
可喜,在兩岸三地,越來越多這樣特立獨行的噪音出現,在「愛上噪音」這個欄目創辦一年之際,網羅了這樣一些勇敢之聲、青春的騷動:
在中國愛上噪音
在2011年七月溫州動車事件後,中國「小清新」派歌手邵夷貝寫下〈正確死亡指南〉,哀悼被掩埋的亡靈。
一首〈苦鬼〉,左小祖咒唱了十二年。1999年、2004年、2010年、2011年,唱了四個版本,音樂不斷改變,歌詞卻隻字未動。1999年他唱:「人民被迫投降,人民越級上訪」,2011年的中國現實,一切如舊。左小說:「我希望它過時,我希望它只是個應景歌曲。」可糟糕的是,到了今天,越來越多的人愛上了這首歌。在樂清村村長錢雲會疑似遭人謀殺後,左小祖咒為艾未未紀錄片中的村長之父配上搖滾樂——〈我的兒子叫錢雲會〉,震懾人心。
年輕人被迫關注公共事務,因為時事與自己和身邊人的性命攸關。火紅的石家莊搖滾樂隊「萬能青年旅店」就是最好的例子。在他們的歌詞中,蔓延黑暗的意象,因為確實是「他媽的苦逼」。他們用誠實而且充滿理想色彩的音樂,招待全世界的青年。
特立獨行乖張詭異的「二手玫瑰」,在俗豔的外表下告訴你什麼是大俗大雅、它的反諷和不妥協、壓抑許久噴薄而出的憤怒,以及隱藏在謙遜之下的傲慢。
蘇陽的〈像草一樣〉是土鳳凰的涅槃。寧夏口音還在,土咄咄的農民腔還在,卻變成了歌唱性的,變成了吶喊,變成了剖開胸膛來向你掏出心肺。
來自新疆的馬條,只要給他一把吉他,就是把他丟進雪地裡,他也會給你折騰得熱氣騰騰。他的〈切蛋糕〉明顯開始了對現實的全面介入與批判。
吳虹飛為中國維權者譚作人唱〈冷兵器〉:「你從來不是國家的敵人,你只是一個囚徒……如果我們在世上繼續醉生夢死,這是否會讓你感到孤獨。」因為她說,譚作人很像個冷兵器時代的人,一刀下去就會見血。而,音樂比政權更複雜,比現實更重要。
來香港幾次,走南闖北的民謠歌手周雲蓬已從細節中,捕捉到香港大陸化的痕跡,也從觀眾的反應中,知悉香港人生活近年被地產霸權擠迫的無奈。於是他即興唱作了〈買房子〉的香港版〈買房子&賣房子〉。
在香港愛上噪音
年輕樂隊C AllStar在歌中追問:香港(小島)沒落或本土價值消逝,我們在其中還有什麼剩下呢?而最危機的情況,「其實是對這座城市不再有感覺。」
黃耀明的〈下流〉好像一首舞曲、一場慶祝,但是它裡面講的全是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的矛盾。但多一點的矛盾,多一點的反思,才是他認為音樂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達明一派每隔十年唱一次「江湖排行榜」,而沒有下一位可以代替此先鋒位置,相信鄧小平可以安坐此位至五十年不變,甚至更久,「五十年不變」在這方面由達明一派落實了!他們今年重組開演唱會推出的新歌It’s My Party,誠如填詞人周耀輝所言,基本上就是號召大家一起以狂歡去對抗現實,以樂趣去對抗政治的一首歌。
在台灣愛上噪音
在〈沒關係〉這首歌裡,巴奈緩緩地唱:「我親愛的孩子,摔了跤、考試考50幾分,沒關係,但山垮了、海灘被賣了、風被污染了、心被利益收買了,我無法昧著良心對妳說:沒關係!」萬籟俱寂,時空中唯有她輕柔的歌聲迴盪著。
胡德夫的〈撕裂我吧〉,是對於台灣社會當中歷史情結、政治分裂與社會矛盾彼此之間層層疊疊的相互角力、牽絆,繼而互為掩映的一組洞察隱喻。
張睿銓在2009年出版的一張為緬甸和翁山蘇姬特別製作的音樂合輯:《Free Burma:獻給被拘禁中的自由》中。這是台灣第一張聲援國際人權的音樂專輯。
就如崔健所說,文藝失去了批判,就只剩娛樂。我們慶幸,還有這些噪音,它們被年輕世代重新發現,激勵噪音精神傳承下去。
每個有動力的社會,都傾聽和包容青春騷動的噪音。那些被主流蔑視和壓抑、侮辱和損害的,是不正常的社會裡每一個正常的人所必需的營養。他們等待噪音降臨的一刻,重重的推開那扇鐵門。因此,如果時代是場電影,噪音就是它最好的配樂。
文/ 柴子文
前言一
「我要抗議」:台灣音樂的異議之聲
當黑名單工作室在1989年唱出「我要抗議」時,就宣示了一個不同時代來臨了。
從七○年代開始,民間社會從長久的政治禁錮之中日益騷動,一個新世代開始回歸現實,反思本土,追求政治改革。七○年代中的一場左翼民歌運動呼應了這個時代精神,主張「唱自己的歌」,並且要實踐民歌的原始意義──走向民間和人民。然而,寫下「美麗島」的李雙澤不幸意外過世;他的好友胡德夫接下歌唱美麗島的火炬,並在八○年代初開始投入原住民運動;另一位也嘗試用民歌去介入社會運動的歌手楊祖珺,卻在主流傳播體制中遭到威權體制打壓,逼著她只能直接投入政治運動。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那個時代乍現的光芒關上了肅煞的鐵門。但這場巨大的暴力鎮壓並沒有讓已然胎動的台灣社會往回走。進入八○年代,政治和社會運動更一波接一波撼動著既有體制和人民的思想。只是國家仍然僅僅控制言論自由,所以難有豐盛的文化抗議,尤其流行音樂。
八○年代前期最具龐大社會輻射力的音樂人當然是羅大佑。不過,羅大佑對時代的歌唱除了「亞細亞的孤兒」這個巨大命題外,更多的只是對台灣剛進入現代性社會的反思,而不是深刻地介入當時正在燃燒的各種社會矛盾。
直到1987年廢除將近四十年的戒嚴體制,台灣開始邁向民主化,才終於出現政治批判的噪音。黑名單工作室的專輯《抓狂歌》是後解嚴時期那個爆炸時代的巨大原聲帶。在專輯製作過程中,經歷了1988年五二○農運的街頭流血、1989年四月的鄭南榕為言論自由自焚,和始終不斷的街頭躁動,靈魂人物王明輝清楚地表示,這張專輯就是希望拉抬整個反對運動的力量。於是在「民主阿草」中,他們大聲唱著:「我要抗議,我要抗議」。兩年後,深受抓狂歌影響的學生歌手朱約信出版了一張抗議民謠專輯,清楚標舉「一個青年抗議歌手的誕生」。
黑名單工作室與朱約信都屬於一個音樂新運動,這個運動的參與者還包括陳明章、林暐哲、伍佰、林強、趙一豪等。他們一方面承接了八○年代後期由水晶唱片推動的「新音樂運動」,另方面在「抓狂歌」之後轉化為「新台語歌」運動,因而創造了台灣流行音樂開始以來的最重要革命:非主流的音樂元素,社會寫實主義的歌詞,並且用台語演唱──在那個政治禁忌剛解放的年代,使用過去被黨國壓抑的台語,就是一種挑戰主流文化霸權的姿態,而本土化很快成為九○年代的時代精神。
新台語歌吹響九○年代的號角,而台灣的民主化工程也逐漸完成,抗議之聲開始更眾聲喧嘩。尤其八○年代末、九○年代初成形的學運世代開始在藝術上發聲,最重要的是濁水溪公社、黑手那卡西、從觀子音樂坑轉化的交工樂隊,以及包括零與解放組織在內的噪音藝術運動。
例如,學生樂隊觀子音樂坑的客家年輕人們不想做傳統的搖滾樂隊,而嘗試走入民眾社區、走入農村,尤其參與從93年開始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主唱林生祥在退伍之後回到故鄉美濃和鍾永豐、陳冠宇等人成立交工樂隊,讓音樂成為美濃反水庫運動的文化實踐。兩千年之後,交工樂隊開始把焦點更放在台灣農村,發表經典史詩專輯《菊花夜行軍》。交工解散之後,林生祥和鍾永豐繼續一系列的音樂合作,尤其成為農村文化的重要音樂實踐,陳冠宇也和夥伴在海岸農村參與農作,並發表相關作品。
在九○年代,除了上述樂隊,同志專輯「撫摸」、書寫台灣史的金屬樂隊「閃靈」,以及其他環境和人權音樂,都接連在音樂舞台上演,雖然為數甚少。1999年,台灣工運團體勞工陣線出版了工運歌曲合輯《勞工搖籃曲》,次年人權團體台灣人權促進會出版了《美麗之島人之島》合輯,這兩張堪稱台灣最早的社運專輯,也總結了上一個十年的抗議之聲。
兩千年之後,獨立廠牌湧現,大型搖滾音樂節的人氣更旺,台灣獨立音樂場景似乎更為熱鬧。而約莫是2004年之後,音樂和社會運動的結合日益頻繁。不僅參與的音樂人更多,且相對於以往大多是少數樂隊個別性地參與,此時更多以集體行動來參與社會議題:去樂生療養院的大樹下演唱溫柔的情歌和激烈的戰歌、和環保組織合作推動「愛音樂、救沙灘」行動、或者呼籲媒體公共化等各種議題。此後音樂和社會運動的結合更為頻繁,不論大小的社運活動都會舉辦音樂會。
此外,2008年,一群獨立音樂人出版了一張獻給翁山蘇姬的合輯,並在2011年復刻出版,這是台灣為國際人權第一次出版合輯,收錄了許多重要獨立音樂人的作品。該年年底則有二十多個音樂人參加了由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所組織的紀念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的各種演唱會。
這些場合中除了前述九○年代的三支樂隊,也出現新一批活躍的音樂人。
原住民歌手巴奈在2000年出版專輯《泥娃娃》後,回到故鄉台東,積極參與台東當地以及台灣各地的原住民權益運動和環境運動,透過她的動人歌聲讓更多人認識東海岸的美麗與哀傷。
嘻哈世代的張睿銓和樂隊拷秋勤則體現八○後世代的矛盾:一方面參與各種社會運動,書寫具有強烈社會意識的歌詞,另方面他們也和潮流文化緊密結合,以吸引更多不同年輕人加入反抗的陣營。
標榜來自農村的「農村武裝青年」是一隻毫不妥協的戰鬥樂隊。第一張專輯《幹政府》充滿憤怒情緒,整張專輯紀錄了台灣過去三年的各種重要抗議運動。第二張專輯「還我土地」則是在進行了數個月農村問題調查之後,提出了一份音樂報告。這三年,他們馬不停蹄在抗爭現場演唱,但也逐漸想要改變這種抗爭現場音樂會的傳統且固定的模式,尋找新的音樂與抗議的接合可能性,例如兒童教育。
青年之外,胡德夫從七○年代至今,始終用音樂和行動在關注原住民與這座美麗島命運:八○年代他為原住民礦工和蘭嶼反核廢運動而寫,九○年代後期他投入九二一重建運動,而在最近這幾年他更是繼續為這個受傷的島嶼、為被權力和貪婪所撕裂的大地而歌唱。從八○年代開始在街頭歌唱的陳明章也不懈地為這塊土地而唱,並且也是毫不妥協地聲援各種社會運動,甚至為中國民主運動寫下「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於是,在這個矛盾的時代,來自不同世代的音樂人,在這個美麗島的不同角落,為了這個島嶼號稱民主化下的各種陰暗面,繼續發出噪音,並且越來越洪亮。
文/張鐵志
前言二
中國搖滾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1994年,崔健推出《紅旗下的蛋》,至今我仍認為這是崔健最出色的一張唱片,然而當時在圈內和大眾中得到的反應和評價卻明顯不如《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解決》。記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一句對崔健的經典評論:「我們都畢業了,他還在罵班主任。」
這就是為什麼崔健卓然獨立於當時整個搖滾圈,甚至把他和同期的搖滾樂隊和歌手相提並論都簡直是對他的侮辱。恭喜那些中國搖滾畢業生,他們無非就想著畢業能找個好飯碗而已。中國搖滾盛世從來都是意淫出來的,「中國火」也好,「中國搖滾樂勢力」也好,「魔岩三傑」也好,都是包裝紙、保鮮膜而已。
只有崔健是一尾獨自活蹦亂跳的大魚,無需魚塘飼養。所謂抗議或反抗,必須先明確何謂自我,何謂他者,要抗誰,要議誰,要反誰?必須先明確自己的身分,認識所處的環境,不獨立,何談抗議?這種獨立不僅僅是思想的獨立,政治社會意識的獨立,還是商業上的獨立,當年只有崔健是獨力殺出自己一條血路,也只有他始終擁有自己的團隊和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發展和運營模式。
恰好,伴隨著商業社會的來臨和消費主義潮流的來襲,中國搖滾載浮載沉。八、九○
年代的中國藝術家見過玫瑰,見過槍砲,卻沒見過錢,他們沒有意識到,一不留神,自己那一腔叛血便被鈔票給輕輕抹掉了。
將搖滾納入商業的魔岩式造神,對樂迷來說,至今仍不乏啟蒙勵志價值,但對當事人來說,卻是一個美麗的陷阱。盛志民講述魔岩時代的紀錄片《再見,烏托邦》,其實面對的是一個脆弱不堪的烏托邦,雖然似乎未經商業玷污,可也經不起商業的考驗,那樣的烏托邦更像是一個玻璃花瓶。那個時代的藝術家,一方面面對商業而擺出清高姿態,另一方面又被商業狠狠打了激素——但或許僅僅是雞血——自身與體制的關係搖擺不定,也就難以保持反抗的能量,甚至難以確定反抗的方向。
在西方語境中,搖滾樂反文化與商業體制始終有一種反噬和反哺的關係,反文化可以經由商業體制順利轉化為商品得以傳播,但在華人世界,受制於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今政治意識形態,二者當然難以形成如此親密的關係。
紀德堡(Guy Debord)說:「反抗,可能就是你所要反抗的裝置分配給你的一份職業而已。」但在中國、香港和台灣,反抗的裝置,甚至絕不會輕易分配給你這樣一份「反抗」的美好差事。何勇當年大罵四大天王是小丑,那是一種本能的反抗,而魔岩處心積慮地推波助瀾,一方面策動媒體炒作,推銷這種搖滾反抗姿態,一方面又通過大量贈票,在紅磡成功製造一個九七前的搖滾愛國主義神話,這是一種經過商業包裝的職業的反抗,可惜這種反抗的職業在中國難以為繼,當何勇繼續口無遮攔在北京舞台上開「勞動模範」的玩笑,下場只能是禁演。
前不久在北京,和崔健、趙一豪一起聊到華人社會的道德保守與虛偽。作為魔岩簽約的第一位藝人,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是台灣最後一張被禁的唱片,在那個時代,其搖滾生涯差不多是以自殺的方式開始的。而林強也是在當年剛剛獲得閩南語流行天王巨星地位後不久,便以一張名為《娛樂世界》的專輯與流行歌壇決裂。這是以反抗的姿態自殺,或者說,以自殺的方式反抗。
而當年不少搖滾老砲,抱怨崔健、何勇連累大家集體自殺,或者說砸了大夥兒的飯碗——畢業之後找不到鐵飯碗,學校之外到處都是垃圾場。他們是把自己的荷爾蒙當飯吃,但這些荷爾蒙甚至來不及做成罐頭,就白白地流失了。這時候他們才發現,整個極權社會也是一所鐵律森嚴的學校,每個人都得在這兒活到老學到老,每個人都是留級生。
只不過有時候,班主任會從一個滿嘴口臭、動輒把唾沫噴到你臉上的老頭,變成一個嗲聲嗲氣、豐乳翹臀的美女教師。這就是我們的時代:從坦克裡施施然走出一個S型美女,消費主義女神似乎可以帶領我們越獄,然而她也可能把你拐進一個瘋人院,在那裡,絞架被做成鞦韆,斷頭台換成充氣床,哦~歡迎搖滾鬥士們來此盪鞦韆,蹦蹦床。
《紅旗下的蛋》一開頭以一首歇斯底里的〈飛了〉,狠狠劃開時代分裂的口子:單向度的反抗已經獨力難支,搖滾英雄鬥士的形像已經開始分崩離析,自上而下的啟蒙幻覺已經開始破滅。搖滾樂文化尷尬地在政治與商業的夾縫之中左衝右突。但也慢慢學會左摟右抱。時至今日,當搖滾樂已越來越成為娛樂消費和假日休閒的樂園,所謂反抗,所謂搖滾的反文化又顯得不合時宜了,假如說老砲們還曾經哭著喊著要逃課,要罷課,要燒課本,甚至要揍班主任,那麼,新一代滾友似乎都意識不到班主任的存在了,只要班主任允許他們玩遊戲「過家家」,他們也心甘情願在學校裡一直待下去,嗨下去。
崔健在七、八年前再次精準地預言和剖析了新時代的本質。他看到雲南有一種□色的草,長得很漂亮,並且繁殖力強盛,但卻飽含毒素,所到之處吸血一般吸取土地的營養造成土地沙漠化,最後自己也死了,與土地同歸於盡。這死亡之花啟發他寫下〈陽光下的夢〉,這首歌不單至今仍未正式錄製發表,甚至歌詞也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修改,至今仍未最終確定,但除了執著而詩意地反覆高歌「陽光下的夢」,還有一句冷酷的歌詞不變:「幸福是一個溫暖的坑」。這揭示了大國崛起經濟奇蹟背後的真相,也揭下了消費主義娛樂文化的假面。
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已經如膠似漆地合體,而政治戴上了商業的面具,這就是新時代巨大的迷惑性。在魔岩時代,中國搖滾樂迷絕大多數是通過那張紅磡《中國搖滾樂勢力》的VCD接觸搖滾現場的,而如今,每年國內的搖滾音樂節已經多達數以百計,這是百倍的繁榮,但也是百倍的虛假繁榮。相當多的音樂節屬於資金運作不透明的政府行為,甚至有些堪稱替政府洗錢。另一方面,對搖滾樂的審查越來越變本加厲——消費式維穩或維穩式消費,正是眼下中國的雙頭怪獸。
2011年4月在周莊音樂節上,左小祖咒上台前,觀眾不斷高呼艾未未的名字,左小祖咒並沒有在舞台上提及艾未未,也沒有唱敏感歌曲,但幾天之後,他卻被警方扣留審查。2012年5月在西湖音樂節上,痛仰樂隊上台前觀眾不斷高呼「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那是痛仰的成名作,但最終他們沒有唱,這首歌至少在北京屬於禁歌。
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句話的作者並不是痛仰,毛澤東應該向這隻搖滾樂隊收取版稅。
假如中國搖滾樂還要繼續擁有反抗的激情和能量,那麼,就必須直面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合體這一雙頭巨獸,把溫暖的坑,重新變成燃燒的戰壕。
2012年5月9日,是崔健首唱〈一無所有〉26週年,也是中國搖滾的26歲生日。崔健交響搖滾演唱會3D電影《超越那一天》的片方,在萬達電影城舉辦了一場紀念會兼電影試映會。原本電影名為《一無所有》,崔健將這首歌放在最後,並在最後打上一句字幕:現在,我們依然一無所有。電影局當然識破了他的險惡用心,一槍斃之。
26年過去,我們不單依然一無所有,甚至沒有表達一無所有的權利。
而就在看這部電影,就在紀念中國搖滾誕生的時候,我收到一個簡訊,出版公司編輯通知我:由於擔心內容敏感,他們決定放棄我的書稿。這部書稿名為:《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文/張曉舟
前言三
香港抗議歌謠前史
香港人曾一度自豪地稱自己的城市為「抗議之都」,又稱「投訴之都」,抗議或者投訴,都是公民權利——行使這種權利的公民,在某政府眼裡就是「刁民」,南粵多刁民,香港獨承之,這的確值得自豪。不算省港大罷工,抗議之都從六七「暴動」、反對天星小輪加價開始抗議,到六○年代末至七○年代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保釣運動、金禧運動等,開始變得專業化、運動化,到八九六四演進到最大規模,九○年代以降,抗議變得日常化,逢週末幾乎都有遊行示威,2005年的反WTO運動又帶來一變,抗議變得更有想像力,更年輕化。
在這樣的背景及核心需要中,香港的流行音樂和民謠,開始不自覺或自覺地承擔起為抗議發聲甚至引領抗議的作用。前殖民地政府改革前的管治下,中低階層華人社會民怨沸騰,以至於粵語流行曲剛誕生就與「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曲相左,明顯更貼近生活而不是幻想。
粵語流行曲真正有創作獨立性的歌手,乃是許冠傑,七○年代率領粵語歌曲佔據歌壇的主流地位,除了因為使用香港人母語創作,其內容的本土化也功不可沒。許氏兄弟的創作與他們本身所出的西化中產家庭關係不大,卻緊貼香港中低下階層生活,部分歌曲甚至帶有強烈的左派色彩、抗議訴求明確。最著名的有〈半斤八兩〉、〈加價熱潮〉、〈賣身契〉,用語「低俗」潑辣,針砭時弊,為當時深受資本剝削和物價通脹雙重壓迫的打工仔階層熱愛。這些歌曲的誕生,固然和唱片公司的營銷策略有關,但也不可不說是許冠傑等七○年代青年知識分子受西方六○年代左翼思潮影響,他們的歌詞去除譁眾取寵成分後,很接近美國藍領民謠,他們的音樂許多直接取用五、六○年代的早期ROCK & ROLL名曲,從身體節奏上營造出強烈的煽動性,也是音樂的另一種解放功能。
當時與許氏兄弟音樂風格相近的還有泰迪羅賓和花花公子(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樂隊、溫拿樂隊等,但內容的激進遠差於前者。遺憾的是,隨著八○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社會富裕程度上升,同時帶來低下階層「香港夢」的造夢潮流,流行曲中的憤怒、抱怨成分息微,靡靡情歌及勵志歌曲一統天下了。然而,就在這樣無可救藥的腐敗氛圍中,「黑鳥」橫空出現。
黑鳥樂隊是整個香港抗議音樂史最重要的一支樂隊,創始人郭達年與Cassi,最早始於1979年與左翼前衛劇團「民眾劇場」的演出,1984年出版第一個作品《東方紅/給九七代》,他們的立場是無政府主義,從作品名字可見他們對極權的反諷和與大時代中香港命運的緊貼,八九六四之後他們出版的作品《民眾擁有力量》震耳欲聾,出離當時反映六四的流行曲的悲情,直達六四運動的人民抗爭本質。黑鳥以大量的創作、現場演出以及地下出版物《黑鳥通訊》,對那一代香港叛逆青年文化造成巨大影響,其接近Patti Smith的知性龐克音樂風格,對某些地下樂隊也有影響。
1999年黑鳥宣布解散,但郭達年等人依舊活躍在香港的社運前線。2007年他們出版了《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唱片加書和唱片合集《BODY OF WORK1984-2004黑鳥全集》,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可視為香港抗爭文化的「野史」。
與黑鳥同期稍後的前衛音樂單位還有彼得小話、盒子,他們的藝術水平甚高,但影響基本局限在實驗藝術的圈子,對一般音樂受眾和社運幾無影響。相反,能與黑鳥的反叛、社會介入發生呼應的聲音出現在主流樂壇,八○年代末開始的樂隊熱潮,其中最重要的兩把聲音:Beyond和達明一派,在成為潮流寵兒之餘,沒有忘記搖滾樂的社會責任。
Beyond的反叛性在另類文化界看來也許非常保守和主流,他們的音樂傾向流行金屬,歌詞大而化之觸及一些普世價值(如〈AMANI〉),直到與填詞人劉卓輝的合作,才出現了〈長城〉、〈大地〉等具有深厚歷史感、反思和批判性的作品。但Beyond對青年文化的影響當時無人能及,起碼樹立了搖滾樂相當於「樂與怒」這一觀念,怒則發聲,這就是抗議、抗爭的基礎。
達明一派和黑鳥的尖銳直接非常不同,但他們的意義相近,就是拓闊了抗爭文化的光譜。在表面的摩登形象掩蓋下,達明一派其實與香港前衛藝術——尤其是進念二十面體關係密切,在後者的影響和需求下,達明一派創作出大量張揚另類權利的歌曲,比較突出的有,與周耀輝等詞人合作的暗示爭取同性戀權益的歌曲、反核歌曲、政治諷喻歌曲,歌詞的敏感與音樂的華麗頹美恰成一體,在抗爭文化中樹立起另一種美學:溫柔的反抗。達明一派的風格孤高脫俗,對底層沒有煽動性,但卻開啟了反叛文藝青年的萬花筒:讓這些香港未來的中產也能意識到抗爭的必然性、抗爭的多元性,比如說同性戀議題或反核議題下,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承受的也許是同樣的壓力。
在九○年代,黑鳥的直接繼承者,誰也想不到,是黃秋生。黃秋生是搖滾迷,他出版的幾張專輯如《地痞搖滾》等深受黑鳥風格的影響,他甚至多次與黑鳥同台演出。因為黃秋生的公眾明星身分,他的音樂傳遞的訊息能更直接進入某些與社運絕緣的耳朵裡。黃秋生一時還成為粗口搖滾的代名詞,與他同時享有這聲譽的是Hip Hop樂隊大禮堂LMF,粗口是憤怒發洩的方式,同時也象徵了底層、草根的立場,更成為傳媒的關注焦點,從這個角度來看是抗議音樂的一種正面力量,樂隊也希望受眾超越表面的粗口與洩憤,關注到內裡表達的青年人困境與不滿。更主流的說唱樂隊還有一支「軟硬天師」,他們更為接近摩登文化,消費後者之餘尚能帶出對社會異象的嬉笑怒罵。
九○年代中後期,受NIRVANA等美國Grunge音樂影響,香港的音樂稍有復興跡象,但多流於發洩青年力比多而已。唯一一支曇花一現、但富於政治激情的樂隊是「午夜飛行」,由原來的香港電子音樂實驗者Simon Ho組建,他有明確的民主派立場,午夜飛行的歌詞有鮮明辛辣的政治諷刺意味,配合簡潔直接的龐克曲風,很適合抗爭歌唱。Simon Ho後來仍回到實驗音樂,做出了很具水準的極簡主義作品,但放棄了龐克的直接激情。
九○年代末,「噪音合作社」及其在「零零年代」的後續團體「迷你噪音」的出現,意味著香港的抗議音樂進入新的階段——抗議重新回到抗爭的主動性和充沛內蘊,真正接續黑鳥精神。他們的活動方式比起前述與流行樂壇脫不了關係的音樂單位更多了游擊隊的特性,因此更自由、更犀利。也因為樂隊本身就是社運成員,音樂直接出自抗爭運動之中,樂隊主力Billy所創作的不少關於工人權益和公民抗爭的歌曲,與當年黑鳥的〈民眾擁有力量〉一起成為了新時代遊行抗爭的必唱曲目。至於迷你噪音在音樂豐富變化上的拓展,更符合新世代快樂抗爭原則,亦啟發更多樣化的意見表述方式,充分證明了一點:想像力的解放與現實解放息息相關。
跟上來的,還有更多的年輕人,my little airport、香港投訴合唱團等團體訴求雖然不一,但都懂得充分利用網路連絡青年文化的優勢,歌者與聆聽者之間的關係更為互動,他們所開啟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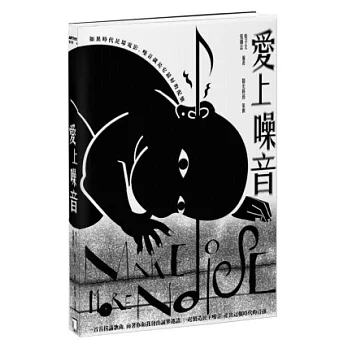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