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邪惡的可能性驅魔---南方朔 近年來,我讀過無數討論德國納粹的著作,但論深度與細膩的程度,沒有任何一本著作能出這部《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之右。《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將來一定會被證明是一部永恆的良心經典,見證著一個邪惡政權與集體瘋狂時代興起的深層原因。
今(二○○五)年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週年,跨全球的紀年活動,已由年初在波蘭舉行的奧許維茨集中營解放六十週年揭開了序幕。再
接下來,歐、美、中、日等國還陸續會有許多其他的紀念活動。而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日本軍國主義以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這三個邪惡的政治極端主義的興起,則無疑的是禍首元凶。
然而,要解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謎,人類終極必須質疑並揭露的,乃是這些政治極端主義為什麼會興起?怎麼興起?它是如何的改變了人們的認知與心靈,因而創造出一個集體瘋狂、自毀毀人的時代等問題的奧祕。當年,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因為拒絕納粹而流亡,他說過:「政治只和極少數人有關,但卻會毀掉全部人的生活。」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要先理解這種集體毀滅衝動的源起、它的肌理和整個邏輯。
而賽巴斯提安.哈夫納這部前半生的回憶錄,就是回答上述問題最有力的著作。他的年齡,使他在幼年、少年和青年時期,先後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二三年的通貨膨脹以及前納粹時期的政治動盪,最後終於看到了希特勒和納粹的興起。感覺敏銳、觀察細膩的他,早在真正的納粹災難形成前,就已從它的動作、性格、思維方式,甚至語言象徵裡,知道了它會走往什麼方向。後來,他於一九三八年流亡英國,這部前半生回憶錄完成於一九三九年。其中著墨最多的,即是希特勒竄起,出任總理的一九三三年。在這一年,他就已深刻的認知到一場巨大的時代災難已開始了它的預演。在這一年,他剛好二十六歲,剛剛參加並通過中級司法文官考試。
展讀《一個德國人的故事》,最具有價值的,乃是作者那以道德良心為本而形成的超級敏銳觀察力和整體性的判斷力,他能從很小的地方,如語言、動作、象徵、人際互動裡,察覺到納粹興起前後,人們感情與思維方式的走向邪惡化;而除了這種細膩的體悟能力外,他又能非常宏觀的看到,從第一次大戰起,整個德意志民族和集體心靈即被一點一點的蛀蝕,那是一種集體的譫妄,瘋狂但幼稚,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無限的激情與惡意的憤世嫉俗;甚至連語言也都逐漸的整個改造,諸如「獻身投入」、「熱情」、「民族成員」、「本土」、「異類」、「劣等人種」等新語彙開始大量出現。一種以「政治正確」為本的集體暴力心態,其實早在希特勒當權之前,即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九一九年初德皇遜位的亂局裡形成,「只不過還差個希特勒而已」。
因此,《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乃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著作。我們閱讀,有些書可以讓人拓寬視野,有些書足以讓人增廣見聞,有些書則可讓人強化思維的能力,但很少有書能夠像這本書一樣,呈現出整個時代的心靈狀態。時代的朽壞必以集體心靈的朽壞為前提,希特勒這麼一個卑瑣、醜陋、歇斯底里,在任何正常社會裡人們都會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居然會席捲整個時代,這不是希特勒出了問題,而是整個時代的心靈都嚴重的生了病,哈夫納對此即指出:「當這一切可憎、污穢、令人做嘔的事物發揮到了極致,反而產生了不可思議的魅力。」而希特勒即是這種「不可思議的魅力」。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因而可以說是所有討論納粹問題的著作裡最不平凡的一部。近代類似著作和研究已多得有如汗牛充棟,而哈夫納寫這部前半生回憶錄時為一九三九年,當時納粹集中營問題也尚未表面化,但儘管如此,由於他精確的看到了整個時代的心靈狀態變化,它已等於替納粹邪惡的根本做出了罕有其匹的觀照。單單這本著作,在價值上即已勝過後來千百本指控納粹暴政的著作和研究。觀察一個社會或時代,最重要的乃是看集體的心靈。有怎樣的集體心靈,就會形成怎麼樣的時代。一個希特勒成就不了邪惡,邪惡需要千千萬萬個小希特勒來擔當助手。本書在呈現這種時代集體心靈上,可以說已達到了所有歷史著作裡的頂峰。
因此,《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在二○○○年出版後,會造成閱讀界的轟動,並被稱為「當年最有價值的出版品」,其實一點也不難理解。因為它在揭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一九三三年納粹崛起這段時間德國集體心靈狀態時,也等於是在對所有已死的和現在的德國人做著精神上的驅魔。這本書把那段時間,德國人集體中魔的過程,如好戰、歇斯底里、逐漸的雙重標準化以及虛情假義的熱情化,最後自然而然的走向集體的惡意與嗜血,一步步發展的軌跡,做了清楚的展露。傑出的德意志民族,因而日趨卑微,再也問不出對的問題,做不出對的事情,一種盲目的、政治正確的毀滅衝動逐漸成為主流;而所有對生命的尊敬和喜悅、善良仁厚之風、善意、體諒、包容,則一步步銷聲匿跡。這本著作在揭露這些的同時,也將整個德意志向下沉淪過程裡,那些有能力阻擋卻不阻擋,大家在因循、無能、逃避、偽善、茫然的等待中,讓事情加速惡化,卒致魔長道消的因果,做了回顧。因而這部著作對德國人或全世界的人,不也是個重要的提示:那就是,歷史的罪惡其實是很容易出現的,只要人們一放鬆怯懦就等於讓邪惡得到鼓勵,再也無法回頭!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它的作者哈夫納出身於一個自由主義家庭,他善良,對邪惡能夠在它初萌時即有所洞察和反省。因此,從他幼年到青年,看著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在心靈和行為上向下沉淪,他的良知不能接受這些。因而在本書開始,他即指控自己的國家:
「那個國家運用恐怖的威脅,勒令該平民捨棄自己的男女朋友、拋開自己的想法來採納官方的論點。並要求他以自己不習慣的方法來行禮、按照自己不喜歡的模式來吃喝、把閒暇時間用於令自己深惡痛絕的活動、獻身於自己所抗拒的冒險行為,更進而逼迫他否定過去與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須不斷為上述事項公開表達狂熱的興奮與感謝之意。」
於是,因為拒絕接受這些,他遂展開他自稱的以渺小的自我對龐大國家的「決鬥」。而本書即是「決鬥」的記錄。他只有透過這個記錄,始能讓自己的良知不被泯滅;但也因此,他才可留給後人如此一部偉大的心靈著作,讓我們得知一個時代的邪惡,其實是有生命的,它會在人們的鬆懈、冷漠與無知裡快速長大,最後讓每個人都無所遁逃。
我對本書的推崇,不是一般的推崇。近代由於集體的鬆懈與犬儒,人們對邪惡的機制、時代的墮落,已越來越麻木無感,因而各式各樣的邪惡與譫狂又告復熾,它表現在世界的益趨動盪上,也顯露在各式各樣政治極端主義的崛起上。這時候,像《一個德國人的故事》這樣的超重量著作,它豈只是在替德國人驅魔而已,更是向全世界對人心向善還抱有希望者的呼喚啊!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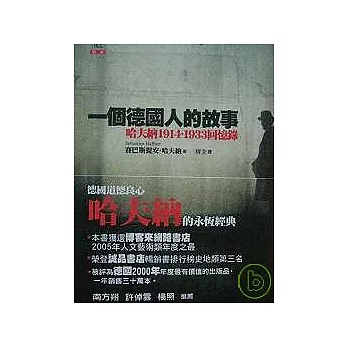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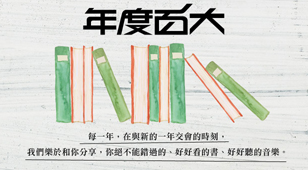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