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論散評皆文心
《舉杯向天笑》像是詩集或散文集的書名,但是?面收集的三十八篇文章,有的可稱正論,有的看似序言實為書評,有的卻是文類的探討,藝術的賞析,不過大體上都可以泛稱評論。緊隨《藍墨水的下游》之後,十年來我的正論散評大致都收羅在此了。
此書之編排以文章之性質為經,而以發表之時序為緯,因為如果全依時序,必定會顯得駁雜不堪。所以分輯是求其性質分明,而每輯的文章則依發表的先後排列。 第一輯十二篇論析的是詩、繪畫、翻譯、語言、文化地理,往往更涉及其間的關係。有不少段落如果當散文甚至美文來讀,也許更好。例如〈邊緣,中心,跨界〉的第四大段,或是〈李白與愛倫坡的時差〉和〈捕光捉影緣底事〉的全文,如果收入我的散文集中,該也不致顯得唐突。正常的論文照理不可以「感情用事」,應該做到cerebral;我的評論不守幫規,時常出軌,演為figurative,但是後面仍是有知性支撐的,要說的道理還是傳過去了。另一項出軌,便是不列註解,不附書目,正文之後沒有「隨扈」,欠缺正式論文的格局。其實多加註解,詳列書目雖然是學術論文的「基本功」,並不是什麼難事。一篇評論真正可貴的是有洞見,與根據這些洞見得來的評斷甚至評價。
艾略特不但是二十世紀的大詩人,更是影響深遠的批評大家。他的許多評論文章都沒有這些註解或書目,但憑了他的高瞻遠矚,憑了他宏恢的文學史甚至文化史觀,憑了他清明的分析與暢達的文筆,他的見解往往深入淺出,令人折服。更重要的是:他雖然不用系統嚴密的理論,更少乞援於繁瑣的術語,但身為重要詩人,僅憑當行本色的創作經驗,說話自然就有權威,至少比一般純學者更有權利。十八世紀的約翰生博士也是如此,短短一段文章,比較朱艾敦與頗普的長短得失,字斟句酌,說理透徹,比喻鮮活,評價精準,一席話勝過百頁的論文。所以能夠如此,除了他博學深思之外,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在詩、散文、小說三方面都有貢獻,因此創作之道能窺其虛實,手既能高,眼必不低。何況一篇評論如果高明得能夠傳後,應該不愁沒有人來註解: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劉勰的《文心雕龍》,都是顯例。
第二輯十三篇全是序言,加上其後第三、第五、第六各輯性質各異的序言,此一文類在本書中共得二十一篇,分量之重已經超過書的一半。其中自序佔了三篇,「他序」最多,佔十六篇,「群序」也有兩篇。他序指為他人出書作序,受序之書從詩集、散文集、評論集到畫冊、譯書和詞典,性質很雜,都是應作者、畫家或出版社之請而寫,可見在《井然有序》一書之後,我的「序債」仍有多重,而文壇學府似乎早有共謀,成了我的討債公司。至於群序則是指為一群作者的龐大選集作序,頭緒就更紛繁,論述也更不易,幸好只有兩篇。
這些序言如果逐一道來,恐怕比寫一篇長序更加辛苦,但是其中有三篇不妨一提。陳幸蕙窮十年之功研究我的詩文,六年來先後由爾雅出版社推出了兩本《悅讀余光中》,分別是詩卷和散文卷,所費心血不下於一部博士論文。我戲稱她似乎成了「余光中的牧師」,熱心傳播「余道」,令我感愧。所以《悅讀余光中》兩卷出版,義不容辭,我當然得寫序以報。不過兩書所論原是我自己的作品,因此我出面為之作序,有點像母雞跟蛋販一起推銷雞蛋:他序變成了半自序。 另外一本是李煒的《書中書—一個中國墨客的告白》。此書是以英文寫成,英文寫得很漂亮,但是英文本迄未出版,卻由余珊珊先譯成中文,先後已在台灣和大陸問世。我的序言是根據他的英文原文寫的:這種反常的作法實為出版史上所罕見,若非僅見。 其實十年來我寫的自序、他序、群序還不止這些。其中自序還應包括王爾德四齣喜劇中譯本和在大陸各地出版的各種選集之前言後語。甚至此刻,我已經答應而迄未兌現的「虛序」,仍有債未清,思之惴惴。我別無他法,只能告訴未來的索序人說:「暫不收件」。
為了慶我八秩生日,今年活動頗頻,其中所謂學術研討會已有兩場:在徐州的一場由香港大學和徐州師範大學合辦,另一場在台北,則由政治大學文學院主持,因此論我的文章忽然出現了好幾十篇。在徐州的研討會上,我在致答謝詞時大放厥詞,說什麼在文學的盈虧帳上,作家是賺錢的人,而評論家是數錢的人。眾學者一時不釋。我進一步說明:作家每寫一篇作品,原則上都為民族的文化增加了一筆財富,但是其值幾何,就需要評論家來評估,也就是數錢了。那一筆「進帳」也許很值錢,也許並不值什麼錢。也許交來的是一筆貸款,是向別的作家借的,甚至是贓款,向人偷的,也許根本是一把贗幣,一疊偽鈔,更不幸的,也許竟是一堆過時的廢票或者冥鈔。同時這一筆錢,幣制混雜,一個人數了還不算,還需要更多人來共數,都肯定了才能定值。所以一位作家僅會賺錢還不夠,最好還能認錢,數錢,不但數別人賺來的錢,更要能數自稱賺來的錢。
余光中 二○○八年八月於左岸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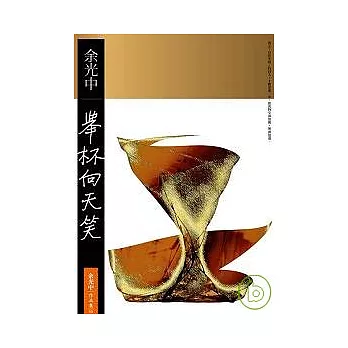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