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不惑以後的道路 林俊穎
一九八九 ~ 一九九三
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秋天,整個世界還在那以單一肉身阻擋一列坦克車的震撼裡,我們倆在一週內先後抵達紐約市。兩個月後,冷戰的陰沉標誌柏林圍牆猝然倒塌。
各自摸索安頓中(強生在曼哈頓,我在皇后區法拉盛),大西洋的天際果然季節轉換明顯,一如鋒刃的薄兮脆亮,地上無有神奇之事。很快的我們見面,我搭七號地點,尖銳車輪聲,溷濁氣味中,四十二街轉R線,八街、紐約大學站鑽出地面,古老的不馴服於城市規劃若靈蛇遊竄的百老匯大街。其實彼此還是生澀的會晤,那個黃昏,我們站在強生華盛頓廣場旁的宿舍露臺眺望落日霞光,旁邊掛有他一件粉紅色襯衫。一百多年前,福婁拜的《情感教育》開場是啟程的輪船上飛快遠離了巴黎,一個年輕人澎湃的夢想著藝術?愛情?世間所有美好?關於此書,福婁拜致友人信寫著:「我要書寫我這一代人的精神史,確切地說是情感史。」
書寫一代人的有形無形之史,我們有那麼高的志向嗎?前程確實遠大,然而我們立足的據點何在?是硬頸的畏友不免幾分譏諷的說法,西方取經?或是因為在盛年的父母的寵愛足夠,無條件支持哪怕只是一場無目的的遠遊?我難免慚惶,比起來強生是更有才智與準備,這一趟來到這世界之都的心,形同阿里巴巴的寶藏洞窟打開大門。
我們一直是淡如水的往來,久久一次相聚,不談文學,不討論寫作,精神暢旺,眼前所有都在上升的色彩與音階,沒有匱乏,沒有磨損,若有缺失唯是我們不努力不用功爭取。那時候,家鄉,異鄉,何惑、傷害、苦痛之有?我們彼此不存在陰暗、祕密、黑箱。我們會面也始終在他紐約大學方圓不到一公里的地區內。世界沒有我們預期的巨大。
永遠的華盛頓廣場,吊人榆蔭裡下西洋棋的閒人,靠北方那茂盛的黃金樹(Western Catalpa)夏天開出如雪花簇;St. Marks Place小街,已是被小日本人攻掠的小攤店面,偶或點綴著龐克族殘餘,令人發噱。傳奇的蘇荷區,曾經馬蹄達達的石頭路猶在,而不景氣的低氣壓罩頂,冬日向晚一片昏暗蕭瑟,適宜孤獨苦思的心靈。
柯林頓繼老布希就職、奧黛麗赫本癌逝前,我返回臺灣。電話辭行,不可能有離情別緒,強生輕快應答,喔要回去了,老是覺得你就在那裡,以後可是隔好遠。返臺之後,在他皇冠雜誌專欄結集的書中,我才讀到其中一年夏天他在靠近Astor Place的宿舍跌傷了腳,乾燥、漂浮著汗臭尿臊且似乎遙遙無止期的暑天,老歌者卡洛金唱著滄桑的〈So Far Away〉陪著他度過了一整個夏天。寂寞繁華皆有意,我想那個大城一直是涵養各種藝術形式奇花異草的沃土,也必然是他的某種意義的烏托邦吧。
一九九五
紐約市的冬天,氣流颳著酷寒,那冰點下的風溫是非常具體、銳利的割著肌膚,我們臨時起義看一部晚場電影,《廿一世紀的前一天》(Strange Days)。進電影院前,強生與一正巧路過的熟人打招呼,道地的美式詞彙與肢體語言。
這次重返紐約,我早一個月到,待從前室友H帶著幾位老友來會合過聖誕節,不得不走觀光路線,一票人摧枯拉朽從世貿雙子星大樓取第五大道到聖派翠克教堂,挺進薄雪覆蓋的中央公園,如同拍翅聒噪的寒鴉,盛夏的草原而今是光禿的白色小丘,更襯出無枝可依的意象;碎冰明晃的小湖沒有一隻水鴨,牠們都到哪裡去了。無人預知死神就悄悄尾隨著我們。
有什麼不可言語的東西確實不再一樣了,包括這折疊著索多瑪的大城的氛圍(《慾望城市》還要三年後才問世;六年後,九一一恐怖攻擊),身為樓叢下螻蟻的我們。冰刃片面的寒冷一時驅逐不了電影製造的暴力躁亂感,我們疾走在少人行的街道,渴望一杯熱飲。愈走倒是愈讓那寒凍逼出清釅的元神,德爾斐神諭:「認識你自己」,或者說我們所欲所求的原型究竟是什麼?
壯年辭世的蘭波──啊,再二年我就到那歲數,強生則還有我的二倍數距──說詩人應該是通靈者,如啟示錄的狂言還是囈語,「必須使各種感覺歷經長期的、廣泛的、有意識的錯軌,各種形式的情愛、痛苦和瘋狂……尋找自我,並為保存自己的精華而飲盡毒藥。在難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堅定的信仰與超人的力量;他與眾不同,將成為偉大的病夫,偉大的罪犯,偉大的詛咒者……」。
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或就是那些瘋狂、痛苦的錯軌形式之數種吧,也或就是找到自我的必飲毒藥吧。更有神話的大鵬金翅鳥,日食一龍王與五百龍,毒發焚身,得一純清琉璃心。
我畢竟對欲求與愛及其變貌的戲劇化,高度戒慎。戒慎的核心,在於我沒有強生的純情與赤子純真。
是以我們走在不一樣的路徑(吧?)。冬天走到這裡,即使有讓銅像僵斃,迫使機場與道路封鎖的暴風雪,不能更壞了。趕路時只聽到彼此咻咻的沉默,沉默中,我們頭頂有天使盤旋飛過(吧?)。然而確如佛斯特的詩,在沉睡之前,我們各自還有好長的不能以哩計的路要走。
還需要再多幾年的時間,再幾次的親履證實,時間帶來蛻變,這個年輕時我們為之顛倒夢想、輕狂也輕諾的城市,一如波赫士之文:「凡是發生在那地區的事情都好像只是個夢,都彷彿發生在水晶球裡似的。」還是更殘忍,《金鎖記》不全然貼切的句子,「將來是要裝在水晶瓶裡雙手捧著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後的愛。」
二○○六 ~ 二○一二
新的世紀開始,我們如何標記,異常悲慘的居然是九一一,那地獄變的浩劫發生時,強生安然無恙的在飛往安克拉治的華航班機上。
隔著浩瀚大洋,老紐約勞倫斯.卜洛克之慨,自此,一切都改變了;如同彗星撞地球歪斜了地心軸線。在島國家鄉,我們不過是拉長了時間曲線,先後經歷了譬如父母一方的辭世,一起領受一、兩位共同好友的殤亡。地球自轉,各自的生命並不因任何的突發、異動而須臾不受時間沖刷。世事確實如常,我們也一如以往在年月的隙縫張望且倉皇,持續在期待時期待,在落空時行禮如儀的吃飯喝酒睡覺偶爾買買樂透。
前後有三年時間,我們常在花蓮見面。山色海風,視野挖空,推廣至能夠隨心野放,我心想這是喚醒書寫種子的所在,如果文學之神還眷顧我們的話。
記得下課後晴朗深夜的花東縱谷上的校園,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的巨靈俯視之下,他興來的好歌喉,唱那一首幾乎算是失傳的老歌,「在這夏日的夜晚,棕櫚透著涼意,我用醉眼看這燈海,輝煌變成迷離,啊,我心在燃燒,不說再見,沒有言語。」彷彿我們青春的繁星,果然伸手可以觸摘,曾經錯失的可以挽回,可以補救。何其美麗的幻覺。
回到臺北,我們記得許多離開好友奇女子朱朱──願她安息,此後我們再也不能如此自夜闇的酒館離開了──的「龍舌蘭」酒吧的夜半,想以長路走散一身的菸霧酒味,在這填塞太多夢想而疲憊不堪的城市,夜氣濁重,尤加利樹上沒有棲息的鳥,收班了的捷運橋墩涎著最後的夜露,天亮有如雛雞在啄殼要破出了,我們不是夜遊神,也不宜再有迷途或徬徨之感,跨過千禧年累積到現在得來的友誼足夠我們瞭解彼此,往後的道路,各自的存在就是提醒。
喜歡與否,我們正一步步走向刪減,人倫的,人際的,由奢入儉。詩經的句子,「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樂見與否,屬於我們時代的永遠的上校之父,那瘋得可以的老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說:「沒關係,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方向。」
因此,這《惑鄉之人》必然是強生寫作志業方向明確的一次重要加法。
書中既是歷史的也是倫常的、一層疊緊扣一層的三角關係連環套,隨著如同颱風半徑座標的故事推移,小說家急於摧毀的「已然事過境遷的無事表層」、急於剝除的「抵達之謎」,是否就是福婁拜的「我要書寫我這一代人的精神史,確切地說是情感史」?那也正是小說家心中的大惑?關於我們島國一百年來的恩怨情仇,關於殖民與被殖民的啟蒙與創傷,認同與身世,或最基底的關於人的追尋與失落。
熱愛電影的小說家彷彿借用了那至今仍令人低迴的《新天堂樂園》的影像,只是要訴說人生如戲?是視覺魔法也是如露亦如電的電影,成了此書的無形魔術師,掌控了一個磁場,牽動了諸要角的生生死死。
強生與我共同記憶之一,現今猶在傳唱的〈橄欖樹〉,有那麼一代人的浪漫大夢是背向家鄉,奔向遠方。而《惑鄉之人》呢,恕我不宜泄露太多,柯律芝奇文:「如果一個人在睡夢中穿越天堂,別人給了他一朵花作為他到過那裡的證明,而他醒來時發現那花在他手中……那麼,會怎麼樣呢?」
請穿越惑鄉,閱讀之旅的終點,我們將發現花在手中。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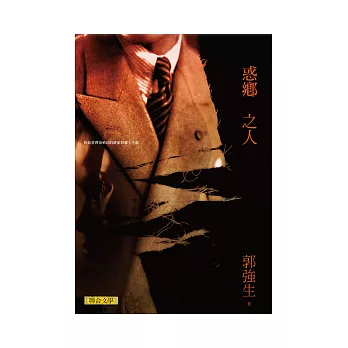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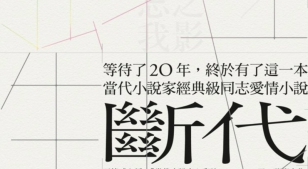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