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詩之神、魅──與羅毓嘉「新詩集」對話
我應該要去找毓嘉,問問近況,問問他進了工作以後,探看的世界還依然世界的模樣嗎?我該問詩人,你睜開嬰兒雙眼後,看到神,看到魅?詩,你在找姓字,你在找名字,你在賦格嗎?你是想站在雲端的女高音?抑或沉入最沉的男低音?
有太多關於詩,我想聽他熾熱熱的靈魂說,他也是想聽我說一些吧?他直覺、衝動地找我,一個偽詩人跟他的詩對話,令我受寵若驚。他的詩對我說了許多,那樣不可能從別的閱讀或別的心靈展開的旋律,我完全沒有能力用我的文字再轉述一次,關於他的詩,其真誠美麗。作為對話者,我若還有什麼能跟他說的,恐怕只有虛長的年歲,碰過較多寫作堅硬棘刺之牆,胸前背後,多了幾道傷口。
時間是詩的拉鋸,詩是時間的線索。
若我們寫作之人,年少時憑一股熱,就管他牆頭多高也不懼拚命沒有下秒鐘似的飆升,反正跌深反彈,身體柔軟如貓,摔落後翻個身,繼續奔跑追逐於文學花園裡的鏡像虛實。特別寫詩,不僅手腳要乾淨俐落,腦袋運轉如夏季風暴,心還得敞開迎接炎陽陣雨,與海浪和天空同作息,這樣每一秒每一刻都想在生活中以詩留下痕跡,青春寫詩,不熱不行。毓嘉已經在上一本詩集做了最佳示範,《嬰兒宇宙》的字句摸來會燙人,他以其獨特的音色,宣告他將不悔不倦帶給我們更多愛與生命的奧祕,並於未來占領他人所無法企及的詩領域。
詩,不就是這樣子的載體嗎?你眼睛看不到,你耳朵聽不見的,你舌根嘗不出味道的,肌膚無能感應的,藉著詩人所擬造的新顏色新聲音,各種神經受器再次被打開,甦醒。毓嘉的詩聯通感很強,突然你會讀著讀著,一陣感受從股端沿著脊椎,直竄腦頂之穴,兩手兩腳也起了雞皮疙瘩,似乎那些經過詩人重塑組合以文字替換的眼前世界、那些無情有情萬事萬物被凝縮在宇宙射線中的微量粒子,輕易可以穿透你的身體,射穿你後將你改變,提升。
特別真是我,這種寫一點點的詩中年,像隻在柏油路面被車輾過,在太陽底下已經曝曬了一星期後的過路青蛙,想要啪啪跳呀跳,跳到路對面的草原和池塘,已經是不可能的。最可能的是有另一輛大卡車經過,帶起一陣風嘯,把黏在熱燙街路的乾枯蛙皮掀翻,踉了幾蹌,幸運的隨風落入池塘,也不會撲通一聲了,而是靜止漂浮於水面,那已經是在詩的路上還能享受到最甘美的禮物與祝福。而毓嘉和他的詩,比這輛大卡車厲害,他們具有讓世界情感起死回生的能耐,我看見自己在柏油路面上,因為他的詩引流灌注如清泉,那僵硬的死皮,竟漸漸恢復了光澤,竟慢慢伸活出四肢,竟抬頭挺胸,竟心動又開始,竟能跳,跳過馬路,跳過草原,撲通跳入池水。
詩不就是該具有如此神蹟式的類宗教性的滲透與靈動。
每個青年詩人一開始摹詩,音色、韻律總離不開其所讀所識前行輩詩人的筆觸,毓嘉的同儕或師友也已指出許多,譬如□弦、楊牧、羅智成、一點商禽和夏宇,我再加一個楊澤詩的神祕感知。然而這本「新詩集」《偽博物誌》,我第二遍以朗讀的方式進行,輕誦呢喃後,確實那些筆跡仍在,但已經不同了,毓嘉直抵的是同這些前輩等高的視野,他已經與他們站成一列觀看。在吟誦過程中,這些詩句突然有波特萊爾寫巴黎城市的憂鬱魅影,也接近里爾克詠物詩之後的神思,詩的視角位置也在這二者之間。里爾克站得高而形上,以其詩人職志,將詩從表象拉升到心靈真實,那是處永恆不被世間侵擾的天境:
……因為美無非是
我們恰巧能夠忍受的恐怖之開端,
我們之所以驚羨它,則因為它寧靜得不屑於
摧毀我們。
(里爾克《杜伊諾哀歌》,綠原譯)
至於憂鬱的巴黎浪蕩子醉倒墮落的姿勢低且深,與城市之華同臥,波特萊爾以詩將爛腐化成生香。
我將獨自把奇異的劍術鍛鍊,
四處尋覓聲韻之偶然;
仿若行走於石子路上,
在字裡行間踉踉蹌蹌,
有時,迎面撞上長久渴望之詩句。
(波特萊爾〈太陽〉,吳錫德譯)
毓嘉凝視世界的眼光正面迎向二十一世紀文明的深處開展,他對個人身上的,城市身上的靜觀,我不想用某些既成的詞彙直說(「說破是破壞,暗示才是創造。」馬拉美),或過多渲染的字語來對看這本新詩集。也不想摘其詩句(要把集中的詩或詩句拆析分解,有我能力不足也不願之處),那會壞了毓嘉在這本詩集進展最完熟的節奏,我推測那是他目前用來穩定自己與穩定詩的最有力支撐。他找到了自己的聲調,因而能自在地歌吟。詩人站在一個新位置,那既是主又是客的雙向互觀,時間與愛的消亡新生在心象內外交融,我是物亦非物,物是我非我,在託物寄語中將生活滌蕩。然而像每個真正的詩人,都是早慧且敏感孤獨於創新之途中。他們看見別人見不到的細節聯繫,物與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他們先於文字,以感官對應極難言說描述的內在究竟發生何種牽連變化,風吹,雨滴,花開,鳥飛,石沉,它們具有意義嗎?如果有,那是什麼?如果沒有,那怎麼證明一個世界的存在?毓嘉竭盡其「通感」能量,鋪陳而出他欲組構的新世紀。
毓嘉詩之穩定,讓我想到楊牧,他們似乎都不必經過青澀時期,直接給人的就是甜熟果實。然我必須說,這本詩集噴湧的曠宇繁花,我只能領略其半(楊牧我大概三分之一)。我第一次用心看,似乎全看懂了(意象);第二遍朗誦兼聆聽,那純屬音樂的旋律(結構);第三遍就是此刻正在寫這篇文章,不得不反覆反覆以分析為前提進行,忽然就失去了整體(語言)。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局限,也提醒我這本詩集很耐讀耐看耐聽。
雖然我未曾真正跟毓嘉聊過天談過地,遑論詩,但從作品中可以完全感受他對寫詩的堅持與懷抱。台灣現代詩的「盛唐」時期似乎過去了,後起新秀所臨之殿堂在現實中或已成廢墟,因此很容易就把詩藝當遊戲。可詩不是格言,或可輕易摘取的警句或文字排列或僅是趣味的形式鋪陳,必得從心裡面去轉折它,才不致亂了內在韻律。當然做練習是可以,哪個段落該讓它傾斜,哪個段落是該和諧,暴跳甚至只是空白的失去聯繫上下詩句,非邏輯性的一躍而縱往深谷或飛向天際,蒙太奇的意象剪接,明暗虛實,把顏色變化一下,把名詞動詞更替,這些好像對詩起了活潑的樣貌,可最終那是遊戲多。在萬花筒裡隨便轉一下,影像多麼華麗與詭奇,但這種驚奇,短暫不長久,你想再看同一次讓你感動的世界,轉,再轉,也轉不出同樣的花色。那是迷障。只有發自內心自在又純然的詩歌,由詩人在經意與不經意的經營之中,情感和文字達到融合,飽滿成一種永遠的契合,那時的詩句,即使在詩人已遠,時代已過,仍是那麼新鮮動容。那時寫詩的人可以體會到一個純淨世界的表述和語言,甚至在哲學與邏輯跟你生存的現世格格不入,但你確實因為創造或閱讀那樣的詩句,而願意相信,生命有其美,生活值得感受與感動。
緊實地說,一個世代只要有幾位,不,哪怕只有一位詩人,能莊重地對待詩對待自己對待世界,那不管瀕臨的是如何破碎的現代廢墟,新世紀都將會於此人心靈之中再現。我相信毓嘉就是這樣的一位。
少年時,詩我迷忘於羅智成;中年時,詩我回神於羅毓嘉。
蔡逸君(作家、《印刻文學生活誌》副總編輯)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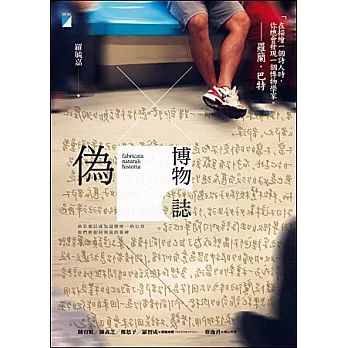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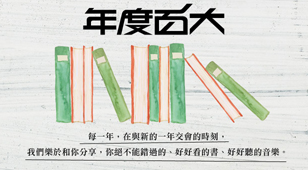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