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導讀
本劇希臘原文為The Bacchae,指的是戴歐尼色斯(Dionysus)的女性信徒。自從公元前三、四世紀以來,尤其是到了羅馬帝國時代,人們就把祂視為酒神,由一群尋歡做樂的仙女、和行為浪蕩的撒特(Satyr)伴隨。這種形象,透過浪漫主義的詩人和畫家,一直流傳到現在。這些藝術家並沒有錯,但是他們只掌握到祂眾多屬性中的一個而已。當然,酒神和酒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這酒富有宗教的意義。耶穌在最後晚餐時祝聖麵包和酒,說它們代表祂的身體和血,門徒飲用後祂就進入他們體內,和他們同在。戴歐尼色斯的酒具有類似的意義,不應與醇酒婦人混為一談。
《戴歐尼色斯的眾多面具》(Masks of Dionysus)一書中寫道:「對古代的希臘人;祂是所有人的所有東西,對我們祂仍然如此。毫無疑問,在所有希臘神祇中,祂最為複雜又最多層面。」(Carpenter, 1)為了解釋酒神和本劇多層面的意義,本文以下分為四大部分:一、對本劇做一般性的介紹;二、以劇本為主要依據,探討戴歐尼色斯的神性和祂的教派;三、綜述近三個世紀來對本劇的代表性解讀,它們的共通點主要是將戴歐尼色斯視為象徵,不是神;四、提出拙見,將本劇當成劇作家對一個社會現象的觀察與反思,從而探索這個劇本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
一、緒論
本劇作家尤瑞皮底斯(Euripides,生卒年代約公元前480-406年),一生創作了八十多個劇本,現在保留的有十七個。本劇約寫於作者去世的前一、兩年,那時他已經離開人文薈萃,但戰亂頻仍、社會紛亂的雅典,接受國勢日盛、但文化低落的馬其頓的邀請,作為國王的上賓。
他死後不久雅典即被迫作城下之盟,隨後的戲劇都是男歡女愛的「新喜劇」。因此,從劇種的變化上看,本劇是一個輝煌時代的壓卷之作;從劇作家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多產作者的天鵝之歌。更重要的是:從今天回顧它的歷史,兩千四百多年以來,它一直令人著迷,又一直令人迷惘,一位學者解釋這是因為它的內涵浩瀚無垠,天上人間,無所不包,以致迄今為止,尚無人能說出一番道理,可以全面詮釋它一層又一層的意義。
本劇共有1392行,最先是開場,然後是歌隊的進場歌,此後分為五場,每場之後有合唱歌,最後是退場。這些場次之間的發展依循著因果關係(causal relationship):前一事件引起後一事件,環環相扣;場次人物與歌隊之間也凝結成一個整體,互動密切。結果是,本劇的結構是如此正式,以致可以視為希臘悲劇的楷模。在語言上劇作家也一反以前自鑄新詞的傾向,大量使用老舊的辭彙,古色古香。成為強烈對照的是它的故事新奇、感情強烈、中心人物的酒神撲朔迷離,由祂設計的殘殺,千古以來仍然駭人聽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尤瑞皮底斯的戲劇最富悲劇性,本劇可當之無愧。
在開場時,酒神以人的形貌,率領了一部分亞洲信徒來到希臘城邦底比斯的王宮之前。祂聲稱祂母親原是當地公主,一度與化身為人的天帝宙斯相愛,後來她受到妒忌的天后慫恿,要求愛人展現本來面目,結果被宙斯如同雷電的天神原形燒為灰燼。那時她已經懷孕,胚胎為宙斯救出,長大後在中東一帶建立了祂的教派。現在祂回到故鄉,目的在展現祂是一位真神,並且招收信徒,建立自己的新教。在同時,祂還要為母親洗刷名譽,因為祂的姨媽等王宮貴婦,一向污衊她行為不檢,未婚懷孕後,就謊言與天帝有雲雨之情,以致遭到雷殛。為了報復,祂來到希臘後就誘迫她們和其他婦女離開家庭,到郊外上山歌舞狂歡。以上這些俱見之於開場白(1-63行,以下「行」字省略),只是戲劇行動的背景。行動真正的展開,是在國王彭休斯進場以後。他強烈反對國內婦女參加酒神儀式,採取嚴厲鎮壓行動,一場驚心動魄的衝突於是展開,最後在酒神的操縱之下,彭休斯遭到母親殺害,他的親人遭到酒神放逐,他的王朝也隨著煙消雲散。全劇在神威無限、神意難料聲中結束。
關於本劇中的戴歐尼色斯,西方歷來的觀點一直隨時代而更易,但基本上可以歸為兩個時期,一是希臘羅馬,二是這時期以後,特別是在十八世紀以後。兩期最大的不同,在前期視戴歐尼色斯為神,而後期則把祂視為一種象徵。哈佛大學的韓瑞克(Albert Henrichs)教授寫道:「戴歐尼色斯有一個基本面,我們作為學術界人士一般都忽視了,那就是:祂的神性(divinity)。」他指出,現代學術注重理念的抽象化或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同時又講求分門別類(compart-mentalization),以致一個多世紀以來,把戴歐尼色斯支解分析,使祂不僅失去神性,而且失去生命。他建議我們用創造戴歐尼色斯的希臘人的眼光,把祂當成一個神。他呼籲:即使我們沒有宗教的虔誠,至少要有文學的想像。
二、本劇的宗教內涵
歷史上以戴歐尼色斯為信仰的教派,大約在公元前十三世紀以前甚至更早,就從中東地區傳播到了希臘。此後希臘的文學作品中,就不斷講述和祂有關的故事。最早是荷馬在他的史詩《伊里亞得》中,提到一位國王追擊祂以致受到宙斯殺害。不過這裡的故事只有短短十幾行,以後相關的作品與記載幾乎只存名目,資訊極少,有關酒神的傳聞反而以本劇最為充實。但本劇是文學作品,不能視為歷史證據。
在尤瑞皮底斯奔放的想像裡,酒神是前面提到的「所有人的所有東西」。祂是神,是人,同時也是獸:劇中提到祂以前曾經是,現在也隨時可以變成一頭牛、一條蛇,或者一隻羊(100、920-922、1018)。祂既是男性,同時也是女性。祂還同時具有其它許多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性質。這種觀察可以遠溯上古,但如今更為流行。哈佛大學的色果(Charles Segal)教授就利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理論,指出邏輯的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是閱讀快感的基礎,而在本劇中俯拾即是。這種雙重性,酒神對自己的說明最為關鍵:「祂最為恐怖,但是對人類也最為慈祥。」(861)
在劇中,酒神主張祂的生命、身分、與力量來自宙斯,祂也遵守宙斯的法則天條,所以嚴格說來,酒神的新教只是原有宗教衍發出來的一個支派(cult)。像所有的宗教或教派一樣,它有自己的教條(dogma)、奧祕(myth),和儀式(rituals)。這些宗教的要件,歌隊一進場就宣告出來。教條的中心是信徒可以獲得「至福」或「滿福」(beatitude)的經驗(73-78);奧祕則環繞著酒神如何誕生(87-100);儀式則見於信徒的服飾、音樂、舞蹈等等。因為這些要件,祂的信徒至少在兩方面可以獲得精神的滿足:(一)參與宗教儀式,獲得幸福感與歸屬感;(二)與神同在,取得超人的力量。
關於第一方面的滿足,歌隊的進場歌就是一個簡單、酣暢、而且充分的說明。關於第二方面的所謂與神同在,則意義非常複雜。其一就是酒神以人的形貌,與信徒一起生活。這種意義的同在貫串全劇。例如:「在祂的國度裡,祂使教友們一起舞蹈,隨著笛聲歡笑;止息憂鬱。」(378-380)另一個意義就是酒神進入信徒體內。在劇中,先知泰瑞西亞斯告訴彭休斯:人類有兩大福祉,一個是大地女神給予人類的「乾的滋養」,一個是酒神介紹給人類「葡萄的流液」,可以使喝過的人們「止歇憂傷」。(274-281)先知接著說:「當我們對神灑祭時,我們倒出的酒就是酒神自己,所以人類是經由祂而獲得福祉。」(283-285)
藉飲酒迎接酒神進入體內,有如基督教的聖餐(the Eucharist)。《約翰福音》記載,耶穌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在最後晚餐中賜給了門徒這個恩典。酒神信徒在儀式中飲酒也可讓酒神進入體內,不過他們注重的不是來生,而是今生今世。
教徒取得超人的力量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常春杖(thyrsos, thyrsus)。它是一根用茴香(fennel)做的長杖,上端挖空,經過儀式處理,插進常春藤而成。常春仗是神聖的,可以當武器使用(25、733、762-763、1099),也可以產生奇蹟。例如:「另一個(信徒)把她的常春杖插到地面,從那裡神為她送上一座酒泉。」(706-707)在下面,兩位老人尚未正式入教,但因為他們穿上了信徒的服飾,拿著常春杖,顯然取得了返老還童的力量。
對於已經入教的信徒,她們更是力量驚人,生氣蓬勃,行為奔放,有時甚至達到瘋癲的程度。酒神的「信徒」或「教友」的希臘字(maenads)含有瘋狂的意義。在一般的用法中,一個人如果精神異常興奮緊張,或是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他就可以被稱為maenad。在本劇中,酒神的信徒無論是追隨祂的亞洲婦女,或是底比斯後的當地婦女,都是名符其實的maedaes。她們瘋狂時的行為,劇中由信使們做了生動的報告。第一次是亞格伊發現有人要逮捕她,於是號召她的隨從者反擊。戴歐尼色斯的教派似乎還相當原始粗糙。它一方面具備任何宗教必有的教條、奧祕,和儀式,另一方面它以強制的方式招收信徒,以殘忍的手段報復侵犯或壓制它的人眾。這正如前面引證過的酒神的自況:「祂最為恐怖,但是對人類也最為慈祥。」復仇對祂來說是正義之舉,是「神的憤怒」(Nemesis)。最後,酒神的信徒在死後似乎還可以獲得某種保障。歌隊在知道彭休斯已被他母親撕成碎片之後高聲歡。
從信史的大輪廓來看,《酒神的女信徒》的寫作時間,介於荷馬的兩部史詩與《新約》之間。前者約於公元前九世紀開始流傳,《新約》中的《使徒行傳》及《羅馬人書》大約寫於公元後第一世紀的五十年代,《馬太福音》等四福音則在它們之後約二十年才先後完成。荷馬史詩中以宙斯為首的天神很少公正的照顧人的現世,更壓根忽視人的來生。史詩之一的《奧德賽》更描寫,人死後到了陰曹都變成孤魂餓鬼,因此這些神祇固然為官方尊崇,但難以饜足人心,尤其是在公元前五世紀中葉以後,希臘戰亂瘟疫不斷,人民生活困苦,生命沒有保障,於是紛紛尋求心靈的慰藉。許多的新教、密宗於是趁虛而入,酒神的崇拜也是其中之一。到了公元後一世紀中葉,基督教的保羅到希臘傳教,批評當地原有的多神教與偶像崇拜,廢除了摩西以割禮為入教先決條件的律法,首度以耶穌基督的名,大量的為非猶太人施洗。《新約》的教義,我們多少都知道,包括它強調靈魂的不朽、耶穌的愛,得救與進入天堂的許諾等等。這些教義,正是亂世人心所想往的,也是酒神教所沒有的。從這個歷程看,《酒神的女信徒》所反映的,正是人類追尋更高宗教的一個歷程。
三、近三個世紀對本劇的代表性解讀
公元前四世紀,希臘的哲學家L. Euhemerus認為,一切神話中的神祇都是人想像創造出來的;祂們的神奇力量,都是人把英雄事蹟誇大渲染的結果。後人用他的名字標誌這種神學理論,稱為euhemerism「英雄神話說」。他的這種看法,沒有引起立即的影響:羅馬征服了希臘,但在文化與宗教上大量汲取了它的傳統。到了中世紀以後,基督教盛行,任何涉及到異教神祇的問題,基本上是壓制、挪用或迴避,所以對酒神、對本劇都無特別的研究。
啟蒙運動以後,對古典文學的研究活潑起來。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盛行的是「反悔派理論」(the palinode theory)。這派人士以為,尤瑞皮底斯一向用理性看待傳統宗教,對它質疑、諷刺不遺餘力,以致受到同時代的作家及哲學家的不滿。於是他在死前的最後一個作品裡,做了臨終前的悔改。依據這個前提,這派的詮釋認為:彭休斯反對宗教,以致受到了應得的嚴懲;他的慘死因此是一種警告:世人要敬畏神明,不可傲慢褻瀆。(Dodds, xl-xli; Hu, 1-7)
首先反對此派的學者們屬於「理性主義者」(the rationalists)。他們分散在英、法、德各國,但一致認為尤瑞皮底斯一貫用藝術反對宗教,無所謂臨終悔改。在本劇中他讓信徒與反對者都受到痛苦,藉以凸顯酒神的無理與危險,但是他受到傳統的制約,不得不採取迂迴的批評方式,因此,這派的大師Verrall寫到:「雙重詮釋是必要的」(18)。例如,彭休斯的死是傳統的一部分,劇作家不便更改,但透過雙重詮釋,他的死亡並不表示劇作家認為他罪有應得;相反的,彭休斯獨抗狂瀾,雖死猶榮,值得欽佩。
理性主義者的最大貢獻在指出:本劇中的酒神教與希臘原有的宗教不同,因而能引起當時人們參加;這點,本文前面已經說到。但是本派進一步指出,就個人言,酒神教訴求於感情的神秘感,讓信徒能打破外在的束縛,追尋自由與快樂。基於同理,它對社會則是弊多於利。當底比斯的信徒們瘋狂到殺死自己的孩子時,這種弊害到達極端。這派於是歸結到:尤瑞皮底斯在劇中展現出雙重人格。作為詩人,他熱情謳歌酒神的宗教;但是作為哲學家,他私淑於彭休斯的理性的觀點。(Decharme, 64)
理性主義者的詮釋也有盲點,那就是彭休斯並非理性之人,酒神也有其殘酷的一面,這些下面還會提到。接著這派之後的一派可以稱為「象徵主義派」(the symbolists),他們的共同點是:視酒神為心理力量的象徵。首倡此論的英國學者Dodds即認為,尤瑞皮底斯不可能相信真有一個客觀的酒神存在,他在劇中呈現的神固然以人的形貌出現,但那只象徵一個宇宙間或人心內的力量,就像人的慾望、或海上的風暴一樣,它們既無理性,更缺道德。在劇中第四場,彭休斯突然改變,不僅穿的服飾和女性信徒一樣,連言談舉止也像女人。這種突變,依Dodds解釋,來自他的心理隄防的完全崩潰:他一向被壓抑的慾望於是奔流而出,終至不可收拾。
(Dodds, xvi)在劇尾,彭休斯的母親和外祖父都受到酒神嚴懲,「反悔派」可以視為罪有應得,理性主義者可以視為酒神殘忍的證據,但象徵主義者則認為,當暴風破船時,所有乘客都葬身海底,無分男女老幼,賢與不肖。(Dodds, 1973, 89; Hu, 19-20)
酒神所象徵的究竟是什麼,說法因人而異。Grube認為它象徵人的熱情。順應這個力量,人就會得到快樂;忽視它、壓抑它,就可能釀成災難。在劇中,彭休斯最後身體被撕成碎片,正是熱情爆破的後果。從這個結論再反觀他在劇中的所作所為,Grube認為「他是個好色的清教徒,極度恐懼放鬆感情的力量。」(Grube, 40-53; Hu, 21-2)。Diller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只承認:戴歐尼色斯象徵一種可怕的非理性的力量,「它驅使一個人拋棄自己的身分,並且極端暴虐的強迫那些頑強企圖保持自我的人。」(366)。
晚近一個世紀以來,歐美學術界還流傳著一種「戴歐尼色斯聖體主義論」(the theory of Dionysiac sacra-mentalism)(Obbink, 66)。在二十世紀初年,劍橋大學人類學者J. G. Frazer 研究非洲土著生活後,在《金樹枝》中宣稱,野蠻人相信將野獸連血帶血生吃,就可以取得所吃野獸的力量,他稱之為「鮮肉餐食的同種療法效果」(the homoeopathetic effect of a flesh diet, v, ii, chapter 12)。劍橋學派的Jane Harrison把這種理論直接應用到酒神,認為祂的信徒相信,他們在祭禮中所吃的牛或羊就是酒神自己,透過聖餐就分享祂的生命(Obbink, 66)。她的理論引起很多的支持與附和,影響到對本劇的詮釋,但劇中並沒有提到「鮮肉餐食」的現象,更沒有那樣的行為。
除了以上略可歸類的意見之外,其它的個人意見還不勝枚舉,其中最為人知的當為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這位一度宣稱上帝已經死亡的德國的哲學家認為,生命的現實令人恐懼、嘔吐,只有藝術連同想像,使人得到慰藉,繼續生存。呼應著L. Euhemerus人創造了神的說法,尼采認為人在夢中創造了兩個神,他無以名之,於是假借希臘神話,一個命名為戴歐尼色斯,一個命名為阿波羅。前者代表音樂等非視覺藝術,後者代表具象藝術(plastic)或造型藝術,兩者結合而成悲劇。尼采認為,生命的外象變化萬端,深邃的希臘人,對最深最微的痛苦,感受都獨一無二。但尼采同時認為,生命的底層是歡樂洋洋,生氣勃勃,且代代相傳,不可能摧毀。希臘悲劇中由撒特(satyr)組成的歌隊,表達出來的正是這種生命。它們在歌聲舞影中,結合超自然的力量,陶然忘我,也使它們的觀眾從中得到慰藉與拯救。
四、本劇的時代意義
以上大體綜述了有關本劇的主要解讀,以下的討論則基於一個出發點:假如有一個人自稱是神,或一個神以人的形貌出現,聲稱要建立一個新教;又假如有一群人成為他(祂)的信徒,在行為上破壞了原有的規範,那時,政府應當怎樣處理,一般人應當持什麼態度?換句話說,把重點放在人類社會。類似的宗教問題不僅歷史上層出不窮,今天也仍存在,而且在很多地方非常嚴重,我們的這個角度,也許能讓本劇更有時代的意義。
本劇基本上可以視為政治與宗教的衝突:前一半國王彭休斯企圖依仗權勢,鎮壓一個外來的正在萌芽的新教;後一半戴歐尼色斯運用祂的神力,毀滅了國王和他的家族。在這樣的過程中,雙方立場對立,觀念相左,互相衝突激盪,形成一種辯證關係,其複雜性可視為人類政教歷史發展的縮影,其前瞻性則至今仍可成為處理類似衝突的指南針。這個衝突可以分為四個角度或層次:從宗教的角度看,彭休斯是罪有應得。從政治的角度看,國王所作所為,縱使獨斷專橫,仍然情有可原。從被壓迫的信徒角度看,彭休斯的言行缺乏理智,過於極端,他可說死有餘辜。從受酒神懲罰者的角度看,祂的懲罰過於嚴厲,因而失去人心。本劇像是廬山面目,橫看成嶺側成峰,它是一個疊景,深邃難測。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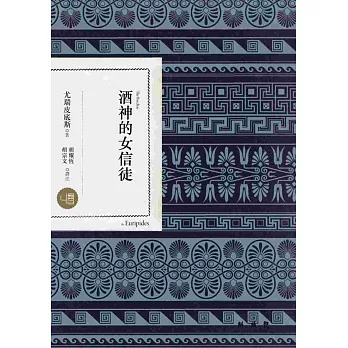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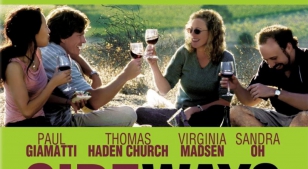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