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十年前我寫了一本書《戀戀風塵──一部電影的開始到完成》,現在,謝海盟寫了另一本書,《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
一個三十年,很長的,也很短的。
很長。「她常常認真的練習飛行技術:吃力的爬上寬寬的窗檯,然後凌空跳到彈簧牀上,儘可能利用在空中的那一剎那,快速的揮動翅膀,認為早晚有一天,終將因著她的技術猛進,可以飛上天空……」是的,長到足夠讓學飛的盟盟長大到,終於,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書。
「終於」,那是因為在這之前,她寫過又毀過的幾部奇幻故事,動輒十萬字起跳,最多寫有七十萬字的那部真令我嫉羨交加,每要勒她脖子求索分個零頭給我的蝸速長篇吧。
但她寫了一冊又一冊A4大小的筆記本,斷然不讓任何人看。從小學(大部分是連環圖漫畫)寫到國中,寫到高中,寫到大學,有電腦以後仍是手寫,圖個不擇時地(機場候機時)皆可寫的便利。自幼以來,若有那不明狀況的熱心人士建議海盟拿出來發表或貼上網,她便靦腆搖頭而笑:「自娛的。」僅僅一位讀者,她特許給表妹,這位表妹喊她「老哥」,掛在嘴上總說「我老哥」,我老哥如何如何,甚中彼意,亦獲其心。
即便她大學畢業了加入電影編劇工作之餘,仍在寫,有時我倆從捷運站走回家,等紅灯換成小綠人時我問她,多少字啦?最後我獲知的字數是四十二萬字。這部她寫穿越,穿越唐。我問她為什麼是唐,而不是其它?她說看《隋唐演義》,覺得寫得不好,打算自己寫一本。我轉頭望她一眼,心想嚇,好個亞斯伯格人。
這樣,令我想起那位苦等奧德賽返鄉遂以織製丈夫壽衣為名擋住追求者們的佩妮羅佩,而白天織,夜裡拆,壽衣永無織成之日。又像奧瑞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宋碧雲譯版《百年孤寂》)打了三十年仗之後回家,重操舊業做小金魚卻不賣,每天做兩條,做完二十五條便融掉重做。這樣不為發表,不為什麼的老在那兒寫,那兒讀,唯一一點好處,如果文字是表意的工具,海盟倒把這工具練得輪轉無礙,辭、達意矣,不像新手。
初始我找海盟來做編劇助理,是把她當一台文書處理機,幫我劇本打字、列印、修改、傳發劇組。然而加入我與侯導的劇本討論不久,她變成了我們的記憶卡,隨身碟。看來我是在壓榨她掃描式的記憶力,但凡材料到手,我愛請她先過目一遍輸入腦中,以備隨時查詢。她的這項利器,在往後從頭到尾沒有缺過一場戲(歸究於海盟那種頑執不醒才可能耐得住的拍攝現場之漫長之無賴)的跟拍側記,她錄影機般,詳實記下了全部過程,《行雲紀》,這本我稱之為「留下活口」的證詞之書。
證詞?是為誰做證詞?
為一部我們曾經觸手可及的想像過、卻始終未被執行出來的懾人電影做證詞。這部在劇本定案時言之鑿鑿被相信一定好看易懂的電影,情感華麗,著色酣暢,充滿了速度的能量。
因為如今大家看到的電影簡約之極,除了能量,其餘皆非。況且能量,不但不從速度來,反從緩慢和靜謐之中來。可以說截然不同的兩部電影,不同到在我看了初剪時轉臉對海盟發恨聲:「你寫的側記比電影好看一百倍。」自稱菜鳥編劇的她,已頭抱鋼盔奔逃至百尺外絕不捲入我的編導大戰,唯我想起來又恨聲:「還好有你的書留下紀錄,不然我們簡直像一群傻瓜。」
究竟,從劇本到銀幕上的電影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西方龍有翅膀,東方龍靠交通工具行雲駕霧。而神龍見首不見尾,卻碰巧叫海盟憨膽見著了,近身觀察沒給電灼雷劈陣亡,倒留下了這本活口之書。
剪接時,海盟本想跟剪學習,但她自去寫了小說《刺客聶隱娘》,得七萬字,看看只有第一章〈最初〉拿得出手,便易名〈隱娘的前身〉列入本書。侯孝賢一向不分鏡,亦不按劇本剪,他是拍到什麼剪什麼,這部分我將另外為文來說。
此書也收錄了三篇文章,可供觀看劇本的演變。唐傳奇〈聶隱娘〉寥寥千字。故事大綱採用二○一一年四月版,當時還未將殺手精精兒與周韵飾演的田元氏合為一人。再是二○一二年十月的第三十八版劇本,舒淇說拿到的劇本薄如iPhone,都是文言文。
在那神農架山間兩千公尺的大九湖溼地拍攝安史亂後的中唐,劇組置景問到海盟這裡來:「到底蘿蔔或玉米可不可以?」海盟說玉米原產於美洲,要傳入好歹也待至大航海時代,那是明代之事了。置景人員遂努力藏妥每一根玉米那是小鎮上最大宗的農作物,莽莽湖岸,四處聽人吆呼著:「玉米不行,蘿蔔可以。」是啊三十年,真短。
朱天文
二○一五年六月八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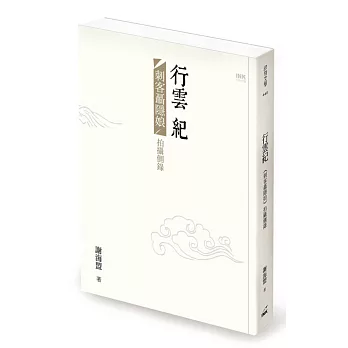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