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對於大部分我在這本書裡面寫到的人來說,憤怒是一種奢扯,他們精疲力竭、苦苦掙扎,薪資無法讓他們遠離貧窮,改善生活,而生活也反過來困住了他們,常用來描述他們的詞彙「窮忙」,根本是個矛盾的修辭,在美國,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應該是貧窮的。
一九九七年,這個國家的繁榮扶搖直上,我開始著手找出那些被拋在後面的勞動人口,我在華盛頓特區的黑人社區裡面找到他們,在新罕布夏州的白人城鎮裡、在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的工廠跟就業培訓中心裡、在阿克倫和洛杉磯的住宅計畫裡、在波士頓和巴爾的摩的營養不良門診裡、在加州的血汗工廠裡、在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地裡。
我的目的是要在他們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地徹底檢視他們的生活,解開導致他們個別困境的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有些人我只見過一、兩次,有些到目前為止則追蹤了五、六年,我反覆地聯絡他們,隨著經濟繁榮的崩潰與衰退的來臨,他們經歷了升遷與破產、結婚又離婚,家裡多了新生兒,也有人去世。
國家經濟的起起落落,對這些人沒有多大的影響,不管景氣是好壞,他們都過得很辛苦,有些人身陷令人麻痺的抑鬱中,逆來順受、無助失意,用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話來說,他們「疲於希望,空於夢想」,不過其他人則自豪地受到夢想與決心的驅使,相信工作的力量。他們很少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憤怒,當怒氣浮現時,往往不當發洩在自己的配偶、小孩或是同事身上,他們通常不會怪老闆、政府、國家,或是富裕階層,儘管他們大可合情合理地這麼做,但他們通常會責怪自己,有時候,這麼做確實也沒錯。
我花費幾年的光陰訪談十二次、十五次、二十次甚至是更多,因此我得喜歡這些人才行,所以我支持他們,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我得試著用清楚的眼光去看待他們,並且不帶意識形態。事實上,堅定的保守派與激切的自由派都會為書中種種貧窮有所觸動,至少我希望能夠如此,因為我所發現的事實,並不符合任何人提出的政治議題,我想要挑戰並且瓦解經年累月在光譜兩端的假設。
這個主題非常牽動情緒,直抵美國人對自己信仰的核心,因此我懇請你們,假如碰上了艱難的事實也請繼續讀下去,吸收這些生命中所有的矛盾,化為更廣的見解。如果想在這些問題上有所進展的話,我們就必須要超越黨派政治。
其實,透過探討那些勉強活在聯邦政府官方貧窮線的人來檢視貧窮,似乎有點奇怪,因此這些家庭大部分都是如此,他們棲身於更廣的地帶,以現有的定義難以界定;但正因為這樣,他們很顯眼,因為企圖逃離困境時,我們能夠清楚看到他們必須跨越的障礙,從貧窮的邊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見貧窮的最深處。
「貧窮」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詞彙,因為貧窮不只是一個類別,不能光用政府的年收入限額來描述。在現實生活中,那是一個沒有標記的區域,沿著逐漸寬闊地區,這片艱困區比社會上的一般認知更為廣大。事實上,有更多比官方認定為「窮人」的人因貧窮相關的煩惱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因此,我使用「窮人」這個詞並不像統計學家那樣,我盡可能以應有的、不精確的方式來使用這個詞,指的是最底層的經濟能力,加上隨之而來的所有問題。
要充分討論勞動的窮人,就一定得談到他們的雇主,所以企業家和經營者也會出現在書裡,他們從廉價的勞動力中獲利,或是奮力經營著自己的生意;除此之外,這趟旅程中也遇見了教師、醫生等專業人士,大家都試著想要有所改變。
雖然我沒有想過要在人口統計上有代表性,但書中大部分的窮忙族都是女性,就像全國大部分的勞動人口一樣,未婚單親,她們通常背負著低收入和扶養青少年的高需求,我描寫的大部分人都是美國公民,但是也有一些移民,有合法也有非法的,他們的勞動力對於國家成長與安適至關重要。
這裡有黑人、白人、亞洲裔、西語裔。貧窮在美國不分民族,沒有種族的界線,大多數非裔美國人就讀的是次級公立學校,在那裡他們更容易碰上障礙,許多人都居住在破敗的社區,他們仍舊得忍受刻板印象和種族歧視,尤其是在他們試圖脫離體力勞動工作,爭取管理職位時。殘餘的奴隸制度尚未消散,美國長久以來的種族偏見,仍使得黑人占低收入戶中較高的比率。然而貧窮也包括了許多共同的困境,折磨著所有種族的人,勞動世界底層的白人,儘管不必經歷全部黑人所承受的困難,卻也遭受不少阻礙,我的上一本書《陌生人的國度》(A Country of Strangers)裡寫過了黑白種族的分歧,現在我要將角度轉移到貧窮是如何作用的,橫跨種族界線,廣為存在。
本書中沒有合成的人物,我完全拒絕這種做法,每個人物都是真實的,如果有人要求不透露全名,我就不指名道姓,在第一次提到的時候用引號加註化名,或是用隨機挑選的姓氏第一個字母代替。
至於那些願意透露真名的人,我要感謝他們,我太太黛比,利用她身為教師與社工的能力,為我開拓眼界,釐清複雜的教養問題,她在我的手稿上增修,豐富了我的報導,在我採訪回來以後,幫助我了解這些故事,敦促我反覆思考所見所聞;我的兩個孩子蘿拉與麥可,都是文采優美的作家,也是敏銳的觀察者,他們的建議大大提升了這份稿子的水準,因為有他們,這本書變得更好;我的大兒子強納森讀了潤飾過的版本,提出許多有幫助的看法。
很多人花時間幫我,書中沒提到或是沒能充分致謝的人包括了:大衛.埃里森,他既是我的朋友,也是前新罕布夏州的議員,為我介紹了該州的反貧窮工作者,也對手稿提出了建議;蘿貝卡.根特斯、司徒南西、鮑伯.奧爾科特,他們向新英格蘭的窮人伸出援手;洪羅伊與維多.納羅帶領著他們有效率的組織,幫助在洛杉磯的韓裔及拉美裔工人;我的表姐瑪麗亞.沃契柯夫斯基是服裝設計師兼製造商,為我敞開大門,帶我了解這個行業的經濟情況;洛杉磯就業服務中心的莫霓卡.戴維斯(、羅笛斯.卡斯楚和理查.凱因斯;華盛頓首岩浸信教堂的牧師李察.柯賓;「人人有飯吃」(SOME Center for Employment Training,SOME)就業培訓中心的主任詹姆士.貝奎斯;還聰敏敬業的年輕小兒科醫生約書亞.沙弗斯,對本書手稿提供了意見,也讓我有管道能採訪波士頓醫療中心的臨床及研究人員;波士頓醫療中心的黛博拉.法蘭克醫生以及巴瑞.祖克曼醫生;巴爾的摩成長與營養診療中心的主任莫林.布萊克;德拉瓦大學的關.布朗;阿克倫基督教女青年會日間照顧中心的主任南希.賴斯;克利夫蘭就業培訓中心的主管瑪莉.拉波特;堪薩斯市地方投資委員會的布蘭特.宣德梅;阿克倫的校長安東尼.馬拉諾與華盛頓特區的校長西奧多.辛頓,這兩位都有很敏銳的洞察力;還有我在洛杉磯訪問韓國移民時,擔任口譯的朱麗雅.宋。
我的經紀人艾斯特.紐伯格從計畫一開始就熱切地鼓勵我,我的編輯喬納森.西格熱情地接受了我的成果,並且給予最有益的建議,他們是我最感謝的兩個人。
如果說這是一本短篇故事集,那麼裡面有角色、有情節,甚至還有些家庭悲劇與孤寂的英雄主義,但是這裡沒有高潮,故事也沒有結局,生活就這麼繼續下去、無解。
大衛.謝普勒
前言 在貧窮邊緣
疲於希望,空於夢想──卡爾.桑德堡(Carl Sandburg)
洗車工沒有自己的車子,負責整理已兌現支票的銀行職員,戶頭裡只有不到三美元,編輯醫學教科書的女員工,已經十年沒有看過牙醫了。
這是被遺忘的美國,在勞動世界的底層,數以百萬計的人活在繁榮的陰影之中。在貧窮與安樂的暮光裡,無論你是富是貧,還是中產階級,每天都會遇到他們:他們為你送上大麥克漢堡,在沃爾瑪超市(Wal──Mart)幫你找到商品,為你收成食糧,替你打掃辦公室,幫你縫製衣服,在加州的工廠裡,他們包裝燈泡,之後會裝在你小孩的腳踏車上,在新罕布夏州的工廠裡,他們組裝壁紙的樣本,讓你在裝潢時可以參考。
他們各自面臨的困境形塑了他們的樣子,有些人正要擺脫福利救助、吸毒成癮、無家可歸,有些人則一輩子都陷於低薪工作中,有些人的孩子營養不良,有些遭到性侵,有些人住在搖搖欲墜的房子裡,造成孩子罹患氣喘,並因此缺課,有些青少年甚至沒有所需的眼鏡,連黑板都看不清楚。
這本書就是關於他們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夢想、他們個人的失敗,還有比他們更失敗的國家。儘管美國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富裕,低收入的事實卻考驗著美國式的、宣稱勤奮工作就可解決貧困的信仰。有些人覺得工作行得通,有些人卻發現這行不通,在高要求、低薪水的工作之間來來去去,許多人只能勉強搆到官方貧窮線以上,岌岌可危的瀕臨於貧窮邊緣。那些對於富裕家庭來說可能只是有點不方便的問題──車子出了點小問題、身體微恙、孩子沒人照顧──對窮人來說卻是危機,因為這有可能讓他們的飯碗不保。他們耗盡一切,毫無存款,總是積欠帳單,銀行戶頭裡少得可憐,或是根本一無所有;因此比起那些生活更為安穩的美國人,他們得要付出更多的費用和更高的利息。就算經濟穩健,許多人還是在邊緣掙扎,永遠脫離不了現況;而經濟衰退的時候,他們向後倒滑,往絕境而去。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因為聯邦福利改革提出的時間限制和工作要求,因而被推入困境。改革實行於一九九六年經濟蓬勃發展之際,許多接受社會福利的人都很讚賞,認為此舉可以幫助他們擺脫仰賴他人的沉悶世界,踏入活躍的職場文化,充滿挑戰與希望。有些人說他們有了自信,得到孩子的敬重,那些夠幸運或是有天賦的人,踏上職業之梯,職位越來越高,收入越來越好;但是有更多的人,收入仍舊微薄,生活水準依然沒有改善,他們還是存不了錢,沒有像樣的醫療保險,不能搬去好一點的社區,也不能把孩子送去承諾前途看好的學校就讀。這些人是被遺忘的美國人,只有從社福名單上被除名的時候,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的存在,苦苦在工作中掙扎的時候,他們就從國家的雷達上消失了。
擺脫貧窮、遠離貧窮似乎需要完美的陣容以及天時地利的條件,先決條件包括了全副的技術、好的起薪、有升遷機會的工作,但還需要目標明確、勇敢與自尊、沒有欠下大筆債務、沒生病也沒毒癮、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誠實正直,還有私人或政府機構必要的協助。這一系列條件要是出現任何缺口,麻煩就會接踵而來,因為你窮,就表示你沒辦法保護自己。不如這樣比喻,假如你打四分衛,但是不要帶頭盔、不要墊肩、沒訓練沒經驗,前方是一排體重只有四十五公斤左右的隊友,弱不禁風,沒有金錢幫襯,沒受過更廣泛的世界的訓練,對於腐敗社會的威脅誘惑毫無防備,貧窮的男男女女就這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解雇──挨了揍,鼻青臉腫,連連慘敗。要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失敗中出現了某次例外,那就會被稱做是美國夢的實現。
在文化上,美國不太確定貧窮的成因,因此也不知道該如何解決,美國神話仍然認定即使出身貧寒,人人都有機會獲得幸福。我們希望那是真的,無論真假,也很欣慰看到那些美夢成真的例子。十九世紀作家霍雷蕭.阿爾傑(Horatio Alger)的作品我們已經不再讀了,不過他的名字卻成了白手起家的同義詞,他筆下的角色都能透過勤懇工作致富,經典的移民故事依然能夠觸動美國人的心,儘管這個國家長久以來一直嫌惡著那些來到「金色大門」之外的「不幸渣滓」,就像自由女神像下方所銘刻的文字所述。即使厭惡大量湧入的移民,我們仍舊陶醉在這樣崇高的說法中,只要努力不懈地工作、謹慎節儉,就能從一個貧困的難民脫胎換骨,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小布希總統親口說出了這個神話,他在即將上任的政府首次高層任命中,安排了兩名黑人、一名西語裔跟兩名女性,被問到這樣安排是否想表達某些訊息,「當然,」這位總統當選人回答道:「在美國,只要努力工作,在人生中做出正確的決定,任何人都可以實現目標。」
這種神話有其價值,替這個國家跟每位居民都設定了嚴苛的標準,國家必須努力,成為傳說中的機運之地,居民必須奮鬥,好好利用這些機會,這樣的理想激發了民權運動、向貧窮宣戰,還有持續不斷的追尋,想找到方法緩解富裕中依然存在的窘迫。但是美國神話也提供了怪罪的藉口,在清教徒的傳統中,努力工作不只是實際需要,也是道德要求,不努力就是道德敗壞,嚴苛的邏輯決定了冷酷的判斷:如果一個人的勤奮工作能夠帶來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種美德、如果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工作得到成功,那麼失敗的人,就是不夠努力。市場是公平的最終裁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低薪是工人的錯,因為那只不過是反映出他的勞動價值低。在美國的氛圍之下,貧窮總是帶有一股原罪的氣息,二○○三年三月,CNN主播茱蒂.伍德拉夫(Judy Woodruff)在主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時,問艾倫.凱斯(Alan Keyes)為何認為道德每況愈下,明明某些道德指標都進步了,她指出:犯罪率下降、未婚生子減少、靠社會福利的人數也變少了。顯然社會褔利是道德敗壞程度的指標。
還有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美國反神話,認為社會必須要為個人的貧窮負起大部分的責任,種族歧視和經濟富裕的階級,造成貧困社區的種種症狀,學校不好、選擇有限,貧窮的孩子被迫犯罪、吸毒,只能從事收入微薄、沒什麼未來可言的工作,個人淪為龐大力量的受害者,自己無法掌控,包括了貪婪追求利潤的企業,只會剝削勞動力。
一九六二年,麥可.哈寧頓(Michael Harrington)在他的《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書中,生動地描述了這種美國反神話,喚醒了當時被富裕蒙蔽雙眼的國家,廣闊的「隱形之地」上的窮人眾生相,一揭露就令人感到震驚不已。這本書催生了詹森(Lyndon B. Johnson)的向貧窮宣戰,不過詹森的宣戰從來沒能夠真正讓這個國家動起來,也算不上什麼勝利。
五十年後,我們在經濟上有了成就,但是貧富之間的差距卻拉大了,收入最高的百分之十的人,資產淨值平均為一百五十八萬九千美元,而收入最低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則是負四千九百美元,也就是說,他們的負債還比收入多。比起日本、香港、以色列、加拿大,以及所有西歐的主要國家來說,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比較低,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然而把這一切付諸文字加以討論,卻沒有解決,大家就更不容易感到驚訝,再也不憤怒了,無動於衷,因此更難有所行動。
事實上,人並沒有辦法輕易用美國神話或是反神話來歸納,這本書裡的每一個人,既非無助也非萬能,而是介於個人與社會責任兩極之間,落在光譜上的各種不同位置。每個人的生活都是混合而成的產物,決定錯誤、運氣不佳、無法選擇的前途,或者因為出身和境遇等意外斷絕道路。很難說人的貧困跟他們的不智之舉沒有絲毫關聯──輟學、未婚生子、嗑藥、工作總是遲到,也很難說人的行為跟他們與生俱來的條件沒有絲毫關聯,父母教養不當、教育程度不佳、居住環境糟糕,觸目所及看不見任何未來的可能性。
該如何定義個人在自身貧困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社會褔利及其他社會政策中的爭論,但很少有人能夠肯定地回答,即使在具體的個案中也一樣。比起富人,窮人比較無法掌握私人的決定,更難自外於冷酷的政府機器,在這個科技與競爭的瘋狂世界裡,窮人更沒有辦法敏捷地避開重重危機,他們的個人錯誤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個人成就得卻只會得到更少的回報。個人與公眾之間的互動如此錯綜複雜,諸如就業培訓這類協助要想奏效,就必須針對個人需求量身打造才行,內容不只要包括使用電腦與操作車床這類「硬技能」,還得包括與同儕互動、樂意服從命令等「軟技能」,要能夠處理多年逆境所累積的怒氣。就業培訓人員發現,屢經失敗的人──在學校裡、戀情中、工作上──要等到明白自己有能力追求成功,才有辦法成功。要擺脫貧困,他們必須學會純熟地控制自己的情緒與雙手。
離開貧窮不是拿出護照,跨越邊境這麼簡單的事情,赤貧與安適之間有一道寬廣的爭議領土,這條通道的距離,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安穩的生活就是可以用一份薪水付清房租──不用存兩個星期的錢才付得起一個月的房租」,泰隆.皮克斯利說道。他是個年約五十歲的削瘦男人,住在華盛頓特區,來自困苦的生活,白天打零工,還吸食海洛英。他的要求特別低,「我不想靠打零工籌錢,」他直截了當地說道,「我想住得舒服點,就算只是一間十英呎平方大小的房間也好,在一個月內,我可以用薪水付清所有的帳單,我不必存什麼錢,對我來說,過得舒服不必非得要有儲蓄帳戶才行。」
在這樣富裕的國家裡,大部分人的胃口都比泰隆.皮克斯利來得大,廣告無所不在,電視幾乎永遠開著,許多美國人學會了把想要變成需要,「當你住在社會住宅裡,你媽媽領著社會救助金,如果有五、六個或者七、八個小孩一起長大,你這輩子想要的東西就數不清了;但是你卻什麼都沒有。」法蘭克.狄可森解釋著,他是一名工友,靠販毒在華盛頓獲得他過去沒能得到的東西,「你有小孩,他們想要漂亮的球鞋跟外套,帶著六、七個孩子,靠社會救助金的媽媽可沒辦法供得起,他們要怎麼樣才能得到這些東西呢?也許年紀越來越大,他們越想要得到好東西,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上毒品。沒錯,你只要出門、交易,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東西,車子、公寓、衣服。」法蘭克.狄可森在監獄裡待了三年,不過他跟妻子也在馬里蘭郊區買了一棟房子,用的是他販毒賺來的錢。
因此貧窮並沒有一種適用的簡單定義,可以是絕對的貧窮──買不起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是相對的貧窮──負擔不起普及的生活方式。能夠以通用的標準來衡量,也可以用不同的指標來看待,就連字典也沒有共識,「缺少或匱乏維持生計的方法,」其中一本字典如此斷然定義,「缺少物質需求或安穩生活的方法,」另一本字典說道,「一個人缺少普遍或社會可接受的金錢數量或財產,」第三本字點如是說(粗體為作者所加)。
以全球或歷史的標準來看,許多美國人認定的貧窮都是奢侈的,住在鄉村的俄國人就算買不起車子,家裡沒有中央空調,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住在鄉村的美國人會如此認為;越南的農夫就算只用水牛犁田、徒手灌溉,住在茅草屋裡,也不會被認為很窮,但是北卡羅萊納州的農夫會,因為他得用手採收黃瓜,一箱才賺一美元,只能住在破爛的拖車裡。這世界上大部分的窮人,都會被環繞在美國窮人周圍的公寓、電話、電視機、自來水、衣服,還有其他種種便利設施給弄得眼花撩亂,但是這並不代表窮人不窮,也不代表處於貧困邊緣的人,並不是真的站在懸崖邊上。
「美國的窮人在香港或是十六世紀也許不算窮,但在此時此地的美國,他們是窮人,」麥可.哈寧頓(Michael Harrington)在香港經濟攀升之前寫道,「他們得不到這個國家之中其他人享有的一切,然而社會只要有決心,是可以供給的。他們活在邊緣,像個圈外人。他們看著富裕美國的電影,讀著富裕美國的雜誌,這些全都告訴他們,他們是自己國家裡的放逐者……當你有一碗飯可吃,而社會上其他人只能吃到半碗,這可能是代表你的成就與才智,也能夠激勵人採取行動,實現自我潛能;但社會上其他人有著精緻均衡的飲食,而你只有五碗飯可吃,這就是悲劇了。」
的確,在富有的國家裡當一名窮人,要比在貧窮的國家裡當一名窮人難受多了,因為在貧窮中求生的技能,在美國幾乎已經消失了。去河內的貧民窟看看,你會發現孩子用瓶棍和生鏽的腳踏車內圈發明了很多遊戲;然而去洛杉磯的貧民窟看看,你會發現孩子都很依賴塑膠玩具跟電子遊樂器。住在柬埔寨的時候,我兒子邁可對於家裡原本要扔掉的東西修一修就好了,這樣的獨具匠心驚嘆不已,那是我們在金邊的時候,他的電視遙控器壞了,只花了一美金就在街角找人修好了。
在美國,聯邦政府對貧窮的定義很簡單:二○一一年,有一名成人與三名孩子的家庭,年收入若是低於兩萬兩千一百一十三美元,就算貧窮。這個數字相當於一個人每年工作滿五十二周,每周四十個小時,時薪十美元又六十三分,或是比聯邦政府的最低工資多三美元又三十八分。一九九○年代之際,經濟擴展、收入提高,官方貧窮率降低,十年之內,從一九九三年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點一,降低到百分之十一點三,接著在後續的經濟衰退中微幅上升,二○○三年達到百分之十二點五,二○○六年百分之十二點三,二○一一年百分之十五點二。
不過這些數字會產生誤導,聯邦政府所界定的貧窮線,遠遠低於像樣的生活所需,因為人口統計局採用的仍然是一九六四年時,由社會安全局所設計的基本公式,之後的幾年間只經過四次略微修改。貧窮線所設定的貧窮,大約是「基本溫飽」(thrifty food basket)所需的三倍,這樣的計算得自於一九五五年的消費模式,當時一般家庭約有三分之一的收入用在食物上,時至今日,情況早已不同,一般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預算大約只有十分之一,但政府還是繼續把「基本溫飽」所需乘以三,只根據通貨膨脹調整,無視於將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生活型態急劇變化。
這樣的結果粉飾了現實,低估了那些照理該被歸類為貧窮的人口數量。人口統計局和國家科學院正在測試更精準的公式,會考慮到食、衣、住以及水電費等等的實際成本,按照這樣的計算方法,收入會包括現行沒有計算在內的福利,像是糧票、住宅補貼、燃料補助、學校營養午餐,生活成本則包括了現在忽略掉的費用,例如照顧孩童、醫療支出、健保費、社會安全薪資稅。這些五花八門的公式在一九九八年開始實施,貧窮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三,官方數據從三千四百五十萬人增加到四千兩百四十萬人。依據二○一一年公布的《補充貧窮衡量標準》(The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貧窮率從百分之十五點二上升至百分之十六,這樣的改變據推測能讓更多家庭有資格申請與他們貧窮程度相關的福利,其中某些項目,包括兒童健康保險在內,已經涵蓋了貧窮線百分之一百五十或百分之兩百的家庭。
就算採用了這些修正過的方法來計算貧窮,還是只能反映出一個家庭短時間內狀況的剪影,在這幀快照裡,動態的起伏不見了,只衡量本年度的收支,不考慮資產與負債。這些公式忽略了過去,而過去往往是現在的沉重負擔,很多人換了工作衝出貧窮線,卻發現學貸、車貸,還有以前信用卡的驚人高利息,把他們的錢全都吃掉了,他們並沒有過得比從前好。
窮人或近乎貧窮的人被問到貧窮的定義時,他們講的不只是皮夾裡有多少錢,而是腦子裡或心裡想些什麼,「絕望,」新罕布夏州一名十五歲的女孩說。
「不是絕望,而是無助」,洛杉磯的一個男人說道,「我幹嘛要起床呢?永遠沒人會雇用我,因為看看我穿的是什麼。事實上,我高中都沒唸完,我是黑人、棕人還是黃種人,我在拖車裡長大的。」
「那是一種心境,」華盛頓特區的一個男人說,「我相信精神狀態比物質重要很多。」
「我很富有,」一個女人說,她剛找到一份操作影印機的工作,讓她擺脫了貧窮,「不只是物質上的東西,這是因為我知道我是誰,現在要往哪裡去。」
另一名女人原本在中產階級家庭中長大,之後落入貧窮,她慶幸自己擁有「文化資本」,指的是她對書本、音樂、理念的愛好,還有她與孩子之間的親密關係,「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一點也不窮,我們擁有許多財富,」她說道,「我們不覺得自己窮,只有在沒錢看醫生或修車的時候才會覺得窮。」
對每個家庭來說,貧窮的組成都是部分經濟因素、部分心理因素、部分個人因素、部分社會因素,部分過去影響、部分現在狀況,每個問題都會擴大其他的影響,全部緊緊相連。一個逆轉就會造成連鎖反應,導致結果與初衷大相逕庭。破舊的公寓可能會加重孩子的氣喘,導致需要叫救護車,造成一張付不起的醫療帳單,於是毀了信用紀錄,讓汽車貸款利率飆升,逼得他們只好買一台不可靠的二手車。做母親的因此無法準時上工,升遷與賺錢的能力受限,她只好繼續窩在破爛的房子裡。在第一章你就會看到這樣一名女性,如果把她跟其他貧窮的勞工父母個別的問題加在一起,這些問題所構成整體,會比部分問題的總和還要來更嚴重。
因此,多數窮忙者所面臨的問題都交織在本書的大部分章節中,每一章則會分別著重在貧窮的某一方面。在關於工作的那一章裡面,你會看到為人父母的故事,在討論到健康議題的時候,你會看到住宅的問題,如果把個別問題獨立出來,像在實驗室裡抽取毒素那樣,既不真實也沒有意義,這些問題大多相倚相存,彼此之間的化學反應讓整體效果更為惡化。
如果問題環環相扣,那麼解決方法一定也是如此,只有工作是不夠的,只有醫療保險是不夠的,只有良好的住宅是不夠的,可靠的交通運輸、謹慎的家庭收支預算、有效的養育方法、有效的學校教育,單獨達成任何一項都是不夠的,沒有哪項改變能夠獨自幫助勞工脫離貧窮邊緣,只有全面兼顧,國家才能履行其承諾。
第一步是要看見問題,而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我們對這些人視若無睹,那些有工作卻仍然過著貧窮日子的人,融入在我們熟悉的景色當中,因而受到忽視。他們構成了隱形而沉默的美國,分析師一個不留意就忽略掉了,「我們現在都住在郊區,不住市中心了,」科羅拉多大學的教授麥可.高登斯坦(Michael Goldstein)宣稱,他在美國公共電視台上解釋,為何沃爾沃斯超市(Woolworth’s)在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取代了沃爾瑪超市。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的提姆.布魯克(Tim Brookes),曾經針對電影院裡定價過高的爆米花,發表過一篇措辭詼諧的言論,他氣不過一小袋爆米花竟然要價五美元,於是調查了實際的成本。據他計算,他拿到那袋五又四分之一盎司的爆米花,在超市裡賣二十三點七一八五美分,不過戲院經理買一整袋五十磅重只要十六點五美分,他慷慨地把爆米花的電費算五美分、紙袋一美分,總成本等於二十二點五美分,扣掉營業稅,利潤是四點零七五美元,或者是百分之一千八百一十一。
顯然這家戲院很有概念,他們不請任何員工,因為布魯克完全沒有提到櫃檯後面有人,他們微不足道的薪水不會影響暴利,因此也不在他的計算範圍之內。那些製作爆米花的人、那些把爆米花裝袋再遞給他然後收錢的人,一定是穿了隱形斗篷,就連公共廣播電台的編輯,似乎也沒有注意到他們。
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他們被看見。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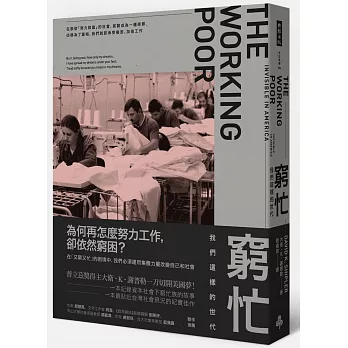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