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每個地球人不可不讀的書
吳惠林(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當代人幾乎都能琅琅上口,其原始出處雖有爭議,但它之所以能膾炙人口,無疑歸功於米爾頓‧傅利曼(1912.7.31~2006.11.16)這位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譽的經濟學大師。由於傅利曼在給大眾的通俗文章中引用,這句話才風靡全球,這同時也突顯出傅利曼在公眾中享有極高的聲譽。
傅利曼獲頒諾貝爾獎,足證其學術成就之高,但他之所以享譽全球、對人類有極大的貢獻,卻是在公共政策領域上對「自由經濟理念」的大力傳布、推廣之故。他在這方面不但著作等身,而且風塵僕僕到各國對國家領導人和普羅大眾耳提面命。為了發揮更大影響力,傅利曼在1968年11月與海勒(W. Heller)舉行公開大辯論,也有一段時間在《新聞週刊》(Newsweek)與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凱因斯學派最主要大將,1970年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紙上論戰,被薩繆爾遜稱為「經濟學界的鰻魚」。
經濟學界鰻魚的情操
這個比喻鮮活地點出了傅利曼的自由經濟觀點在當時屬於少數,但卻頗富攻擊力,有如遠洋漁業捕魚者,為了維持所捕獲魚群的新鮮,必須放入幾條鰻魚與魚群相鬥。這也顯示出傅利曼處境的艱難,但他為真理「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隻身力戰群雄。
除了以文章、演講、辯論宣揚自由經濟理念外,傅利曼更深入政治、專制獨裁國度與領導人對談,或充當經濟顧問,將經濟自由灌輸在政策決策者腦中,最有名的當推他在1970年代充當智利軍政府獨裁者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1915-2006)的顧問,促使智利致力於推動市場自由化策略。但也因為如此,傅利曼在1976年被宣布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引發史無前例的抗議風波。
舉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系和瑞典商業學院的教師及研究員的抗議信為例,內容是:「儘管傅利曼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有一些成就,但他完全不理會他所推薦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他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做了巴西和阿根廷的軍事獨裁者之顧問,也替智利軍人政權擬出一條經濟政治路線。……這一切不但指出了皇家科學院的政治幼稚病,也完全抹煞了傅利曼的得獎資格。……」
除了有這種書信抗議外,頒獎那天,場內有一人示威,場外更有四千人示威,創下截至該年為止,共75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受到破壞的先例,且因為示威者擋道,典禮後的國王傳統晚宴也首度延遲開席。雖然受到如此激烈抗議,傅利曼仍堅持其藉機轉變獨裁者理念的做法,繼續擔任各國政要的諮詢顧問,最著名的就是與中共經改初期的關鍵人物趙紫陽之交往。
為何傅利曼敢於干犯眾怒,冒著「為虎作倀」的罪名持續幫軍事獨裁者擬定經改政策?在傅利曼夫婦1998年出版的對話式自傳《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的第24和26兩章,對該事件的始末,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和辯解。我的理解是,傅利曼相信「經濟自由的結果將促成政治自由」,在智利,皮諾契特將軍接受人民的裁決(公民投票),安排於1989年12月進行總統選舉,軍事執政團把政權交給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恢復了真正的政治自由,而新民主政府繼續執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也終究實現了「自由市場經濟在自由社會中健全運作」的終極目標。
堅信自由經濟最能造福人群
傅利曼之所以有如此的勇氣,乃在其對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堅信,堅信這種制度對人類的福祉最有助益。為了促進人類福祉,他不辭辛勞地從事自由經濟的佈道工作,並將他的完整理念在1962年作了統整,以《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這本書呈現,那是一本以一般讀者為目標的書。
由於當時那些深恐政府的規模擴大,以及深恐福利國家和凱因斯思想的得勢會危及自由和繁榮者,是被居於相當多數的同輩知識分子視為怪異分子的少數團體,因而該書受到漠視,沒有任何一份全國性的主要刊物對之評論,出版18年也才賣出40幾萬本。但到1980年,當這一本《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出版時,情況卻大為改觀。這由傅利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的〈1982年版序言〉中可清楚得知。
傅利曼這樣寫著:「過去25年來學術氣候轉變之大,可由我的妻子和我合著的《選擇的自由》一書所受到非常不同的待遇得到證明。《選擇的自由》一書刊行於1980年,在思想上直接承襲《資本主義與自由》。《選擇的自由》得到所有主要刊物的評論,而且通常是具有特色的長篇評論。《書摘》不僅摘述該書,而且以它為封面作號召。《選擇的自由》出版後的第一年就在美國賣出40萬冊精裝本,1981年初並印行普及版,而且已被譯成12種外國文字。
我們認為這兩本書被接受程度的不同,不在於品質的差別。事實上,較早的那本較著重哲學思想,也較抽象,因此是較為基本的。而《選擇的自由》,如同我們在該書的序言所說的,『較多精微實例,較少理論架構』,《選擇的自由》補足了,而非取代了《資本主義與自由》。從表面上看,讀者對這兩本書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可以歸功於電視的力量。《選擇的自由》是根據我們在公共電視台同名的節目而設計的,原本也是要伴隨該節目的推出來銷售。毫無疑問,電視影集的成功,突顯了該書的卓越。
這種解釋相當膚淺,因為電視節目本身的存在和成功,正可證明學術氣候的改變。在1960年代,從未有人來找我們製作像《選擇的自由》這樣的電視節目;這樣的節目即使有贊助者的話,也必定很少。如果真的製作出這樣的節目來,觀眾也一定少得可憐。因此,《選擇的自由》所得到的不同待遇,以及電視影集的成功,正是輿論氣候改變的當然結果。雖然我們這兩本書的論調依然稱不上知識的主流,但至少現在已得到知識分子的尊重,而在廣大的讀者群中幾乎要被視為傳統的作品了。」
輿論氣候的大轉變
傅利曼又說:「輿論氣候的改變,來自經驗,而非理論或哲學。蘇聯和中國曾經是知識階級的大希望之所寄,如今很明顯地已經被唾棄了。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曾經對美國的知識分子產生極大的影響,也早已身陷困境。回頭看看美國,一向熱衷於大政府的知識分子,其中大部分又為民主黨的支持者,在經過了越戰,特別是甘迺迪和詹森兩位總統所扮演的角色後,已感到大失所望。許多偉大的改革計畫,諸如國民住宅、支援工會、學校的種族融合、合併學區、聯邦對教育的補助、反歧視運動,這些過去代表福利的旗幟,如今已多化為灰燼。和其他人一樣,鼓吹改革計畫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袖珍本著作也受到通貨膨脹和高稅率的衝擊。是以上這些現象,而不是理論書籍洋洋灑灑陳述出來的理念,解釋了1964年高華德(Barry Goldwater)的大敗,到1980年雷根(Ronald Reagan)的大勝之間的轉變。高華德和雷根提出了相同的計畫,也傳達了相同的訊息,卻遭到截然不同的命運。
那麼,像本書一樣的同類書籍,它們所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就我看,有兩層意義。首先,是提供了自由討論的題目。如同我們在《選擇的自由》一書的序言中寫到:『唯一能真正說服你的人是你自己。你必須讓這些議題自在地在心中翻動,咀嚼這許許多多的論點,讓這些論點去喧騰鼓動,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把你的偏好轉化為堅定的信仰。』
其次,也是較為基本的是,在環境必須做轉變之前,保有開放的選擇空間。在私人行事中,尤其是在政府的體制中,都存在著一種巨大的慣性,這種慣性可以說是維持現狀的殘暴。只有在面臨危機時──不管是實際發生的還是預期到的危機──才能產生真正的改變。一旦危機發生,應付危機所採取的行動,是依當時社會廣為流傳的理念而定。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功能;亦即,對應於現存的政策,發展出不同的方案,使這些方案持續存活且具可行性,直到它們從政治上的不可能採行,變為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選擇的自由》補足《資本主義與自由》
經由傅利曼的自述,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與自由》與《選擇的自由》兩本書是互補而非替代性的,而《資本主義與自由》雖也討論了12項社會重大議題,但因較偏向哲理、抽象、具原創性和嚴謹,較難被普羅大眾接受,因而沒達成傅利曼「以一般讀者為目標」的理想。而這本《選擇的自由》因脫胎於電視節目腳本,藉由日常生活中諸多實例以平易近人的文字撰寫,結結實實打動了凡夫俗子的心坎。
這本《選擇的自由》共分十章,由「市場力量」開始,再談「管制」的專橫,接著剖析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真相,第4章以「從搖籃到墳墓」為題解剖「社會福利」的迷思,第5章探討「公平、正義」這個弔詭課題,第6~8章分別對「學校教育」、「消費者」,以及「勞工」的福祉是否應由政府負責作翻案式解剖,第9章針對「通貨膨脹」這隻怪獸的出現及消除作探索,最後一章總結時代潮流向「人的自由和經濟自由」兩個觀念攜手並進,並在美國產生了十分豐碩的成果。
傅利曼在1980年時認為,美國人正在覺醒,也再度認清「受到過度管理的社會很危險」,也了解「好目標會被壞手段搞砸」,而「依賴人的自由,根據他們本身的價值去控制自己的生活,是充分實現偉大社會的完整潛力,最牢靠的做法」。所以,傅利曼以「也幸好,身而為人,我們仍然能夠自由選擇應該走哪條路──是否繼續走政府愈來愈大的路,還是喊停和改變方向」,作為全書結語。
不過,傅利曼雖慶幸美國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力,但他在1993年2月於《資本主義與自由》1982年版的〈中文版作者序〉中,卻提出了震撼人心的警語。
經濟自由倒退
傅利曼寫道:「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書中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著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地,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1960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最重大的行為變革發生在原本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包括蘇聯和其衛星國,以及中共。那些國家試圖以自由市場取代中央集權控制,來獲取最大可能的利益,位處於西半球的我們對這些發展深感得意。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形態,而共產主義國家正在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形態。
我對台灣的了解不深,因此我不敢說台灣的情形是否亦如上述的西方國家之態勢。然而,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做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在台灣發行《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像是運送煤炭到電氣化的城市,因為台灣過去四十年來遵循本書所闡釋的理念,已經變成二十世紀的經濟奇蹟之一,一如香港、新加坡、二次大戰後二三十年的西德,以及過去二十年來的智利。不過,這樣的成果並不是說本書的理念就不相干了。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形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我非常希望本書的發行能夠幫助台灣保有、且擴大其人民的自由和經濟的自由。」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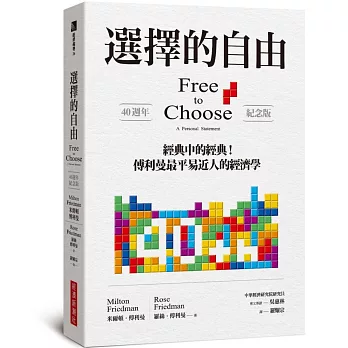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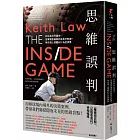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