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撥去濃霧的勇敢之書
郝譽翔
已經很久沒有讀到如此撞擊入心的散文了,黑色的文字線條,彷彿是一筆一畫沉沉地切割入白色的紙面,也直切進人的心坎底,那般的大汗淋漓,痛,以及暢快。
書名取為「濃霧特報」,讓人誤以為內容會是和自然生態,或是地球暖化氣象之類的有關,但根本不是,每一篇其實都環繞著最親近的人與事,例如家人,或是男友,乃至於日常生活飲食,或是職場工作。然而這一切始終籠罩在陰霾之下,濃霧不散,若是借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那便是:「時而清醒,時而恍惚,吃東西宛如一場豪賭,不知下一秒會帶來怎樣的人生,極少有天堂,大部分是地獄。」
換言之,閱讀《濃霧特報》,就彷彿是在穿越一場濃霧瀰漫的生之地獄,令人啞口無言的震撼之旅。雖是如此,作者的直言坦率,卻又讓人不禁打從心底湧起了一股釋懷,那便是終於有人敢大膽地說出真相了:這人生,果然是極少有天堂,而大部分是地獄,
如此一來,佛家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並不是在哀悼人生短暫,聚散無常,以及美的轉眼即逝,反倒是在驚駭人生之惡,而當惡到不可思議的極致之時,反倒轉成了一齣令人不知該哭還是該笑,如夢似幻又光怪陸離的,荒謬劇。
我喜歡〈大滅絕〉中的楊氏家族書寫,一直上溯到平埔族母系社會,而那一座充滿喜悅、好生、樂天與和平的烏托邦天堂,如今早已隨著平埔族的消失而無影無蹤,家族的成員更瓦解崩落,淪為一座座沉默的孤島,彼此互不往來,生機滅絕。這儼然是一則台灣島嶼上的百年孤寂寓言,由羊癲瘋患者、豢養暴躁猴子或滿牆昆蟲標本的詭異人家,以及在路上遊蕩的瘋女,和喝酒成癮的浪蕩子所組成,瘋狂的基因依然在家族的血脈之中繁衍,增生,而人們從小就殘殺成癮,只因這已演化成為一種根深柢固的本能,只管盡情奪取這世上一切所能奪取的東西。
我也喜歡〈惡意〉寫婦人抓住青蛙後腿,興奮的咯咯直笑,對他人之痛苦,乃至自己的暴力與殘忍毫無知覺,而這樣毫不掩飾而赤裸裸的惡意,幾乎遍布了我們所生存的空間,讓人已經失去了憤怒的力量,只剩下一股冰涼的寒意,冷到骨髓裡。於是《濃霧特報》就這樣打造出一個「潮濕陰暗,幾近崩塌的世界」,真實到令人怵目驚心,而當人與人之間的日常對話都無以為繼時,語言究竟還有什麼效力?而文學呢?不更是一座以話語所編織而成的迷宮,甚至一場華麗又徒勞的紙上展演,而如此精神的自欺與自慰,又果真能夠救贖一顆已然麻木的冬之心靈?還是只能換取來沉沉的疲憊?
對於文學,我向來就不樂觀,更不天真,因為文字的意義只向自己展現,無須去說服別人,那全是白費氣力。《濃霧特報》亦然,楊莉敏誠實到叫人心驚,她像是一個大喊國王根本沒有穿新衣的孩子,總是斬釘截鐵而無須迂迴。她寫自己在夢中對父親大喊:「你為什麼還不去死?」而這句話不也彷彿是一道回音,狠狠地朝向自己反擊?但死又如何呢,死已經不是答案了,因為生命已成封閉的迴圈,連死都失去了召喚的魔力,只能以一個「乖孩子」的靜默姿態,日復一日,平和安順的過下去而已。而這不也正是我們多數人所切身感受到,陷入其中而默默承受著的,卻沒有勇氣說出口的人生真相嗎?
《濃霧特報》全書以父親起始,又以父親患癌症過世結尾,因此父親成了貫穿全書的核心主軸,也是成人惡之世界的隱喻,一切暴力和恐懼的最初起源。通過雄性的父親,一個孩子才開始「明白了恨」,並且「藉此抵抗父親未能符合該有樣貌的種種失落與失能」,進而學會了築成一種「侵略性的黑暗」,讓它強大到足以吞噬所有,才終究得以長大成人:成為一個「不會感到疼痛」更「不會害怕」的人。
我以為《濃霧特報》說出了成長的殘酷,而在這過程之中,一個孩子必然經歷了某種抵抗的過程,被剝奪,乃至戰鬥。就像楊莉敏獲得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的〈不散〉,也同樣是在勾勒一個瘋的瘋、死的死,鬼影幢幢的世界,也同樣被困在濃霧瀰漫的生之牢籠,而一個「不受寵愛」的「乖孩子」,「是不會平白無故就有糖可吃的,必須努力取得成績來討人歡心才行。但那麼世故,真令人厭煩。」這一段話簡直像是出於張愛玲之口,一襲華美的生命之袍,即使爬滿了噁心的蚤子,但仍承認生命是華美的,其情可憫,一如《濃霧特報》中的孩子,在世故的面具底下,躲藏的是一顆天真、易感又良善的童稚心靈,對周遭的人世,總抱持「如得其情,哀衿而勿喜」的悲憫。
也因此《濃霧特報》若非出之於一種毫不自欺、更不偽善的勇氣,又何以能夠以如此簡潔有力的文字,彷彿匕首一般,去逼視惡的存在?又如何能夠生出一股源自黑暗的力量,去抵抗撒旦所鋪天蓋地散播而下的詛咒?《濃霧特報》雖寫疏離,寫死亡,寫黑暗,寫惡,但其實卻是一本心痛之書,柔軟之書,溫暖之書,即使濃霧瀰漫,卻又曖曖內含光,而那才是文學真正打動人們心靈的所在。
霧濃重而成為霾
言叔夏
讀楊莉敏的《濃霧特報》,常讓我想起剛搬到這座中部城市的時光。那是在春冬之交,沿一條中港路離開城市,翻過坪頂山頭。擋風玻璃前開展的,是一條大路滑向海線的斜坡。龍井、大肚、沙鹿、清水……這些寡淡的地名蒙著一層灰,沿坡面散落排開,名字摸起來竟是有顆粒感的。一如眼前的地平線,分不清究竟是季節交替的濃霧,還是其實是PM2.5的煙霾,遮蔽了去路。在那些鄉界與鄉界的邊陲,兩旁的地景不知何時被悄悄置換成低矮的透天厝、檳榔攤、鄉間小吃部。天黑以後,偶爾會在一條寬如險峻河床的大路,砂石車與聯結車的短兵相接裡,驚險地遇見一台車廂過於光亮的BRT。偌大的兩節式車廂,空蕩而困惑地,疾馳向更深的夜裡。多年前剛到東海的一門課上,曾鼓勵學生多多利用此城公車十公里免費的優惠,畢竟創作課坐在教室裡是如此無聊;「不如你們翹課搭車去看海?」這話真是講得太過自信浪漫了。期末有人回報他果真翹課搭上那班駛往台中港的公車:「根本沒有海。到處都是砂石車,風還超大,我眼睛嘴巴都是沙子。」
那或許是《濃霧特報》裡的一則具象的隱喻。文學研究所畢業的青年返鄉工作,等在前頭的,不是被抒情濾鏡美化過的海,而是飛沙走石式的鄉間圖景。昔日學院裡奉之如神靈的文學,畢業以後回到老家,竟成為她日日辦公的一座文創園區。在那溢出了「台中」這個詞彙的遙遠的海線邊陲,荒地與大路彼此吞沒,顯得再無去路。書裡的場景遂化成一種超現實主義式的變形,而鄉土空間的畸零邊界,則顯得陰翳:死巷底塌了又修的土角牆。水泥凹陷破洞的廚房地板。代稱為「前頭」的神明廳……這樣一座修葺縫補的平房屋子充滿一種錯置與拼接,從而曝現了那些從「我」之處所輻射四散的感官網絡,其實早已堅硬地斷裂,裸露出裂縫的紋理。她寫幼時父親兩次棄狗,第一次丟棄不成,隔了一年,狗又回來;第二次丟棄,狗已經死了。「為了這個身體哭過的父親,選擇把牠裝在紙箱,載去那個曾經把牠丟掉的地方,偷偷找了塊空地,挖個洞,連同紙箱一起掩埋起來。」在同一個地點將同一個身體丟棄過兩次的父親,那哭泣,究竟意味著什麼呢?而這樣為那一個身體哭過的父親,死在布滿破洞的廚房地板時,「由於太胖了,沒人搬得動。」只能一直被放在那裡,和廚房裡的許多垃圾什物放置在一起;這是這本書裡難得霧散的晴朗場景之一。作者說:「天氣這麼好,父親卻死了。」四周的景物輪廓遂清晰起來。旁觀的作者在死亡事件的外圍逡巡,掉落出來;「我只是想活著,而且不必活得太辛苦。」
這些像是壞掉娃娃搬演的家庭劇場,不知為什麼,對我來說竟充滿強烈的既視感。那或許是同樣來自中南部一邊陲偏鄉的背景,深諳從那些鄉間的畸零破洞出發,如果想要獲得幸福,這條「幸福路上」所需具備的技能,往往不是增加什麼,而是拋擲。丟掉床板、家屋、相簿;丟掉名字、父母;丟掉字,這些情感的負累與記憶,一不小心就會在光天化日下站立起來變成異物。世界是野獸的。如同進食與吞噬是一體兩面的,她的胃病與厭食,是被噬者從吃與被吃的循環迴路裡脫落出來的,一種安靜的承受與抵抗。
如此影像式的,不同於散文寫作的主流慣性,個人的獨白常開出一片意義的流域,有始有終;《濃霧特報》更像是一捲畫片,嚴厲而尖銳地割礪出風景與故事的線條。讀者若想從這部錄記著生活的重複、家族的破敗,以及一代文藝青年無出路感的文集中找到慰藉,恐不容易。但或許正是這種殘忍而決絕的手勢,我們得以在作者招來的一片大霧之中,辨認出事物邊界的輪廓,與前進的道路指引。獨屬於她的「看太陽的方式」。
據說分辨霧與霾的方法之一,關鍵正是「太陽」。真正的霧會在日出之前就隨陽光散去。反之如果太陽出來後,整個白日仍一徑地霧濛地白,那就是霾。霾是那髒汙殘酷的現實介入抒情迷霧後的一種超現實變體。這使得這本書在書寫的光譜上,是如此地接近卡夫卡或布魯曼.舒茲(在台灣,那或許是同樣來自西部海線鄉間的七等生──)。尤其是後者。它常使我想起那間沙漏底下被扭曲變形的鄉間療養院,住著父親死後不停播放佛音的母親,把昆蟲釘在地板不斷肢解的哥哥,還有「我」;「我」在白日的官僚體系裡,猶如迷宮中的彈珠不斷迴繞,找不到迷宮的出口與盡頭。而「父親」呢?「父親」的身體一直放在廚房,隨著平房老屋底下不斷流失的沙,一年比一年下陷,終於被地板吞噬進裂縫。
大地有縫,填補以安插在其上的房舍與木麻黃林,掩飾著縫存在的現實。生活是補釘的野獸。但《濃霧特報》使我們看到,那些匍匐凹折的變形姿勢,其實是一種生存的掙扎,一種想活下去的渴望,因此,也就有了一種前進的可能。祝福莉敏與她的寫作。有朝一日,那些寫在沙上的字,也能反過來將霾豢養成一種動物,而且是可愛動物。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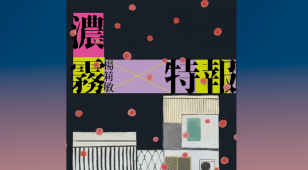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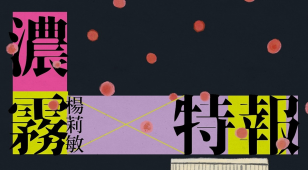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