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英文平裝版序
時光飛逝,我在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ma)普吉特海灣大學的演講已是20年前的事。演講之際正值美國建國200週年,這亦早成過去。日本在1995年迎接迥然不同的週年紀念。首先,紀念日本帝國首次參與現代戰爭,並戰勝大清帝國。1895年的《馬關條約》成為日本致力躋身西方列強的第一步。對日本人而言,意義更重大的紀念是1945年的敗戰。經歷半世紀的軍國主義、戰爭及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後,戰後日本在強調主權在民,天皇是國家“象徵”的新憲法下獲得長治久安。昭和日皇裕仁在位62年後於1989年駕崩,日本人一邊回首往事,一邊邁步向前。
適逢時代交錯,戰後日本人身處的世界亦正迅速轉變。蘇聯的突然解體令1945年以來的國際二元權力架構隨之結束。美國對日政策亦出現變化,從昔日地域安全主導變成經濟主導。日本的經濟增長不再是亞洲的個別“神話”。身處亞洲周邊沿海的韓國、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的經濟均呈現高增長,而且開始影響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亞洲的經濟增長在本世紀末冠絕全球。中國大陸雖然在政治上抗拒自由化,卻放寬經濟控制以吸收外國資金,估計它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在中國沿岸省份的貿易和工業發展一日千里,但工廠煙囪排放的廢氣卻將酸雨帶到日本的森林。
美國亦不再一樣了。它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其國際影響力在戰後數十年間不斷下降。到了1980年代,美國驚人的赤字預算令它成為世上最大的負債國,而日本則躍升最大的債權國。日圓對美元持續升值,令日本在海外的投資火熱,在亞洲尤其活躍,連美國亦有其投資。日本國內工資成本上漲,各大企業不得不在海外尋找廉價勞工及市場保障,而日本企業亦成為這些市場不可或缺的部分。不過,日本資金在美國房地產市場購入最上等的貨色卻招來美國人反感,不少日本人對此感到驚訝。
1991年,波斯灣戰爭顯示邪惡獨裁者無法繼續在與強國對立中獲利。美國先進的軍事科技在這場戰爭大派用場,備受美國傳媒的追捧。日本投入僅次於沙特阿拉伯的130億美元資助卻被冷待。東京政府在處理捐獻上手法笨拙,被新聞界批評為“支票簿外交”。
冷戰結束對日本國內政治有同等份量的衝擊。自1956年成立後開始執政的自民黨受到連串醜聞打擊,威脅到它的認受性,求變之聲隨之四起。離黨的成員紛紛成立小政黨,與反對派日本社會黨結盟,組成好幾個短命而不穩定的聯合政府。首個聯合內閣由一位廣受歡迎的前熊本縣知事領導。他成功改革選舉制度,務求把政府和人民拉近。雖然沒有人能夠對這些變革的成果抱有信心,但是停滯不前的政治秩序終於有改變跡象。意識形態隨政治環境及世界事務而變遷。日本的社會黨派人士在1994年摒棄大部分已堅持數十年的立場,與昔日對手自民黨聯合執政。各派政治人物皆希望政府能夠回應訴求,但是政治不穩反而讓官僚制度獲得強化。官僚最喜歡諸多管制,無意下放權力。雖然有人認為日本已達轉捩點,然而日本並不會迅速轉變。因為商界、官僚及政府根深柢固的利益糾葛與態度,改變肯定只能按部就班及採取漸進式。
日本在國際事務的態度亦是如此。日本憑藉經濟力量在所有國際組織扮演主要角色,但是這些組織並未對此作結構改革。聯合國在化解柬埔寨政治困局及處理非洲和東南亞前所未有的難民潮問題上,皆受組織裏日本官員的指揮。面對一片要求日本廣泛參與國際事務的呼聲,日本國會小心翼翼並不情願地派遣了一支小規模的維持和平部隊,這是日本戰後首次派員參與海外事務。經過國會激烈辯論後,日本決定派遣非武裝部隊,以避免參與武裝衝突。觀察家終於明白大部分日本人對恢復日本作為“大國”感到厭惡。不過,少數政治領袖卻認為日本恢復“正常國家”的時機已經來臨。他們倡議更改憲法對軍事的禁制,以迎合二十一世紀的現實。半世紀被壓制的禁忌議題再次成為可能之事。
在新的形勢下,日本人開始顯示全新而更強的亞洲意識,甚至有些人對此稱作日本的“亞洲化”。這個說法很難被取代。1985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額比對亞洲的高出三分之一,到了1993年情況卻剛好相反,對亞洲的貿易額比對美國的多三分之一。日本在亞洲的投資如雨後春筍,跟東盟(ASEAN)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合作亦對亞洲融合有所貢獻。日本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是日本的第二大夥伴。在1981年到1991年之間,全球貿易的實質增長率為48%,但是日本以至整個東亞地區的增長卻翻了一倍。在日本的院校,來自亞洲的留學生數目亦遠遠超越西方學生。
簡言之,自我作這些演講以來,日本人的世界觀已徹底改變。我在1975年的演說中曾對300萬日本人的海外經驗表示驚訝,然而在1994年此數字已經上升至1,350萬,當中的五分之四是遊客。20年前我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卒於1989年)為例子,現在要為這三人選擇繼承者言之尚早,但肯定他們將會比前人更具備世界公民的特質。
最初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副社長暨編輯米R.里亞姆‧布羅考女士(R. Miriam Brokaw)催促我把這些講稿交予出版,我在此衷心感激她及其接任人把它們再度出版。
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
1995年於普林斯頓
英文版初版序
值此美國慶祝立國200週年之際,我們正好乘此良機回顧日本200年來的變遷。200年前,日本是一個不發達的、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小國。100年後,它決定根據西方模式改革制度,乃派遺居於領導層的大批精英分子廣遊西方,考察使列國富強的各種因素。為了表示近代化和國際化的意向,日本參加了1876年費城世紀博覽會(The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當中陳列的展品給人深刻的印象,而且展覽的規模和令人感興趣的程度,幾乎沒有哪個參加國可以相比。那樣優越的展覽品,使一位作家承認:“我們慣於認為日本是沒有文明的國家,或充其量只是半文明的國家。但我們卻在這裏發現充分的證據,證明日本閃耀的藝術光輝使歐洲最開化的國家也黯然失色。而歐洲國家是以藝術為驕傲和光榮的。認為藝術是自己高度文明的一個最值得驕傲的象徵。”現在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後30年,而日本又成為世界上的大國之一,也是少數工業化的民主國家之一。
在這200年間,日本的世界觀(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急劇轉變,是不足為奇的,問題將在本書中集中討論。日本從孤立中崛起,成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這對世界歷史、尤其是美國歷史,影響至大。在二十世紀,這一轉變因日美雙方的誤解和各自的錯誤而被玷污,也被暴力戰爭打斷了。美國也跟日本一樣,在這同一時期成為了世界上的重要國家,美國對國際社會的看法,轉變之巨,不亞於日本。
美國對日本的看法尤其反覆轉變得厲害。在我國圖書館的書架上,敍述日本友好迷人而且富有異國風情的圖書,和那些要提醒讀者日本是侵略成性、粗暴易怒和不可信任的敵人的圖書並排擺在一塊。大戰以後,日本實施軍事攻擊的危險性已經被淡忘了,不時一再出現的警告都不過說日本是個勤奮、沒有幽默感和技藝驚人的經濟對手。預言家也逐漸改變腔調,從強調日本喪失了對大陸和殖民地的控制則註定窮困,到強調日本靠勤儉也能生存;之後,再強調日本靠其經濟不斷繁榮興旺,總有一天能雄霸天下。戰後對這個新超級大國的種種稱呼,混雜着樂觀和沮喪情緒,見諸隱喻影射,就有例如以花朵盛開來暗示其脆弱性的,所以對於日本人自己從心情愉快一變而為意志消沉,也不必大驚小怪。
不過,日本人的世界觀在思想和心理兩方面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這是新聞記者和空談家所始料不及的;這些歷史上的思想和心理因素多年來成為我的研究核心。我以為這些因素對了解近代日本和近代東亞是愈來愈重要的。直到近代,在日本人眼中,世界是分成等級的,他們傾向於把世界各國按其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來排列,這無疑是源於他們本身的社會結構和經驗。我在以下幾個演講中利用一些特別令人感興趣的人物的事業和觀點,去探討這個等級排列的變遷。近年來,大量書刊和論著問世,使我尤其感到要採用這種研究方法來進行集中討論。不過,循着這樣的途徑對日本進行研究,尚屬初創階段,我希望我的論述能引起人們注意這種研究方法的價值及可行性。
本書是一部講稿,但增補了一些事實、統計數字和篇目,以適應新近的發展和出版要求。
馬厄利爾‧詹遜
1979年於普林斯頓
中文版初版序
本書的內容由三篇演講組成。這三篇演講是在十年前美國200週年國慶時發表的。那時我正想藉國慶慶典的良機回顧一下200年間事物變遷的情況,適值普吉特海灣大學的朋友要求我以日本作為“布朗與哈利講座”的講題,於是我就決定了以200週年國慶的精神來探討日本的世界觀在過去兩個世紀的變化。就我看來,日本在十八世紀從中國的巨大影響下脫穎而出,進入十九世紀,經過一連串全面改革,力求在國力和經濟上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到目前日本強大的經濟力量和生產率已取代了過去的政治和軍事勢力。
為突出重點,我盡所能在以下三個時期──1770年代、1870年代和現代──各選出一位中心人物,他們的功業和生涯足以作為他們各自時代意識的縮影。這幾位當選的人物當然不是“代表性的”,因為他們在當時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臨近的變革;然而,他們都察覺到自己所參與的變革,而且,他們也曾推動和加速這些變革;他們在年老的時候,可以檢討他們有生之年所目擊的變革。我選擇的17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學習西方醫學的先驅杉田玄白醫生,他在50年後撰寫的回憶錄,把他那個時代日本翻譯西方著作日益增長的傾向,和千多年前日本漢學勃興的情況作了比較。1870年代我選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國家的岩倉使團的書記官。該使團引人注目地長期遊歷西方,這是因為政府領導人想探求西方國家國力和組織上的秘密,為日本未來選擇合適的制度做準備。久米也很長壽,他在半世紀後口述撰寫回憶錄時,目睹了大英帝國的沒落。諷刺的是,他本人卻成為被日本社會視為正統的“新神道民族主義”猜忌下的犧牲者。替1970年代選擇象徵性的人物加倍困難,因為日本由軍國主義走向商業的和平主義的不規則進程尚在進行中。我所選擇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從事新聞工作、評論工作,及至成為國際機構的主持人。他的回憶錄《上海時代》和新近問世的《近衛時代》,詳細刊出了從未披露的史實。
在美國立國的200年間,世界各國都經歷了驚人的變化,日本當然並不是唯一曾面對經歷百年大變世界的國家。但我以為,這三個演講可以說明日本人不論是個人或集體,對這些重要的變化認識並作出反應的速度皆是非比尋常的,我之所以選擇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這點闡釋明白。我想,有一天對中國提出同樣的問題接着使用同樣的方法,才令人感興趣。例如可以把十八世紀時麥卡特尼勳爵(Lord Macartney)覲見乾隆皇帝、郭嵩燾出使西方或者王韜留學外國作為對照。乾隆給英國的著名答覆──中國並不需要任何英國產品和根本不用“奇巧之物”──當然是帶點誇張的官腔。不難想像,當德川將軍同樣遇上一個新來的外國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時,也會同樣輕易作出傲慢的答覆。但兩者之間重要的區別在於,清朝皇帝雖然未曾正式與西方“隔絕”,但無所作為,並不像日本人那樣利用長崎的荷蘭人駐地有系統地吸取西方知識,而且中國也沒有像日本個別知識分子那樣着迷於西方知識及其運用的人。在十九世紀當日本人到西方詳細考察時,中國人也來到西方。但可以想像,此中的巨大區別莫過於:明治時代的政府高層領導人幾乎半數曾親身周遊世界,使自己了解日本進行制度現代化時會遇到的各種大小問題,而相形之下,中國人離開國內的權位,則有招惹猜疑或不務正業之嫌的風險。直到二十世紀,區別仍然存在。日本在戰爭與戰敗的十多年間誠然與世界大勢脫節,但一旦遊歷和觀察的機會重現時,明治時代的範例也就再次出現,隨而大量引進知識與技術,使偏處一方的日本轉變為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大國。相反,中國卻退出國際市場,放棄西方技術,尋求自給自足與實行本土主義。當美國在1976年慶祝建國200週年時,中國這種可怕的行動已成強弩之末。在1980年代,這兩個重要的東亞國家首次在平等與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商談和貿易,一個真正放眼於國際的世界觀也許終會形成。
上述情況只不過預示將來可能有更全面的變化。如果這幾個講演能夠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事情和挑戰提供參考資料,我之所得將極其豐碩。我對柳立言君承擔本書的中文翻譯深表謝意。我從1950年代初開始研究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以來,中日關係一直是我的學術研究主題,我盼望看到中國讀者對這本小書的反應。
馬厄利爾‧詹遜
1986年5月於普林斯頓大學
中文版再版代序:從《日本的世界觀》看詹遜史學
《日本的世界觀》(Japan and Its World)是一本重要的小書。雖然其篇幅,不論英文版或中文版,只有薄薄的百多頁,但卻盡見馬厄利爾‧詹遜(Marius B. Jansen)作為一代日本史大師的丰采。
詹遜治日本史富有個人特色。第一,他對日本史有整體看法,將人物、事件及著作都能巧妙放在適當的位置。從樹木見樹林,決不流於瑣碎辯證或空談闊論。第二,他將日本史放在東亞史及世界史的脈絡加以梳理。對他而言,日本史不是孤獨的發展,而是不斷在與東亞及世界互動中形成。他對中日關係史尤為關注,亦是西方研究中日關係史的權威。第三,資料詳實。他非常重視原始史料,擅長透過原著及政府檔案作分析。他對西方及日本的學術著作瞭如指掌,包容各家之說如海納百川,引用資料得心應手。第四,文字精煉。大學主修英語的他行文用字十分老練,寥寥數筆已能表達豐富意思及其幽默感。其文章不但典雅、自然、流暢,而且思路清晰,層次分明,可讀性高。以上詹遜史學的主要特色在《日本的世界觀》中均可窺見。
《日本的世界觀》原本不是學術專書,而是一系列公開演講的講稿。因此它未有採用學術文章的格式,沒有註釋、艱深術語及冗長引文。這些演講的對象並非其日本史的學生,而是一般美國人,故其內容淺白易明,而且令美國聽眾覺得跟他們的歷史及所處的時代相關。
此書探討近200年日本人的世界觀所呈現的變化。詹遜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個歷史人物為主線,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戰後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及給自己定位。透過人物講故事,從而帶出歷史的重要性正是詹遜史學的常用手法,其孫中山及坂本龍馬的經典研究便是這方面的典範。
杉田玄白身處日本史上,日本人的世界觀出現轉移的關鍵時期。蘭學的普及令日本知識分子明白日本、中國及印度(傳統世界觀的“三國”論述)只是地球中一小部分,而且日本的傳統學問亦非金科玉律,在醫學及自然科學的知識上遠遠落後於西洋諸國。杉田親自目睹人體解剖後,發現中國醫學有關內臟的知識不及蘭醫可靠。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被質疑,日本人的世界視野從本土、亞洲擴展至全球,厭惡迂腐的舊思維,對新事物感到莫大興趣。
若德川中期的世界觀轉移主要只是出現在知識分子身上,到了幕末明治初則已發展成全國性的思想甦醒。中國不但不再是學習的對象,甚至淪為亞洲近代化的反面教材及他者。日本努力向國際接軌,一團又一團向西方學習的官方及地方使團令人想起昔日的遣唐使。久米邦武便是出使西方最長時間的岩倉使團書記官,他親自見證美歐的進步,並留下詳盡記錄,以供明治政府作改革參考。他將美國及歐洲列於國際秩序之首,亦是日本的模仿對象。他蔑視落後的中國,並恥與為伍。明治期全國上下一心求變,透過西式改革令日本搖身一變成為亞洲的新盟主及典範。
松本重治是昭和史的見證人及史家。戰後日本從頹垣敗瓦發展至經濟大國及亞洲成功模式之一,亞洲各國紛紛向日本取經,連西方對日本的成就都給予高度評價。日本人重拾自信及民族自尊,感到已實現日本多年在發的大國夢。日本在經貿、科技及商業管理方面已在全球先端之列,不再像昔日般以與先進國對齊為目標。日本的成就刺激新民族主義,強調日本人如何優秀及獨特的日本人論有很大市場。日本對美國及中國的關係變得複雜。對前者似近還遠,對後者似遠還近。在一片歡呼聲中同時又隱藏不少隱憂,日本為其經濟奇蹟付出了沉重社會成本。
《日本的世界觀》出版後日本及世界均經歷巨變。當今日本人的世界觀如何?誰可作當今日本的代言人?日本人是否愈來愈有國際視野?還是回歸民族主義?若詹遜仍在生,一定會親自為此中文版再版寫序,對上述問題給予精闢見解。現在只好由各讀者自行思考。香港商務印書館在2016年重印柳立言譯的《日本的世界觀》中文版,詹遜在彼方必然感到欣慰。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比較日本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初春驚蟄之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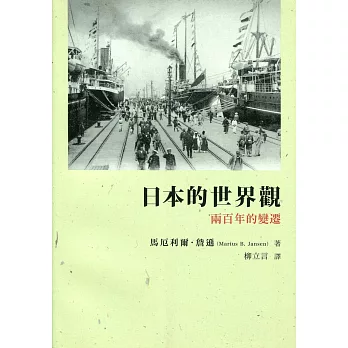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