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寫在前面
她已經非常虛弱了,
但她想要寫的,還有好多好多。
「書名就叫《有型的豬小姐》。」她翻找出手機螢幕上時髦的布偶角色Miss Piggy解釋這個書名,她說某天有一個很少來台北的藝術家朋友忽然北上,她以為他是為了一場拍賣展覽而來,朋友卻嘲笑她:「才不是,你看過豬自己上菜市場的嗎?」
豬不上市場,藝術家不進拍賣場,李維菁問自己:那麼作家究竟立足何處?
因為熱愛文學,在報業平台有很好發展的時刻,決然辭去工作,開始一篇一篇地寫。沒有冠冕堂皇的文壇背景,她寫自己相信的、創造屬於她這一代女性的文字,站出去就要有自己的樣子,她總是說:「要很有型,要有自己的風格」。
八年前,許涼涼駐進數萬顆讀者的心;兩年後,女孩們朗朗上口「帶我出門,用老派的方式約我」,她被陌生襲來的掌聲與眼淚打動,捨棄工作後,沒有穩定收入,多數時候就在自己的小空間與內在的創作欲搏鬥。二○一五年,推出長篇小說《生活是甜蜜》,透過徐錦文訴說她對藝術懷抱的憧憬:「藝術是人類試圖與上天溝通的嘗試,是曠野中、暗夜街道上,無處可去孤魂野鬼共同的歸依。是自由的國度,被溫柔海洋包覆的地球,裡頭住著平等的子民。」實然,並非如她所想,她心碎於那裡終究是富人與無賴的領地。「只有創造者有機會永垂不朽。」創造者不該對物質鞠躬哈腰,不該上市場,癡心創造的她,要把自己活成有型的豬小姐。
今年六月,知道時間可能不多,她為自己許下願望:要出一本文集。九月初,她在與病痛搏鬥的過程中交出一疊這些年通過自我省視,自認合格美麗的作品,一篇篇挑選改寫,每個字都得使出力氣,悄聲求著上天:讓我寫。她跟自己的時間拔河——今年一定要出版!
就在我們抓緊時間翻尋所有文章,一篇篇挑選一讀再讀,透過電郵簡訊讓她確認,「這篇要收」,「那篇我也喜歡」,從一開始的熱烈討論,到斷續簡短的回應,她的信息越來越短,對作品如何成形的意志卻越來越強。十一月初,與她相約確認要多寫篇序文。交稿那天,她答應我們「明天沒問題」,貼了一個可愛熊貓貼圖,但明天等來的是空白……十一月十三日凌晨,她未讀未回,從此告別。
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出版經驗,作者參與了內文編選、書名、書封至宣傳規劃,留下足夠的文字與談話,卻沒能等到這書印刷裝訂成冊的那一刻。作為她的編輯出版者,我們在哀傷之餘,只能堅持為她完成,讓她的讀者知道:直到最後她都是在創造的路途上。
感謝維菁女士的家人與好友們,最後這一段路,靠著他們的愛,我們一起完成這本書。「是中場感言,是創作宣言,也是愛的回顧。」維菁在書中寫下這段文字,她是個珍愛創造的人,在裡面,找到自己的天空。那裡的她不被世間的痛啃蝕,在那裡,她將迷人地淺笑,擺動著衣裙,拉著愛她的讀者們溫柔訴說,為什麼要做個「有型的豬小姐」。
新經典文化編輯部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序
記維菁
文◎鍾曉陽
初見面,是二○○八年十月我赴台為《停車暫借問》重出做宣傳,在一飯局上。在座有時報出版總經理莫昭平、楊澤、葉美瑤……此外有維菁。她跟我打斜對面坐,我暗驚這女孩真瘦,瘦得讓人擔心,坐在那裡細長一條,耀眼的粉紅連身裙,長頭髮兩邊各束起一撮,活潑俏皮像哪本漫畫走出來的少女,卻是文靜得有點閨閣,微微笑不怎麼說話,就是在那裡炫著人的眼。飯局畢大家站起散開,才看到她那裙子直落到腳踝,底下是高底的涼鞋,更顯得她柳條搖曳。在楊澤的邀請下又去了一家中國古典情調的喫茶店,維菁也來了,這回我們坐得近,幾乎膝頭碰膝頭,卻因為都說話聲音小,彼此要把頭湊前來聽,她說的話我記得其中一句是,一個人關在家裡亂寫是最開心的是不是?因此我知道她寫東西。她又從隨身的大包包裡取出她在看的書,把它豎在面前讓我看封面,我看到是艾莉絲‧孟若的短篇小說集中譯本,一雙聰明眼睛像是裝滿了話很想告訴我甚麼,從她那熱情的眼光我知道她愛這作家。一直我都有點模糊她當天是以甚麼身分在場的,也沒問,後來看到她寫關於我的報導才知她是時報文化版的記者。多年後讀孟若,總會想起維菁把書豎在我面前很認真地把她介紹給我的模樣。
二○一一年,一天收到一位台灣友人寄來的包裹,火紅的一本書跳出來。只看那裝幀跟書名,便覺著一股氣勢。《我是許涼涼》,多麼響亮的自我介紹。從小說概念,到文筆,到那對世道人心的洞見,我的一個感覺是「不凡」。是多麼罕有我們能看到一位作家帶來一個全然獨特的視角,是她多少年來的累積,經她不斷反芻內化理出來了一個用之格物的系統,從而給文學平添了新詞新意。從一開始維菁就那麼純然地是她自己,一個鮮明獨立的自我站在了讀者的面前。
二○一五年,在幾年前創辦了新經典文化的美瑤邀我為維菁的新作《生活是甜蜜》寫推薦語。我有點忐忑,還是應允了。讀畢全書後的震盪餘波多天不散,儘管美瑤說只寫幾句也可以,我寫了一段又一段。美瑤收到推薦語後,電郵傳來維菁的回應:「我出去哭一下。」
其後維菁寄來的贈書的題字稱我「曉陽姊姊」,翻開見到時不禁恍神,平常她想起我時心中是這樣呼喚我嗎?
二○一八年,我的《遺恨》由新經典文化在台灣出版,美瑤在建議行銷提案時一開始便提到維菁的名字,果然在後來收到的活動流程中看到維菁將在朗讀活動做我的同台講者。作為事前熱身我上網看了她的一些影片,包括二○一三年她出席香港書展講座的錄影。我發覺跟我記憶裡的她很不同了。不那麼瘦了,成熟了許多,完全是大人,有大人的自信和自若,但是嘴角翹翹笑起來時那少女的特質又自然流露。用她的少女學語言來說,世故與純真,似乎在她身上渾然融合了。有一點不變的是,任何時候她完全是真誠的自己。
青鳥書店朗讀活動的那晚,前往華山文創區的路上,美瑤告訴我維菁剛做完手術出院,沒說詳情,但我心情沉重起來。可後來在華燈初亮的暮色中見到的她不但無病容,簡直容光煥發,頭髮在腦後束了條馬尾,是她那故事繪本《罐頭pickle!》的插畫有畫到的一個樣子,黑裙搭配閃亮紅鞋的打扮俏麗亮眼,中間這十年被壓縮成一瞬,彷彿光是為了這一晚,她鞋跟一敲,一搖身變回了少女,比當年更美麗。在會場旁邊的披薩餐廳吃餐,她盤子上的食物幾乎都沒碰,卻是看來心情很好講了不少話。我說起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她還記得。看我緊張就安慰我說:「待會兒有甚麼覺得不想答的就拋給我沒關係。」又有新經典的一位編輯同事告訴我,維菁曾對她說:「只要是曉陽姊的事不管是甚麼我都願意做。」
忽然我像有個美少女戰士護衛在旁隨時在我危急時躍出解圍,而我的確也借助了她的力量。活動中每次回頭看見維菁坐在那裡,我的心便安然,彷彿有她在我不會糟到哪裡去。
當晚她有個動作表情是我至今難忘的,是大家聊起《遺恨》的主人公于一平時,為了表示她對一平的喜愛,維菁豎起兩隻大拇指,一臉「我就是愛他」的嬌憨笑意。
她的離去,是于一平失去了一個知音,是我失去了一個知音,一個曾帶給我莫大的閱讀上的喜悅的文友。
想起來不過見過兩次面,為甚麼有個錯覺是更多?回美國後每想及她,總未免牽掛她的身體狀況,總想著下次回亞洲一定要抽空去趟台灣,不為公務而純粹就是玩兼探訪朋友。一定要去看維菁,就我跟她兩個,找個地方好好聊。或許我終於能當面叫她一聲「維菁」,因為我好像還沒有當面叫過她的名字。
此刻她那可親可愛的溫柔身影仍那麼活生生的縈繞我眼前。但這不過是剛開始。以後必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在不同的場景中,黯然想起「維菁不在了」的這個事實。
如果有甚麼可稍慰思念的,或許就是她留下來的書。人是從文壇這個場域永遠缺席了,她的書會被閱讀下去。
作家是她幻想的家人,香港書展的那場講座上她這麼說。
費茲傑羅是她戀愛的對象,辛波絲卡的詩作她用來卜詩卦。
啊維菁,現在我也只能這樣了,到你的書裡去召喚你了。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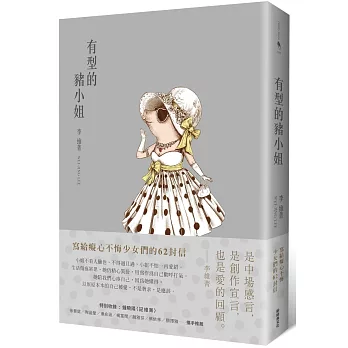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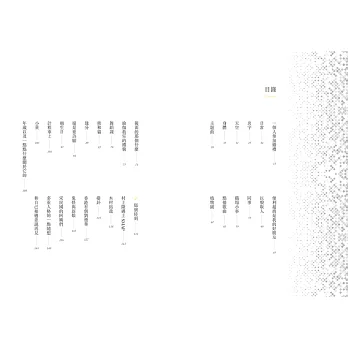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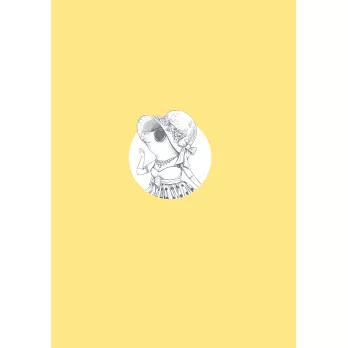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