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故國平居有所思
我和郭春林兄認識多年,剛認識的時候,春林兄正在同濟大學執教,承蒙不棄,贈送了我一冊他主編的馬原研究資料,至今,還是我教學的案頭書。又數年,春林兄在同濟召開孫甘露作品討論會,邀我參加,共話先鋒小說的過去和未來。多年過去,春林兄調到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在王曉明教授的帶領下,轉向「文化研究」,這本書,收錄了他在上海大學五年的研究心得。
我有時會想,春林從「先鋒文學」的研究者,轉向文化研究,從「孤獨的自我」,走向「無窮的遠方」和「無數的人們」,是什麼原因所致,背後,又有哪些力量介入?這似乎是一種斷裂,但有時想想,好像又不盡然。
春林出身中文系,1980年代的文學青年,少有不受到先鋒文學影響的,先鋒文學到底影響了他們什麼,這本身就是一個話題。「自我」大概是一個重要因素,但這個「自我」和1980年代早期的「自我」,是很不同的,或者說,同中有異。1980年代早期的中國文學,可以稱之為一種廣義的「改革文學」,所謂「新時期」,一路的高歌猛進,到了先鋒文學這裡,卻略顯遲滯。「自我」開始游移,感受到孤獨和痛苦,未來不再閃爍耀眼的光芒,理想也招致質疑,懷疑和自我懷疑,多少構成了先鋒文學(包括它的閱讀者)普遍的焦慮,偶然、虛構、真相,等等詞語的介入,也開始拆解1980年代逐漸穩定的意義結構。背後,包含了新一代人(1960)的失望和苦悶。先鋒文學的意義不應被高估,事實上,它對1980年代的叛逆和反思也相對有限,源於自我,囿於苦悶,作繭自縛,或許是先鋒文學的某種寫照,突破成規,化蝶重生,也成為先鋒文學爾後持續性的焦慮。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抹去先鋒文學的意義。儘管先鋒文學後來成為主流,但在當時,卻是以非主流的形象出現,這也同時使得它的閱讀者開始在邊緣的位置上思考問題,多多少少,學會和主流拉開距離,冷靜或者不冷靜地思考自己所處的時代。當然,經過先鋒文學洗禮的這些人,最後又和先鋒文學分道揚鑣。其中的複雜邏輯,不是我在這裡能說得清的,我倒是希望春林以後有機會能把這些問題好好說一說,給後人留一份研究檔案。但我想,只有深入先鋒文學的內裡,才能理解春林,也包括和春林相類的一些人的轉型。似乎突然,但也未必。
但是,從「孤獨的自我」走向「痛苦的人群」,還需要其他更重要的因素,這其中,包括文化研究在中國大陸的興起。
在中國大陸,文化研究的興起,已經不僅僅局限在方法論的意義上——當然,這也很重要,比如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對於許多人來說,也包括春林,文化研究引領著他們走出自我,重新關注社會,關注歷史和現實的中國問題。文化研究不能一概而論,對於春林來說,影響頗深的,可能還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並宛轉進入伯明罕學派,這也是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的理論特色。春林對這一脈絡的經典理論,用力頗深。其中,似乎尤喜雷蒙.威廉斯。春林這本集子的最後一篇,簡要介紹了他的研究心得。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先讀這篇文章,多少可以窺見作者近年來的理論背景。不過,我在此要說的,倒不是這些具體的學派理論,而是,通過這些理論,春林究竟得到了些什麼。
早在198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開始陸續進入中國,那時,中國學界的主要關注點大都在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興起,帶來的,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雷蒙.威廉斯、湯普森、霍爾、阿爾都塞、伊格爾頓,等等。我在閱讀春林這些文章的時候,有時會覺得,重要的,似乎還不是這些理論,而是這些理論勾起了他的某些記憶。這些記憶,不僅通向現實,更通向歷史,明確地說,通向中國革命的歷史。也就是說,經由文化研究,春林開始重新走向馬克思主義,這似乎也是許多人的心路歷程。當然,這一軌跡的理論局限在哪裡,我現在還說不清。
但是,它的意義是重要的,這一意義的重要性,首先在於,人民的概念再次得以確立,並從這一人民的立場重新審視現實(包括審視自己),並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開始尋找個人的歸屬。因此,我推薦讀者重點閱讀本書的後記,這一後記,讀來令人動容。恰如春林在後記中所言,究竟是什麼,導致了他的思想和情感的變化。按照時下的劃分標準,春林也應該算是這個社會的「成功人士」了,教授學者,有房有車,但是,卻有一種力量,在提醒他,在這個世界,還有窮人,還有「無窮的遠方」。因此,他試圖做的,就是重建自己和人民的血肉般的聯繫。這也是文化研究給他帶來的最為重要的啟示,這一啟示已經遠遠超出了所謂的學術,而是生命以及生命存在的意義。
這似乎又要回到1980年代,1980年代的高考制度,包括後來廣受非議的高校擴招,使得一大批貧寒子弟得以進入社會的中上層。其中的一部分被成功規訓,接受並認同這個時代的「新意識形態」(王曉明語),有些,甚至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語)。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卻始終在邊緣處抵抗。他們的出身、經歷,包括家族成員的命運,或多或少影響著他們對事物的判斷,這似乎也能說明,為什麼春林那麼欣賞雷蒙.威廉斯,包括他的「感覺結構」的說法。更重要的或許是,對於他們來說,1980年代開始確立的精英化的知識結構,已經難以容納他們的思想和情感,並最終突破這一結構的制約。這似乎也可以說明,他們為什麼最後選擇了和「先鋒文學」的分道揚鑣。
文化研究在中國的重要性恰恰就在這裡,一旦他們經由文化研究走向社會,現實問題就會紛至沓來,並重新勾連起自己的底層記憶,這時候,很難再讓他們心安理得地蜷縮在「象牙之塔」(儘管象牙之塔的思想也是重要的)。因此,本書的第一輯是非常重要的。儘管這一輯裡的文章比較雜,有些是書評,有些是為某社會組織的眾籌活動而寫。也有些是春林參加社會組織的活動上的發言修改而成,但可以窺見到春林這幾年對中國問題的思考。這些思考目前來看,還不成系統,但一些思想的火花已經開始閃耀。根據春林的這些思想記錄,我大致把他思考的中國的現實問題分成幾類。
一、現代高速的流動性帶來的問題,這一流動性打破了因為隔絕而生產出來的幻象,並開始衝擊相應的美學範疇。「面對面」使得矛盾無法通過審美化解。同時,這一流動性也帶來了底層人民新的苦惱,所謂「無家可歸」。春林近年著力思考新的城鄉關係,大致集中在這一範疇。
二、私有化產生的問題,這一私有化不僅表現在法的領域,同時,也開始向其他領域蔓延,包括倫理、情感、觀念,等等。一種新的等級關係開始產生,並形成一種壓迫性甚至掠奪性的社會結構。而這一社會結構顯然很難為春林所接受。
三、階層分化帶來的問題,流動性和私有化,都急劇地加速著這個社會的階層分化,富者更富,窮者更窮。面對這一階層分化,目前能做的,是反對階層固化,也即要求階層間的流動性。但這一所謂的流動性,實際是以承認階層(階級)分化的合理性為其前提的,是一種無奈的現實選擇。春林大概也很矛盾,一方面,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選擇,所以,他會強調「文化與命運」;但另一方面,他又很難完全接受這些,尤其在理論的層面上。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一上升的空間實際上極其有限。而如何安頓這一「大多數人」,一直困擾著春林近年的思考。
這些問題,不僅纏繞著春林兄,也纏繞著很多人,他們迫切地希望中國能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在這一意義上,我覺得春林兄非常理想主義,這一脈絡中的文化研究,也非常理想主義。
那麼,這條道路怎麼走?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春林的回答是,深入社會底層。這幾年,春林積極投身社會實踐,不僅參加「鄉建」的活動,也開始深入「新工人」群體的文化活動。過去,我們有句老話,「同吃同住同勞動」,是形容幹部或者知識分子深入群眾的做法,現在,把這句話用在春林兄的身上,也非常貼切。在這一點上,我很羨慕春林兄,坦率說,我做不到,自愧不如。
本書的第一、二輯包括春林這方面的數篇文章,這些文章,可以說是隨筆,也可以說是散文,但讀來真的令人感動,尤其〈薄奠〉等。在這些文章中,我是真正看到了春林和工友的那種血肉般的聯繫。這很不容易,說起來容易,真正做到不容易。講學理容易,寫出有溫度的文字不容易。感情的變化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底層的過程中,春林開始觸摸中國真正的問題。讓底層人民站起來,過一種幸福又有尊嚴的生活。這些想法很樸素,可是,我們現在缺的,不正是這些樸素的想法嗎?
但是,什麼是幸福?在本書的第三輯中,春林集中討論了這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他回到歷史,研究了1950-1960年代幾次有關「幸福」問題的討論,另一方面,也在研究現實。這些文章對照起來讀,很有啟發。「幸福」的定義幾經修改,一方面,是國家、集體、精神,另一方面,是小家、個人、物質、日常生活,歷史和現實的交織,令人眼花撩亂。能從這裡突圍而出,尋找一種更合理的幸福生活嗎?這個問題,實際是很重要的。一百年來,中國社會變化的內在動因之一,就是有關幸福的爭論,乃至對幸福的追求。
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春林兄,當然,還有其他學者,尤其是那些青年學者,他們一直在幫助底層人民學文化,包括進行文學創作。他們一方面是輔導,另一方面,也是在向人民學習。其中,春林兄和底層的音樂人來往尤為密切,我揣測,他們想的是如何讓人民自己發聲。這一方面,是對目前的精英文化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對現在流行的文化工業的挑戰。所有這些,對我們來說,實際上並不陌生,中國革命的先驅者,早就做過。這方面,有經驗,也有教訓。結果如何,也很難料。但是再難,也需要有人去做,理論的總結很重要,但實際去做,也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我對春林兄,也對那些青年學者,比如李雲雷、張慧瑜等人,心裡是充滿敬意的。也許,有些人會認為他們傻,但我們現在缺的,恰恰就是這種傻。
書名《倒退著走進未來》,春林的文章中交代,這句話來自雷蒙.威廉斯,的確,誰能說倒退不是另一種前行?往往這樣,在某一個節點,我們進入歷史,進入歷史,不是為了回到過去,而是走向未來。近年,春林在思考現實的同時,也在研究中國的革命史,用功甚勤。本書的最後一輯,傳達了春林這方面的一些思考。我感覺,在這些文章中,他開始進入更加廣闊的思想空間,由「文化」延伸到整個社會的結構性思考。當然,我更希望的是,在我們討論中國革命史的時候,不要回避它的問題,尤其是它失敗的命運。我們既要以成功者,也要以失敗者的身分重新進入歷史,思考未來。往事可追,往事也可鑒。
現在,春林兄遠赴重慶,和他的妻子一起,開始新的生活。我在這裡祝賀他們。我不知道,迎接他們的會是什麼,但是可以肯定,是更加艱巨的工作。也許,春林兄會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也可能會重新回到文學——這兩者並不矛盾,但我相信,這五年的思考,會使春林兄終身受益。一切都在變化,一切都已經改變。
這些話,不敢稱序,只是我閱讀本書的一些想法,謬誤之處,敬請春林兄和本書讀者批評指正。
蔡翔
2018年10月2日,上海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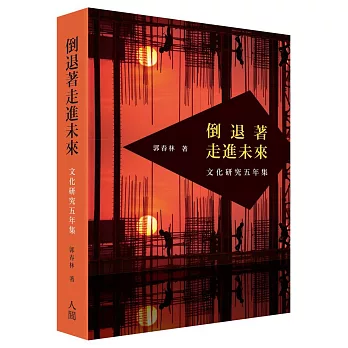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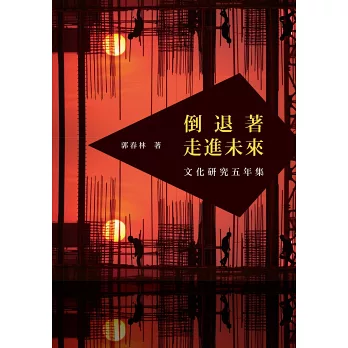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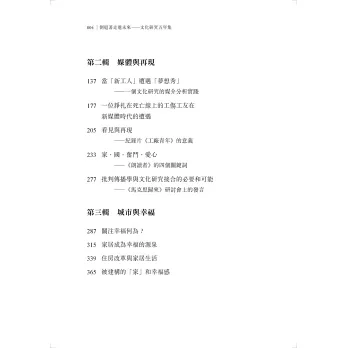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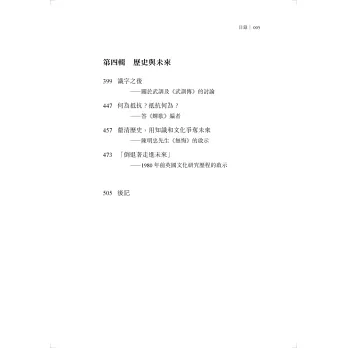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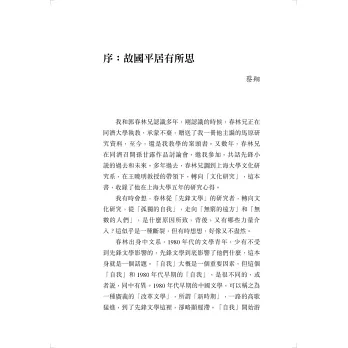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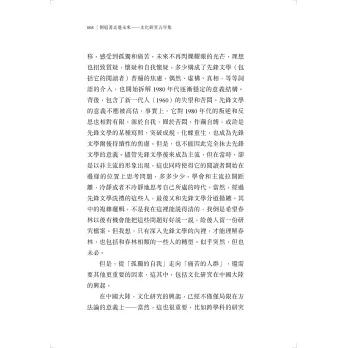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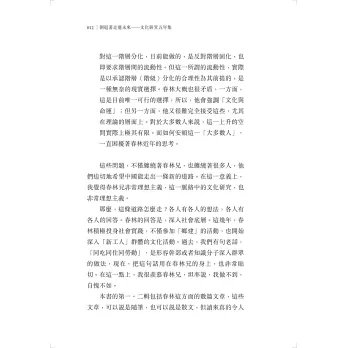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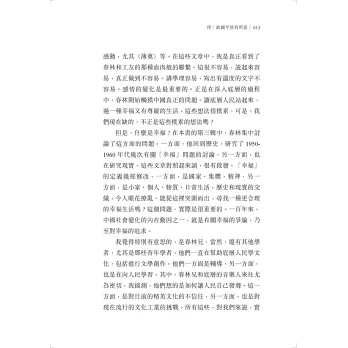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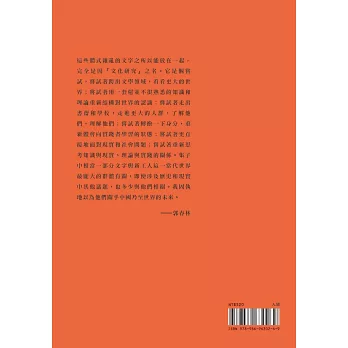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