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眾聲歸來
共分九項的食療法講完,人車已遠去,兩人發著午後熱病似的不小心掉入懷舊的陷阱,但卻不掙扎,甚至暗自有些歡迎,久久總要暖身溫習一番,害怕事蹟湮滅,記憶遭到腐蝕。
出於一種奇異的默契,他們,他、和老蔡,努力的存活,不只為自己,也為了保薦對方的存活。他一點也不知道老蔡擺攤以外的生活狀況,包括他的居處。老蔡也是,可能只有他的電話號碼,這他不確定,因為也沒通過電話。但只要待在這城市的一天,或長或短總會在彼此面前現身,讓對方知道自己的還存在,日日謹慎認真的出示、維繫自己的足跡和糞味,一旦有事時,利於對方的追蹤偵伺。-朱天心,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
對某些政治犯來說,重返社會的一刻人生已經太晚,在「陌生的至親」間無可挽回地過著淡漠的家庭生活,時間讓人變得馴良,肉體再也無法負重,卻依舊匍匐在理想的悲願中。《讓過去成為此刻》第二卷開篇,我們走入了政治犯的晚年,「為了持續地保護自己,」也為了提出對國政有意義的建言,老人無止無盡地投書,寄信。在無人回應的郵件與回憶中,我們讀到「綠島老先生」曾有的夢想,他如何放棄既得利益,將耕地分給佃農,卻在出獄後返鄉得知,鄉人及其後代如何將務農視為負累,「堅定地待他如同佃農對地主。」他付出的自由沒有換來他人的自由,「他成了一個白髮老公公。」他肯定遭到監視,受迫者敏銳的嗅覺令他懷疑這人是特務,那個人也是,他害怕再次被捕,也不甘就此沈默,無所不在的監控一再阻斷他孤獨的「陳情」事業,直到他發現「敵人」原來近在咫尺。
那些曾經的政治犯,後來怎麼了?他們如何記憶?怎樣遺忘?是本卷的核心主題。這涉及威權統治的「記憶管理」:你不可以說。不可言及白色恐怖,也不可言及二二八。人們豎起耳朵聽,卻緊閉著嘴巴。問題是,倘若沒有人說,耳朵要怎麼聽呢?總是有人在說,偷偷地說,以流言,傳說,耳語,種種地下傳播的方式,傾訴著截然不同於官樣敘事的、隱蔽的民間真相。而小說像一把探照燈,領著我們進入傳說的裡面,再裡面。那不是挑戰禁忌那麼簡單,而是思考禁忌,將它拆解,重組,盡可能逼近那「不可說」,將該還的贖還。正如李昂在〈虎姑婆〉中寫下的,「我們的驚恐來自於被教導連親眼看到的事都不能相信,」但「我們知道『它』確實存有。」我們就是知道。
〈虎姑婆〉就是謝雪紅。這篇小說以「三伯父」的魔幻講古,重構了民間對謝雪紅的記憶與虛構,從而偷渡了民間對二二八的記憶,以及其後,關於「匪諜」的種種消息。這三伯父曾短暫入獄,經家人行賄才被釋放,他將自己輾轉聽來的種種官方說法,揉進隱密的民間傳說,給出了一個複雜,立體,百變而充滿肉體感與性能量的革命女性形象。而「那件事」,那件政權不許人們談論的事,「在不能被提及,當然更沒有資料、文字、圖像可見的情況下,以一種更巨大模糊而至無所不在的真實,恆久禁錮在我們周遭。」帶著鮮明的曖昧,化成各種鬼故事,與瘋人的囈語。當土地廟邊拖著四個小孩乞討的婦人,以「匪諜」的身分被捕而謠言紛飛,消失的謝雪紅繼續在小說裡進行她無盡的逃亡,成為一片豐饒的空缺,等待史學與小說的填補,一如「事變」後的地景,那續接而來的白色恐怖,在陳垣三的小說中化為一個彷彿不存在的地方,「浦尾」,寄存著一段彷彿不存在的時間,「浦尾的春天」。
在這篇風格奇異的小說中,有一個很廢的男孩,虛戀著一個同樣很廢的、阿姨年紀的女人,在荒村般百無聊賴的時光中,暫時停擺的廢工寮裡,談著某種廢到不算戀愛的戀愛。小說裡的人物個個有著不清不楚的過去。女人有過一個男人,但那個男人不知怎地消失了,男孩聽說後來有個「便衣」追求過她,而她最終嫁給了管區警察,這警察最終當上了市長。工頭以前是個老師,或許還當過校長,不懂他為何困在這裡。女人的父親混著地方派系,跟「當局」有著無法言明的默契。而那個春天不驚不擾地,在等待復工的「作廢」時間裡緩緩流過,直到工地掘出了一堆人骨,有彈痕的人骨。在陳垣三慵懶幽默的語言底下,我們閃進了一個彷彿大屠殺之後,時間卡住了的墳場地景。之後,我們才得知工頭曾經入獄,並且在人骨出土後再次被捕,一串工人受到牽連。而女人之嫁給管區,是為了尋求庇護嗎?女人過去的男人與工頭有什麼關係?我們都不清楚。這是一篇神祕的小說,神祕於白色恐怖的神祕。
神祕的人骨。神祕的人血。人血在早春的寒流中,化為「圳上的血凍」。楊照在這篇小說中,以大學生的視角,帶我們重返祖輩的「大正浪漫」。這是一篇注青春於革命的純愛小說。純愛的是「阿舍仔」,身為浪漫愛情的受害者,他四處浪蕩,墮落,報復他婚前出軌的妻,不斷重覆著「自責的循環」。妻子在一樁由墳墓遷葬而引致的「鬼的騷動叛亂」裡,死於一件超現實的意外,喪妻後,阿舍投入了反日的鬥爭,前前後後被抓去關了好幾個「二十九天」。阿舍在政治運動中愛上了「博子」,為了守住博子的忠貞,亦步亦趨投入了博子關心的事,因為她「不是那種會乖乖被關在家裡的女人」。純愛的也是博子,她在內心耍賴地告訴自己,「是啊,我是個有可能會放蕩的女人啊,你得一直看管著我喔……」純愛的還有敘事少年的祖父,他每見到博子,內心就「有些什麼在蠢」,而博子是祖父一生所遇「最危險的女人」,她是一個共產黨員。
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共產黨員?藍博洲半生的書寫,都在回答這個問題。在楊照筆下,亡者在生者的夢中歸返,化為一隊隊「沒有身體的傷口」。生者昭告子孫,絕對不准觸碰政治,卻暗暗銘記,留待解嚴以後滔滔述說。生者對政治暴力的敘述衝動,本身,就是最微小的抵抗行動。政權知道這一點,所以恐懼。在言論禁制下,藍博洲早早就孜孜不倦於追索「在臺地下黨」的身世,以口述歷史為職志,抵抗遺忘。小說《臺北戀人》貼著史料,以扎實的細節,第一手報導的形式,還原了「四六事件」及一九四九年的抗爭現場。當時的大學生怎麼搞運動?怎麼做組織?如何在宿舍抵禦軍隊攻堅,以「無辜」掩護「非法」?校長怎麼與高層談判?人如何躲藏?怎麼被抓?怎麼出逃?隔著七十幾年的時差,重返這些細節,只感覺與當代的強烈共振。
就在「四六事件」的下一個月,國民黨宣布戒嚴,大逮捕開始了。地下黨組織在五○年代被殲滅,六○,七○之後,潛伏者逐漸被肅清,槍決案減少了,但白色恐怖並未消退,政權對挑戰者的打擊,甚至延伸到解嚴以後,包括一九八九年自焚的鄭南榕與詹益樺,與一九九一年的獨臺會案。黃凡筆下的「賴索」,是在荒蕪的六○年代出獄的。小說時間啟動於一九七六年,「這一天對混亂如常的世局並不重要,」然而這一天,對賴索而言,正是「一連串錯亂、迷失、在時間中橫衝直撞的開始。」因為,當年逃亡的「組織上級」韓先生從日本回來了,經過二十多年的流亡,韓先生重歸「自由祖國」的懷抱,即將上電視接受專訪。小說領著我們走過賴索的青春,家庭,與婚姻,直到莫名其妙的中年,他成為一個體重四十六公斤,「內在力量消失殆盡」,在果醬工廠上班,一個「矮小、生動、黑色的背影」。他要去電視臺找韓先生,向他討個說法。
一個人被捕多寂寞。在《臺北戀人》裡,年輕人這樣豪氣地說。二十一歲時,賴索也曾在軍事審判官面前,「表演了一次男子氣概,」卻在刑期中變成一個打小報告的人,並且學會了,再也不要崇拜任何活著的人。於今,他潛入韓先生的錄影現場,賊也似的,被工作人員問東問西驅趕著,但他不是來這裡回答別人的問題的,他是來提出問題的,卻在人生中這歷史的一刻,發現,「自己什麼也沒有準備好」。韓先生之「轉向」,與賴索的困頓,令人感到悲傷的,並不是理想的傾頹,比此更一無所獲的是,他們甚至連可以失去的理想都沒有。而賴索的虛無,並非源自無知,或膚淺的犬儒,而是小人物無從掌握個體命運,也無從辨別歷史趨向的無力感。這與東年筆下那種略帶沈鬱的虛無並不相同。
《去年冬天》這部中篇,寫的是七○年代出獄的政治犯,在當上父親迎接新生的時刻,遭逢美麗島事件。小說男主角「王戎」自政治撤退的傾向,優雅地,並未轉向保守主義,也沒有落入輕挑的犬儒,而比較接近於,對政治行動深思熟慮的懷疑。無從掌握也無意掌握政治權力的人,出獄時並無喜悅,反倒感覺,「自己好像上臺替別人演了一齣戲,下了戲退場時,並沒有什麼掌聲在迎接他。」而女主角陳琳瑯,那個原本拒斥政治的少女,反而在步入中年以後,從現實主義轉向精神上的激進派。整部小說就挨著這樣的張力,一路走向悲劇。黃凡的〈賴索〉,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夕,得到一九七九年的時報小說首獎,這樣的題材在當時可說罕見而創新。東年的《去年冬天》完成於美麗島事件後的一九八○年春天,卻因為新聞局的禁令,無法發表。敗者的輕聲細語,與創傷者年邁的癲狂,由小說收容起來,等待未來的讀者。
時間是老人,但遲到的青年會趕上來,以當代的想像力,活潑地,還歷史以青春。於是二○一七年,我們迎來了黃崇凱的〈狄克森片語〉。小說起於一個提問:臺灣高中生必讀的英語參考書《狄克森片語》與《新英文法》到底是誰寫的?前者出自一個由古巴移民美國的混血女性瑪麗亞,後者出自綠島與泰源監獄的政治犯柯旗化,兩個人皆以外國人的身分,教外國人學英語。這是一部思考語言之可能性,語言之安頓意義,語言之橫徵暴斂的小說。語言可以拿來拷問、欺瞞、與威嚇,也可以拿來承載思想與義理。語言可以拿來寫信寫卡片,騙孩子「爸爸在美國留學」,語言也可以拿來養家。政治犯在獄中編寫詞條與例句,比如說:假設句,非事實的現在︱假如我在獄外,我要買車,帶妳出去玩,重新跟妳談戀愛。讓語言代替自己抵達夢想,以這樣機械化的形式寫作,讓自己存活下來。小說一邊思考語言,一邊解開語言的暴力,也寄望語言的解放,讓詞彙自由四散,「退回到面對世界的原初狀態,語言還不存在,事物還沒有名字,歷史正要開始。」
傷殘的身體或許可以靠義肢幫忙,但是,精神是無法裝義肢的。然而,傷殘的歷史或許可以靠小說幫忙,小說是精神的義肢。
胡淑雯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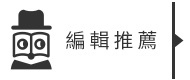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