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的華爾滋 邱貴芬
-解讀林芳玫《達文西亂碼》
密碼Phi
在一九九○年代積極介入台灣婦運的林芳玫出人意料地跨界到文學創作,最近即將出版一部長篇小說,名為《達文西亂碼》。林芳玫擅長媒體通俗文化傳播研究,她的《解構瓊瑤愛情王國》至今仍是台灣女性主義論述的經典作,也是媒體研究必讀。由她來解讀《達文西密碼》,把丹?布朗編組的《達文西密碼》再重新組合排列一番,當然有其獨特的奧妙之處。這本書的敘述者擔任一位女性主義學者的助教,透過她課堂教學資料準備和課堂上講解《達文西密碼》這部小說的種種女性主義式解讀,敘述者過去被壓抑的記憶重新返回,迫使敘述者意識到他所不知的(具有同性戀傾向的)自己,並對過去的人際關係產生不同的聯想與詮釋。芳玫在學界一向以視角犀利、思考靈活著名,這次她又不按牌理出牌,以一篇小說創作來展示她對這本因電影改編而風靡全球的小說的回應,可想而知,此部小說處處珠璣,具有相當繁複的思考面向,卻不失好玩有趣,特別是前半部女教授對《達文西密碼》的詮釋,犀利活潑,後半段轉進敘述者記憶探索,記憶的負擔與沉重才逐漸改變敘述的語調。《達文西亂碼》涉及的議題從解讀達文西、性別論述、讀者反應、記憶、到知識的追尋、歷史的塑造等等,林芳玫筆下從「密碼」轉化來的「亂碼」當然也不是可以簡單破解。
以《達文西亂碼》對應《達文西密碼》。透過《達文西亂碼》來解讀《達文西密碼》對達文西的解讀,亂碼除了一再打亂與挑戰原先密碼提供的解讀秩序之外,卻也提供了一個解讀亂碼與密碼的鑰匙,一個迷人的密碼:Phi。Phi是什麼?書裡提供了這個密碼的解讀:「Phi通稱黃金比例,大約是1.618,它是自然界構成的基本要素。」Phi的一種表現方式為:
(1+√5)÷2
這個讓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數學公式與兩本小說有何關係?兩部小說都指向達文西之謎,達文西的性別「問題」(達文西到底是不是同性戀?)、達文西畫作裡謎樣的性別呈現(柔美的耶穌與使徒約翰、畫作裡雌雄同體的人物表現)、達文西令人讚嘆的藝術之作是否源於他超越世俗性別觀的追求?《達文西密碼》這部小說也有強烈的性別意涵,一般認為作者有意平反女性在基督教裡的位置:「歷代的英勇騎士追尋聖杯、保護聖杯,就是在保護一批關於抹大拉生平的文獻,證明她是耶穌的妻子、替耶穌生了後代」,小說似乎在「宣揚女神崇拜」。機靈聰明的芳玫當然不從俗,自有她另一番解讀的見解:《達文西亂碼》透過《達文西密碼》看似前衛的性別書寫位置(宣揚女神崇拜、凸顯女性在基督教傳承裡的重要性等等)其實仍落入劇情安排以及性別角色刻劃的窠臼:男性角色主導解碼過程,女性角色只能「每事問、事事問」,而且女性角色基本上仍落入女體神聖∕女體邪惡的傳統框架。小說前半部以《達文西密碼》為主的敘述進行當中,我們其實處處可見芳玫女性主義角度批判角度的印記。但是,代表黃金比例的Phi與這種種解讀又有何關?依照小說內文的提示,Phi也是philosophy,哲學:熱愛智慧。Phi展現形式(1+√5)÷2暗示一種人生道路的曲線,必須透過雌雄同體,超越性別分界,才能領悟的智慧。同時,它也強調女性於此道路的重要性。小說裡提到,「女人就像√5」,永遠在拉扯與擺盪當中生成。而1則是男性,單有1無法成就Phi,單有√5也無法讓Phi現形。Phi是(1+√5)÷2,是最高境界的智慧,「是自然界的基礎」,是「完美比例」,卻也是沒完整明顯界線和固定疆域的無理數,沒完沒了。這不是一種固定的標準,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生成」。而(1+√5)÷2究竟是雌雄同體?還是超越性別分界的不可知物(人)?如何想像那小數點之後沒完沒了的Phi,也就是如何想像超越目前人的定義的「人」,而就這本小說推展而言,這是透過記憶的追溯,推向超越個人記憶的遠古集體記憶,那樣的集體記憶超越時空,超越性別,是綿綿無盡的時間所累積堆疊而成的Phi。黃金比例。智慧。自然界的基礎。
《達文西亂碼》與當代台灣文壇
如果《達文西密碼》以性別角度切入,透過記憶來重塑西方基督教的歷史,由於撼動了整個西方文明的歷史理解,造成極大的轟動,非一般通俗小說可比擬。就台灣文壇而言,《達文西亂碼》又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除了沒有創意地把這部小說放在「同志小說」、「記憶書寫」這兩類一九九○年代以來已成文學研究大宗的範疇裡來解讀,我們又可以從中讀出什麼新意?我必須繞個大彎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忘了是在今年哪個台灣大報「年度書選」文學類的報導裡看到,入選二○○六年台灣文學類最佳十本好書,首度以散文書居冠。「散文」是一種獨特的文類,在散文體裡「我」被抬舉到一個制高點的位置來呈現「我」見「我」聞。由於散文體不像小說或戲劇一樣,往往必須設定場景和公共互動的場域(愛爾蘭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說,如他著名小說三部曲裡的最後一部《無可名》〔The Unnamable〕是少數的例外)來進行角色刻劃,散文是「我」的書寫文類,是文類中「私密化」程度最高的創作方式。散文成為戰後台灣文壇的一大文類,與「小說」並駕齊驅,而勝過慘淡經營、苟延殘喘的「戲劇」創作,其來有自。我想這與台灣戰後承襲中國文壇「副刊」傳統與生態有關。「副刊」創立以來,雖與「啟蒙」、「教化」民眾這樣的中國傳統「文以載道」實踐不無關係,但是副刊也因此具有「通俗」的傾向,開放給非專業作家舞文弄墨的重要場域。「散文」的鬆散結構要求與副刊一拍即合。戰後台灣文壇選擇性地繼承了中國五四「抒情傳統」(這是張誦聖的說法),更讓散文成為台灣文壇的重要文類。「我」在抒情散文裡得到最大的發揮。
晚近這樣的散文化書寫更延伸到小說領域來。翻閱二○○六年各大報的文學獎小說類,普遍的特色是沒有劇情、沒有對話、只有主要角色的喃喃自語。這樣的小說創作傾向前幾年即開始浮現,在去年各報紙文學獎的參賽和得獎作品中更為顯著。我想這與最近十幾年來副刊推動小說「輕質化」當然有關。文學獎設定小說發表字數在五千字左右,除非作者功力非凡,否則要在這短短篇幅裡營造對話、劇情鋪陳、和寬廣的視野,談何容易?「散文化」的小說書寫因而是最容易取巧討好的文學獎投稿方式。「散文化」、「私密化」堪稱步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文壇的一大特色。在功力淺的作家手中,「私密化」往往不知不覺中滑向「瑣碎化」,加上對於女性主義所提倡的「瑣碎政治」的一知半解,這樣的「私密化」、「瑣碎化」很快就被視為「政治正確」的當代創作方式而大行其道。但是,所謂的「瑣碎政治」書寫仍有高下之分,寫得好的「瑣碎政治」作品其實仍開展出繁複的思考面向,最膾炙人口的例子是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和後來改編成電影《時時刻刻》的《達樂威夫人》(Mrs. Dalloway),這兩部小說寫的是女人一天中瑣碎家務事的照料,卻在這瑣碎之中帶出「時間」、「死亡」、「人生」這些哲學議題的深刻思考。相對於吳爾芙這樣的瑣碎政治書寫,寫得差一等的「瑣碎書寫」就只有「瑣碎」而已:「我」的小貓小狗、「我」的感情、「我」的旅遊見聞、「我」「我」「我」「我」「我」……,除了「我」還是「我」,私密的我。濃膩得化不開的「我」的渲染創作,卻談不上什麼文本「稠密度」。
除了上述台灣文壇特殊結構和歷史傳承的因素之外,「私密化」的創作趨勢與一九九○年代以來身分認同政治書寫的興起也頗有關係。「個人私密的東西也有其政治性」的批判論述更對這樣的書寫風潮推波助瀾。創作私密化在現代主義時期曾開出燦爛的花朵,作家往內心深處挖掘,開展極度深刻的哲學思考與議題。不過,當「私密化」寫作在當代台灣成為風潮之時,卻顯現一種視野窄化的隱憂。由於副刊主導的創作型態通常要求短小篇幅,作家極容易以文字洗鍊取代思考深度的提煉,在台灣文壇取得一席之地。可能是對這樣「除了我還是我」的創作厭煩了吧,幾年前台灣文學評論家葉石濤先生在一場演講裡就曾提到,台灣的作家其實無須讓自己限制在自己眼睛所見方圓幾里內的眼界(他當時的用詞是「只看到自己的肚臍眼」),台灣上下好幾百年的歷史都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題材,讓創作者可以往大開大闔的方向去馳騁想像力。借重歷史而迭有創作佳績的作家包括王家祥、舞鶴、夏曼?藍波安、平路、李昂等等。除了歷史之外,「自然」也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泉源。吳明益、夏曼、廖鴻基、劉克襄或挖掘深度自然意涵,或探討自然與歷史人文的互動面向,也開創了台灣文學另一番遼闊的景致。芳玫的《達文西亂碼》則另闢蹊徑,展示了台灣文學領域裡非常罕見的一種創作模式:取徑國外文學,開發台灣文學創作空間。自日治台灣新文學發展以來,西方文學即對台灣文學創作者產生重大影響。從俄國的托爾斯泰、杜斯朵也夫斯基對於日治作家的影響、到戰後現代派時期王文興、白先勇師法卡夫卡、喬伊斯、海明威,乃至於後來拉丁美洲魔幻寫實小說對宋澤萊、張大春創作的啟發等等,西方文學作品是「歷史」、「自然」之外,作家汲取不斷的創作泉源。但是,儘管台灣作家對西方文學的關注密切,西方文學正式搬上檯面,成為創作主題的,或是作家在作品中與西方文學展開深度對話的卻不多。楊牧的詩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方文學與台灣文學的關係通常是「檯面下」以「影響」、私淑的方式來進行。林芳玫的《達文西亂碼》以轟動全球的《達文西密碼》來架構其小說敘述,堪稱一部結合性別批判的「讀者反應」小說,凸顯解讀西方小說的過程:小說中的角色女性主義學者解讀《達文西密碼》,並對此部風行全球的西方小說提出獨特的女性主義角度解讀,敘述者則不僅透過此女性主義學者的解讀,來解讀《達文西密碼》,也在這過程當中重新解讀自己的記憶。如果記憶的曲折路徑與歷史的空白、錯認塑造等等是《達文西密碼》發揮的主題,這些記憶的謬誤與糾纏問題也在《達文西亂碼》裡展開另一種形式的變奏。如是繁複演繹台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關係的作品,在台灣文學小說領域裡相當罕見。透過與國外文學的對話來開展小說繁複層次,帶出另一番格局與視野。《達文西亂碼》於台灣文壇的意義,可以從這個角度來關照。
初識芳玫,正是一九九○年代身分認同和統獨之爭在台灣沸沸揚揚展開之際。當時學院的外文系好不熱鬧,不少人從事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積極介入台灣身分認同的辯論,與今日在一片「回歸英美文學研究」的聲浪中進行研究的台灣外文界景象大不相同。我記得與芳玫初遇,是在高雄中山大學舉辦的比較文學會議,芳玫發表一篇論文談論李昂當時引起台灣外文界學者高度興趣的《迷園》,剖析小說中性別與國族認同的瓜葛糾纏,在會場讓人眼睛為之一亮。一九九○年代,我們都還算是年輕的歸國學人,女性主義、身分認同、後殖民論述當道,我們在那充滿希望與理想的熱潮當中,一路在社運、學院生涯和日常生活實踐當中體驗書本的理論,也在實踐過程嚐到未預料的酸甜苦辣。居住在台北之外的台中,我不久就看到我與台北婦運團體的距離,一者因為地理的區隔無法及時參與婦運界的種種運動,更重要的,我發現「女性主義」帶來了批判性思考的無限空間,但同時也逐漸形成一種無形的枷鎖:「我的行為符不符合女性主義標準」成為隨時隨地檢驗自己的一把尺,「解放」的欲求反而帶來反作用力。當時我還未體認到其實「女性主義」的實踐有所彈性,「女性主義」到底是誰來定義?這樣的定義是否不當地壟斷了「女性主義」的意義?忙著在眾多角色中折衝的我沒時間細想。而我相信我的困境與困惑其實也是其他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的共同處境。我早早抽身,決定回歸學術研究,從學院論述來演繹我能理解的性別論述對台灣文化場域的影響。
研究媒體的芳玫卻是選擇在社運的場域實踐女性主義的理想。我不時從平面和電視媒體裡得知芳玫的消息。民進黨初次執政,芳玫被徵召去擔任青輔會主委,放棄了學院的教職。這樣的決定,需要一種奮不顧身的執著與勇氣,是怎樣的理想執著讓芳玫這樣的學者願意在官僚體系的水深火熱當中搏鬥?要準備怎樣的鬥志才能通過那險惡複雜環境的消磨?但是,介入行政高層體系必然也帶來不少學院無法搆著的眼界和視野高度。只是付出的代價自然不小。去年得知芳玫歸隊,回歸學術研究,而且選擇進入台灣文學研究所來接續她的道路。這對從外文界轉到台文界從事教職的我,毋寧是個讓人振奮的消息。相較於早期外文界對台灣文學的關注,近幾年外文界「回歸英美文學研究」的趨勢,讓外文界與台灣文學文化的互動淡薄許多,升等的論文方向要求幾乎截斷了外文年輕學者大力為台灣文學界挹注資源的管道,削弱了不少「在地」思考能開展的研究觸角與視角,在此情況下,芳玫選擇從台灣文學研究所再踏入學界,真是意外的驚喜。芳玫回來了,而且還帶著禮物:《達文西亂碼》這本以女性主義和在地視角重新演繹一部西方重要文學作品的小說創作,提醒我們透過外國文學的閱讀與重寫,我們可以創造出什麼樣的台灣文學空間與格局。台灣作家的創作有無限的寬廣空間,又何需以都會角落裡的喃喃自語來劃地自限?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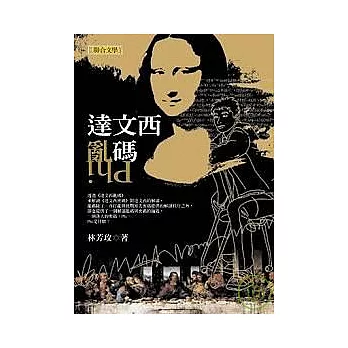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