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寫給穆倫.席連勃
蔣勳
重看了席慕蓉一九八二年以後,一直到最近的散文精選。看到一個頗熟悉的朋友,在長達三十年間,持續認真創作,看到她寫作的主題意識與文字力量都在轉變。而那轉變,同時,也幾乎讓我看到了台灣戰後散文書寫風格變化的一個共同的縮影。
席慕蓉第一本散文集是《成長的痕跡》,作者對自己那一時間的文學書寫,定了一個很切題的名字。席慕蓉寫作的初衷,正是大部分來自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她在《成長的痕跡》這本集子中很真實也很具體地述說自己成長中的點滴,圍繞著父親、母親、丈夫、孩子、學生,席慕蓉架構起八零年代台灣散文書寫的一種特殊體例。
讀到第一篇〈我的記憶〉,我就停下來想了很久。
席慕蓉年長我應該不超過四歲,但是她在〈我的記憶〉裡講到在戰爭中的「逃難」經驗,我愣了一下,那「逃難」是具體的,有畫面的,有細節的。我忽然想起來,我ㄧ出生就跟著父母逃難,但是,我的「逃難」沒有畫面,沒有我自己的「記憶」,而是經由父母轉述的情節。
席慕蓉在〈我的記憶〉裡這麼清晰地描述──
我想,我是逃過難的。我想,我知道什麼叫逃難。在黑夜裡來到嘈雜混亂的碼頭,母親給每個孩子都穿上太多的衣服,衣服裡面寫著孩子的名字。再給每個人手上都套一個金戒指。
我在這裡沒有看到戰爭的直接書寫,但是看到了戰爭前「逃難」時一家人為離散落難做的準備。
台灣戰後散文書寫一直持續著這個主題,是「戰爭移民」離亂到南方以後,安定一陣子,隔著一點安全距離對「逃難」的記憶。
席慕蓉寫〈我的記憶〉是在八零年代,那個時候,每天早晨,孩子跟父母道別,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沒有哪一個父母需要把孩子的名字寫在衣服裡面。
席慕蓉野心不大的散文書寫,並不想寫戰爭,甚至也不是寫「逃難」,而是在幸福的年代輕輕提醒──我們是幸福的。
我初識席慕蓉是在七零年代的後期,台灣還沒有解嚴,我剛從法國回來,在雄獅美術做編輯,也在大學兼幾門課。席慕蓉比我早兩年從歐洲回國,結了婚,在大學專任教職,有兩個孩子,家庭穩定而幸福。
多年後重讀那一時期席慕蓉的作品感觸很深,〈我的記憶〉裡寫到「母親」被人嘲笑,因為逃難的時候,還帶著「有花邊的長窗簾」。別人嘲笑「母親」──「把那幾塊沒用的窗簾帶著跑」。
「誰說沒用呢?」席慕蓉反問著──「在流浪的日子結束以後,母親把窗簾拿出來,洗好,又掛在離家萬里的窗戶上。在月夜裡,隨風吹過時,母親就常常一個人坐在窗前,看那被微風輕輕拂起的花邊。」
席慕蓉對「安定」「幸福」「美」的堅持或固執,一直傳遞在她最初的寫作裡。或許,因為一次戰爭中幾乎離散的恐懼還存在於潛意識中,使書寫者不斷強調著生活裡看來平凡卻意義深長的溫暖與安定,特別是家庭與親人之間的安定感。
席慕蓉持續寫作畫畫,然而她的文學與藝術創作,不曾干擾攪亂她幸福安定的婚姻與家庭生活。
不是很多創作者能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也不是很多創作者在現實生活的安定與藝術之間能夠做到兼顧兩全。
席慕蓉處理創作時的感性自由,與在處理現實生活時的理性態度,有令人羨慕的均衡。尤其做為她的朋友,除了感覺到她在創作領域任由情感肆無忌憚地馳騁奔瀉之外,卻也捏一把冷汗,常常慶幸那馳騁奔瀉可以適當地在現實生活裡不逾越規矩。
喜愛席慕蓉散文和詩的書寫的讀者,應該讀得出她在文字間流露的兼具感性與理性的聰敏智慧。
在精選集收錄自《有一首歌》的散文裡席慕蓉這樣分析自己──
到底哪一個我才是真正的我呢?
是那個快快樂樂地做著妻子,做著母親的婦人嗎?
是那個在暮色裡,手抱著一束百合,會無端地淚落如雨的婦人嗎?
是那個謹謹慎慎地做著學生,做著老師的女子呢?
還是那一個獨自騎著單車,在迂迴的山路上,微笑地追著月光走的女子呢?
席慕蓉一連串地自我詢問,似乎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事實上,她的「謹謹慎慎」,似乎
是為了守護一整個世代在戰爭離亂後難得的安定幸福吧,而那「謹謹慎慎」對生活安定的期盼也一點不違反她內心底層對自由、奔馳、狂放熱烈夢想的追求。
多年前,有一次席慕蓉開車帶我和心岱夜晚從高雄縣橫越南橫到台東,車子在曲折山路裡飛馳,轉彎處毫不減速,幽暗裡看到星空、原野、大海,聞到風裡吹來樹木濃郁的香,一樣還要大叫大嚷,驚嘆連連,也一樣毫不減速。
我坐在駕駛座旁,側面看著席慕蓉,好像看著一個好朋友背叛著平日的「謹謹慎慎」的那個自己,背叛著那個安定幸福的「妻子」與「母親」的腳色。我好像看到席慕蓉畫了一張結構工整技法嚴謹的油畫──(她正規美術學院出身的科班技巧,總使我又羨慕又忌妒,她創作上的認真,也一直使我又尊敬又害怕)但是,她忽然不滿意了,把一張可能受眾人讚美的畫作突然都塗抹去了,狂亂不羈地大筆觸揮灑下,隱隱約約還透露著細緻委婉的底蘊心事。我想像她坐在畫前,又想哭又想笑,拿自己沒辦法。
我喜歡那時候的席慕蓉,又哭又笑,害怕失去安定幸福,又知道自己自由了,像她在南橫山路上的狂飆,像她在大地蒼宇間全心的驚嘆呼叫,看到一個在安定幸福時刻不容易看到的席慕蓉,看到一個或許在更長久基因裡就一直在傳承的游牧種族的記憶,奔放,自由,豪邁,遼闊,激情──我忽然看著車速毫不減緩的席慕蓉說:「妳真的是蒙古人唉──」
席慕蓉前期的散文書寫裡提到的「蒙古」並不多,〈飄蓬〉應該是比較重要的一篇。讀者隱約感覺到席慕蓉應該有另一個名字──穆倫.席連勃。我有一次央求席慕蓉用蒙古語發音給我聽。「慕蓉」聽起來像一條在千里草原上緩緩流著的寬闊「大河」。我很高興我的朋友有一個叫「大河」的名字,她,當然是不應該永遠是「謹謹慎慎」的。
這一本散文精選,分為三輯,第一輯結束在《寫給幸福》、《寫生者》。已經到了接近九零年代前後,台灣從戒嚴走向解嚴是在一九八八年。公教人員的解嚴是一九八九年八月一日,席慕蓉在這一年八月底前就到了蒙古高原。
九零年代以後,台灣解嚴了,一般人容易看到初初解嚴後社會被放大的失序、混亂、吵雜,甚至因此懷念起戒嚴時代的「謹慎」「安定」。
但是,從文學書寫來看,九零以後的議題顯然多起來了,議題多,絕不是「失序」,絕不是「吵雜」,而是一種「自由」的開始。
九零年代,台灣的創作者和讀者,一起開始經驗從剛剛由「威權」控制的「秩序」裡解放出來的「自由」,享受那種忍不住的「自由」的快樂與狂喜。
「自由」的初期總是要有一點放肆任性的,每一個人都爭相發言,用來掙脫綑綁太久的束縛感,用來表達自己,用來讓別人聆聽自己、理解自己。
收在這本集子裡「輯二」的作品,都是席慕蓉創作於九零年代解嚴以後的散文。席慕蓉書寫自己家族歷史,尋找自己血緣基因的作品多起來了。從書名來看──《我的家在高原上》、《江山有待》、《黃羊.玫瑰.飛魚》、《大雁之歌》、《金色的馬鞍》、《諾恩吉雅》,那深藏在席慕蓉血液裡的蒙古基因顯露了出來。她一次一次去蒙古,她不斷向朋友講述蒙古,她書寫蒙古,要朋友跟她一起去蒙古,一九九一年十六名朋友跟她去烏蘭巴托參加了蒙古國的國慶。
或許我們很少細想,台灣解嚴以前,是不會有「蒙古國」的,我們也不可能去參加「蒙古國」的「國慶」。
文學書寫裡的個人和她所屬的社會一起經歷著思想心靈上的「解嚴」。在那個時期,席慕蓉一說起蒙古就要哭,像許多人一樣激動,迫不亟待,要講述自己,講述別人不知道的自己。
有一次跟席慕蓉去苗栗一家作客,主人熱情,當時積極推動台灣獨立,他熱情好客,親自下廚做菜,拿出好酒,酒喝多了,私下偷偷問我:「席慕蓉為什麼老說蒙古?」
我笑了笑,看著這個從早到晚「愛台灣」掛在口邊的朋友說:「你老兄不是也老是說台灣嗎?」喝多了酒,這「老兄」忽然眼眶一紅,就哭了起來。
我喜歡台灣的九零年代,我珍惜台灣九零年代的文學書寫,我珍惜每一個人一次天真又激動的自我講述。每一個人都開始講自己,因此,每一個人也才有機會學習聆聽他人。台灣九零年代的散文書寫記錄著解嚴以後的真實歷史。
收在精選集「輯二」中的幾篇作品相對於「輯一」,篇幅都比較長。很顯然,席慕蓉的散文書寫,到了九零年代之後,由於對歷史時間縱深與地理空間的開展,她前期來自於個人成長單純生活經驗的感觸,必須擴大,可以容納更具思想性與資料性的論述,她在「輯一」裡比較純粹個人感性的散文文體風格,也一變而加入了時代深沉感喟的論辯。
對於熟悉席慕蓉前期文體唯美風格的讀者,未嘗不也是一種新的挑戰。創作者,讀者,都在與整個時代對話,一起見證九零年代台灣解嚴以後的新文學書寫的變化。
〈今夕何夕〉、〈風裡的哈達〉都是席慕蓉第一次回蒙古尋根之後的心事書寫。那是一九八九年,解嚴後的第一年,許多人踏上四十年不能談論、假裝不存在,無從論述的土地,許多人開始回去,親自站在那土地上,重新思考「故鄉」的意義。台灣的散文書寫擺脫了假想「鄉愁」的夢魘回憶。
〈今夕何夕〉只是在找一個「家」,一個父親口中的「家」,父親不願意再回去看一眼的「家」,席慕蓉回去了,到了「家」的現場,然而「家」已經是一片廢墟。
就是那裡,曾經有過千匹良駒,曾經有過無數潔白乖馴的羊群,曾經有過許多生龍活虎般的騎士在草原上奔馳,曾經有過不熄的理想,曾經有過極痛的犧牲,曾經因此而在蒙古近代史裡留下了名字的那個家族啊!
就在那裡,已成廢墟。以前讀到這一段,我就在想,席慕蓉原有散文的篇幅大概已經不夠容納這麼複雜的家族故事了。
在席慕蓉對安定幸福生活的夢想中,有一段時間,她也許不知道,也許不想清楚知道,為什麼父親要長年在德國大學教授蒙古歷史文化,不願意回故鄉,也不願意回台灣。
席慕蓉的母親是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蒙古察哈爾盟八旗群的代表,母親一九八七年去世,在散文書寫裡席慕蓉要晚到二○○四年才透露了母親受到情治單位「監視」的事,收在「輯三」的第一篇〈記憶廣場〉裡寫到一個家庭多年好友在母親去世後說出如下的話:「其實我當初接近你的媽媽,是有任務的,你們在香港住了那麼多年才搬到台灣來,我必須負責彙報她的一切行動。」
進入二○○○年前後,徹底的思想解嚴,台灣的散文書寫裡大量出現自己家族或自身的經驗回憶。在這一方面,相對來說,席慕蓉卻仍然寫得不很多。她的父親母親的故事,牽連著蒙古近代在幾個政治強權之間求族群存活的血淚歷史,牽連著國共兩黨的鬥爭,也牽連著中國、俄國、日本或更多列強的利益鬥爭。
席慕蓉矛盾著,她站立在蒙古草原上,嗅聞著廣大草原包圍著她的清香,或在暗夜裡仰望滿天繁星,淚如雨下,她相信那是父親母親少年時都仰望過的同樣的星空。
然而,她寫了篇幅巨大的〈嘎仙洞〉,追溯到公元四四三年三月一日北魏鮮卑王朝拓拔太武帝的歷史,席慕蓉引證史書,參考當代學者的考古報告,親自到現場勘查,似乎要為一個湮沒無聞的被遺忘的族群曾經存在過的強盛做見證。
那曾經是輝煌的歷史,但那確實已是廢墟。
我更喜歡的可能是「輯二」裡的〈丹僧叔叔──一個喀爾瑪克蒙古人的一生〉,席慕蓉用近於口述歷史的方式,記錄了家族長輩丹僧叔叔的一生,牽連到新疆北部一支蒙古族群從十七世紀以後遷徙流離的故事,牽連到近代二戰中這一支蒙古族在中國、俄羅斯、德國納粹之間求夾縫生存的悲辛歷史,他們十幾萬人東飄西盪,只是要找一個「家」,為了找一個「家」,十幾萬人死亡流散超過一半。
席慕蓉的散文書寫有了更廣大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視野。但是,我相信她仍然是矛盾的,或許她仍然願意是那個對一切美好懷抱夢想,隔著距離,單純嚮往美麗草原的過去的自己,但是,顯然書寫創作使她一往直前,再也無法回頭了。
〈異鄉的河流〉寫父親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逝世,寫跟父親相處的回憶,寫父親的一生,寫得如此安靜──
追悼儀式中,父親的同事,波昂大學中亞研究所的韋爾斯教授站到講台上,面對大家,開始講述父親一生的事蹟之時,我才忽然明白,我一直都在用一個女兒的眼光來觀看生活裡的父親,那範圍是何等的狹窄。
我從來沒有想過應該也對自己的父親做一番更深入的了解──是的,那個在蒙古自治運動遭遇種種險難的「拉席敦多克先生」是席慕蓉散文書寫裡的「父親」,席慕蓉不像有些書寫者可能更重視歷史裡的「拉席敦多克」,她勿寧更願意耽溺在享受萊茵河畔父女依靠著談話的美好時光。
她願望那時光停止,凝固,變成真正的歷史──
三十年前,初識席慕蓉,我們都有健在的父母,如今,我們都失去了父親母親,我們也都有了各自的滄桑。
席慕蓉的散文與詩,在華文書寫的世界,為許多人喜愛,帶給讀者安慰、夢想、幸福的期待。
她的認真、規矩常常使我敬佩,因為是好朋友,我也常常頑皮地故意調笑她的拘謹工整。
但是她一直在改變,「輯三」裡的最後一篇〈瑪麗亞.索──與一位使鹿鄂溫克女獵人的相遇〉,席慕蓉記錄了二○○七年五月她在大興安嶺北端探訪八十歲鄂溫克女獵人的故事,敘述一個只有兩萬多人口的鄂溫克人,鄂溫克人分為三部,而其中,使鹿鄂溫克人又是三個部裡人數最少的一支,如今已不到兩百人。
席慕蓉看到瑪利亞.索,她寫道──
山林已遭浩劫,曾經在山林中奔跑飛躍的女獵人,白髮已如霜雪,一目已眇,卻仍然不肯屈服,寂然端坐在自己的帳篷裡,隱隱有一種懾人的氣勢。
這篇壓卷的作品不只是一個女獵人的傳奇故事,也在寫使「山林浩劫」的現代文明。席慕蓉反覆詢問著、質問著,一種敬天愛地的傳統存活方式,為什麼常常被認為與「現代文明」衝突。而巨大國家政策的「封山育林」又將使這些世代狩獵維生的小小族群何去何從?
席慕蓉的散文書寫有了更深沉也更現代性的命題一本精選集的出版,書寫者回頭省視自己一路走來,可能忽然發現,原來走了那麼久,現在才正要開始。
有了滄桑,不再是父親的女兒,不再是丈夫的妻子,席慕蓉的文學與繪畫,是不是又將要有全新的起點了。
席慕蓉一定知道,說這句話時,我是心裡悸慟著說的。我多麼希望在自己的書寫裡永遠不要面對滄桑。但是,如果一定要面對,相信這條路上,是有好朋友可以結伴同行的。
──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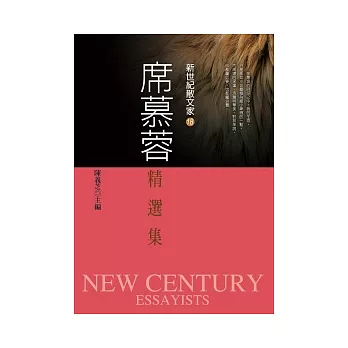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