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豐饒複雜之心靈地貌
保羅.奧斯特原著,王穎導演的電影〈煙〉中,有這麼一個橋段:一個雪茄店老闆在十四年的時光裡,堅持每天八點從店門向街口拍攝一張照片,如此看似隨機、無法籠罩涵蓋全貌的取樣,因為累積了十四年,奇異地形成一種「同一時間、空間,人類的某種生存狀態」。在我的想像:「年度小說選」是一個類似的紀錄(只不過它是以一年為單位,以短篇小說而非攝影)。它必然有漏缺(選入的作品群隨每年不同編者的口味而有不同面貌),它像是時光河流裡的刻舟求劍,妄想以這樣一本十多篇短篇小說,讓許多年後翻開此書的人們相信:喔這是二○○九年台灣小說創作(我更奢望是班雅明的「全景幻燈」:這個島的人們某種存在狀態之模型、小型心靈史、一間集體夢境的檔案室)的某種陳列和收藏。
這次編選二○○九年年度小說選,有幾點心得:
一、這樣以一年為時間截切面,儘可能閱讀此間曾發表過之短篇小說,深深感慨我們這座島嶼(以小說為其鏡像)所濃縮、摺藏、化石岩層壓擠,如此豐饒複雜之心靈地貌。幾股九○年代以降的敘事伏流:原鄉、情慾、性別、認同、都市漂流、青春啟蒙……仍匯聚、混種,如王德威先生當年描述之「眾聲喧譁」。
二、表面上看這次選出諸篇,似乎鄉土題材為對象的作品比重極高。事實上我在挑選過程閱讀大量各地方文學獎作品,確乎被這樣題材的繁殖、重複和話語的封印凝固,而產生「單一性」之隱憂。我想解釋:這並非我個人閱讀小說口味的結果,而是透過學院、大報文學獎、地方文學獎……層層文學機制建構的結果,當我們下一世代最好的寫手們,全把小說視鏡凝注在那憂鬱的鄉土,我難免擔憂一種生物學上「顛峰適應」之後的記憶體單一化。不過,這次收進的諸篇之間,完全像不同鑽石切割手法,不同的語境,在似乎相似的本土視窗後面,其實是落點在西方現代小說時間地圖差異極大的霰彈分布。從小說語言(譬如周芬伶、陳淑瑤、陳雪、胡淑雯,完全不同貼伏筆下人物的世故、體會、哀憫與「活生生的氣味」,完全不同的風格語言);從觀看視距(譬如許琇禎的〈裹〉那強大寫實彷彿復刻三○年代經典卻異境的素描力;或童偉格那難以言喻,揉合卡夫卡、塔克夫斯基、福克納的飽漲詩意的視窗);想像力的炫耀(譬如甘耀明的〈天公伯青瞑〉、壹通的〈壁虎〉);以時間為對象之形式操作……
三、在儘可能翻尋過去一年之短篇小說的過程,發現「短篇小說」這一文類,有點像照片裡站在那些溶化浮冰上一臉茫然的北極熊。報紙副刊一年內刊登的短篇小說數量少之又少,主要的「貨源」竟來自文學獎得獎作品;少數那兩三本文學期刊;再就是拆自長篇中某一章節,以短篇形式發表之「折子戲」。就長篇觀之,二○○九年其實可算台灣青壯輩小說家進入創作成熟期的豐年;陳淑瑤的《流水帳》、陳雪的《附魔者》都是個人藝術性的巔峰,甘耀明《殺鬼》的出版,更備受矚目。在天后朱天心惜墨如金,讓人望眼欲穿(王德威語)舉重若輕的時光與懺情賦格之書〈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終於出手時,童偉格散見報章的幾個短篇,站在不同的舷窗眺望時間的光弧。隱隱然有一種「小說狂飆」的風雲再起,在這些重裝小說騎兵軍,列陣在台灣被翻譯小說如漫天蝗群吞食成一片荒原的敘事地表,讓人幸福又期待「下一輪小說太平盛世」真的將要展開?但短篇小說確乎如波赫士的「夢中老虎」,奇異地存在於一個寂靜的、不為人知而高度技藝的祕境。這當然是老梗,可能每一年年度短篇小說集的編者都要唏噓感傷一番,而我的心情其實更像保羅.奧斯特筆下那個雪茄店老闆,其中的一個早晨拍下的照片,我的感想是:「還不賴。」瀕臨絕種的威脅一直存在,然物種自有其存活的本能,以最嚴格的小說技藝標準沙裡淘金,我們還是撈捕到十來篇發出神奇光輝的美麗作品,或有遺珠之憾,實乃選集之篇幅限制。
朱天心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以一種「小說百科」的全景透視,「赫拉克利特河床」的小說覆蓋小說之幻技,寫暮年之哀。
之前拆散發表過的兩個不同版本,情境環繞著一對「沒打算離婚,只因彼此互為習慣,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塊化了的溫吞好酒如久洗不肯再回復原狀的白T恤的婚姻男女」,一場重建昔時豐饒至福之時光廊的贖回之旅。兩種不可思議的小說之於時間暴動。此次選入之「神隱」,為同一主題的第三(乃至更多)種形式之變奏。
從《古都》起,朱天心的動員不同時光重瞳凝視,剝解,漫遊一座城不同身世、記憶、物質史的「萬花筒寫輪眼」即已臻極限,黃錦樹當年評為「都市人類學」、「都市社會中資訊 / 垃圾處理機的深沉憂鬱」。後仿影響者眾(包括筆者)。此次在〈神隱〉這個系列篇章組成的短篇,更將這樣鏡廊之城的魔術,一組「誤解辭典」,樁植進「衰老」這個抽象的時光主題。
這樣同時往虛空孤獨搭建不存在之棧道,甚至飛翔叩問包括波赫士、大江、馬奎斯諸大家暮年時亦踟躕夢遊、思索的神祕之境;同時展現禽鳥變化焦距之切換小說話語的強大控制力。我以為在華文小說中對小說之形上思辯與實踐,朱天心不愧是另一層次的小說家了。
童偉格的〈將來〉讓人想起馬丁.艾米斯的《時間箭》:「當生命顛倒著走時,一切竟然變美好了。」奇怪的是,「將來」作為這篇小說之篇名,恰像童偉格自《無傷時代》即發展出來的時光劇場。核爆過後的世界,一種靜默的瘋狂。計時失去了任何藉以形成描述人類存在之意義。與回憶相對應的是一個被永恆取消掉了的「現在」。那是一個死亡的時間,「已經」終結了,但無法在重建同時解決這一切枯荒絕望曠野的物理時間仍在前進,所以形成一種難以言喻,未來比昔時還陳舊的「塔克夫斯基的荒原」。
未來的世界發生著什麼事呢?一種保護著─甚至如在碎成破片的倒影世界裡傻笑著,如失聰者、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痴」─《無傷時代》的,父不在的以及父亡歿所踟躑的兩個鏡像世界,以超荷於「小說所能贈予、贖償真實之空無」的願力而黏貼模型那樣「小小世界真奇妙」的一個空間化的「白銀時代」(借王小波的書名)。
那是我所能想像,小說家用不可能之死物與屍骸,用一「借來的時間」讓他們活在宛然畫面裡,而我們看著這個畫面。古怪又詩意。其實是因為童偉格將那「災難」的耳半規管從所有飛翔的情節之鴿子內裡摘除掉了。那變成一個「空望」:有校園、有軍營、有村落、有家庭、鄰里親人……存在這些地貌場所上活動並進行著什麼的人際關係。但那是一個死者們的「今之昔」世界。
每次讀童偉格的小說,總讓我心生悵遠感。我會反省:怎麼回事?這傢伙小我十歲,但我曾經可能靠近的那純粹書寫時光為何一去不回?
甘耀明的〈天公伯青瞑〉是長篇《殺鬼》中一個篇章,讀到這樣的小說,只能感嘆「祖師爺賞飯吃」,好像完全不受限書寫的任何重力限制,任意竄走、變形、流動、蹦跳……,在一種嘻嘩痴傻的狂歡中(確實像《百年孤寂》、《鐵皮鼓》、《惡童日記》的混血變種),不可思議的畫面像妖術幻術擎天祭起,想像力噴灑,讓人瞠目結舌。這種推到極限的「夢遊者視窗」(連背景畫面都像超現實畫顏料旋轉)背後其實帶著極大的暴力之內化:在殖民與戰爭的雙重暴力下,「殖民者是瘋子,被殖民者是傻子」,於是像主人公pa這樣的神力超人,便像宮崎駿卡通頭被斬掉的憤怒神祇,歷史認同與文明場面悉數消失,所餘僅最原始肉身的怪物化,劈神殺鬼搖天撼地;以及跟在身後像歌隊群眾演員的痴傻學徒兵。這樣的大敘事在西方有其傳統,譬如〈痴兒西木傳〉或〈好兵帥克歷險記〉之「流浪漢傳奇」。但甘耀明的小說魔術在於將這些原本嘲弄、質疑暴力施與者的痴兒、傻瓜,與新世代透過好萊塢電影、日系漫畫、動畫的強大視覺運動感結合了(赫克力士般的大力士pa竟可以舉著欺敵的大鐵盤將美軍軍機擊落,這不是〈海賊王〉是什麼?)。並且可以將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日語在這樣孩童化初民化的「馬康多世界」裡,形成一個豐富流動的雜語劇場。
周芬伶的〈八又二分之一草原〉亦是一篇「後廢墟時光」的優美小說。九○年代末以降在身體密林、流動慾望、母系家族故事之探幽勘微,已累積一份繁麗景觀的女性書寫,將之結合土地思索。家已崩毀,情人也棄走,土地又在大自然嚴酷肆虐的臉貌下,變成一脆弱、無可依傍的浮土。這樣的故事卷幅,讓人想到D.M. Thoms的《白色旅店》,作為女性易感且傷痕累累的精神地貌,夢遊般所遭遇、所發生的全是孑然一身的女子穿行過災難橫行、屍體意象紛紛墜落的空曠死蔭之谷。這樣的敘事女聲,如多麗斯.萊辛,如愛特伍,常帶著一種教養與憤怒,風格與尊嚴,往昔記憶已成時光債務,卻必須和原始野蠻之惡土重新抗搏,建立諒解甚至新的抒情性之可能。小說中那只有十九歲的園丁是一個帶著神性的角色,他和女主角共同經歷的唐吉訶德式遭遇,其間饒富趣味、詼諧、透澈的對答,使得這篇小說在不能承受的廢墟絕望中,溫情脈脈,無比自由。
在陳雪的〈附魔者〉中,「父之罪」在傷害啟始的神祕時刻,在那人間倫理慘不忍睹的光影濛昧暗室,她並不是將之放置在一精神分析式的辯證,而是進入一神祕主義的攝影。那些台灣市井男子的陽剛、暴烈,分三段曝光式的「聲音與憤怒」截切記憶,面對那個被父所玷汙,卻以「女兒之愛」包裹柔覆之的神性少女琇琇,反而啟動了他們的「附魔」。這是一篇把性寫得如此純淨,畫面諸人卻如孟克之「吶喊」被超越他們能承受的瘋狂和光焰所擊毀、壓碎。陳雪寫這些剽狠男子為那附魔而無法重回人間義理秩序的語境惑亂,寫他們為那無比妖豔無比純真的羅麗塔所激發,像八家將起乩的猙獰與痛苦,我覺得放在整個華文小說裡亦屬傑作。
陳淑瑤的〈落雨炸〉是她那時光卷軸畫般的《流水帳》其中的一章。那確像沈從文的〈靜〉,完全沒有現代主義小說時間的焦迫和扭曲,如此恬淡、慢來。整幅畫面是一屋老小女人─阿嬤、阿母、阿姆、少女們,在讓男人心慌的夏雨(因為瓜會泡爛)「困住的時光」裡,在屋內歡鬧地炸番薯。那像黃頁農民曆其中一個節氣,這群澎湖女人們如夢似幻在時光流動的一小格單位。如果以全本長篇來看,那像《紅樓夢》、《海上花》一般慢速情節的兇險或改變這些人物命運的暗潮洶湧,都藏在這些折子戲、單幅靜物畫,疏眉淡眼的素描後面。(看似若無其事,其實流光偷渡遞轉,線索攥抓、惘惘威脅)。即以獨立短篇看,〈落雨炸〉這樣一個像是微物之神調控了無數聲音、光影、空氣中節氣的氣味和憂鬱,所有女人(女孩)們卻明晃無憂地笑著,這一切讓人讀到胸口承受不住的「畫框外」的巨大悲傷(因為「地老」了?老去的女人和年輕的女孩同樣擱淺在這困頓時光),又好像並未真的發生什麼戲劇性的事件。我以為這是一難度極高的慢速書寫。
張萬康的小說語言一向帶有極強的原創性和暴力。譬如這篇〈半吊子〉,每一小段文字都擠滿表情,全是聲音與憤怒。這種「幹醮體」─從剛過世的沙林傑,到中國大陸王小波,到印度天才女作家沙娣.史密斯,甚至魯西迪─通常以單一的個我如何對龐大堅固異化的資本主義大峽谷豎中指,如唐吉訶德對風車奮力擲出鏢槍。那註定是挫敗、荒謬、憤怨並髒話連篇的,「活的超敗」。對我而言,這樣的小說直如夢幻逸品,一種小說話語的噴湧與飆舞,一種對撲天蓋地的部落格、msn、噗浪廢話,語言退化的,一種小說語言躁鬱又暴力的反擊。那麼古怪,不被允許進入(女體)的性,那麼邊緣不被允許進入(群體)的遊晃,卻每一個句子像被割斷頸子宰殺前的雞,怒意勃勃的掙跳。這真是一篇「過於喧囂的孤獨」。
伊格言的〈花火〉,則借北野武的電影名片,寫青春的哀歌,因為某種命運的設定(北野武電影裡是妻子的絕症,而這篇小說直到最後才翻底牌原來是男主角得了絕症)形成敘事中不時暈散出一種末日的倒數,哀愁的預感。一種品質性努力假裝在正常世界活著的孤獨。與童偉格、甘耀明同為三十歲這輩作家領先群的伊格言,極早便建立其充滿詩意與鏡頭效果的語言風格,甚至可算是如今鄉土魔幻的最初實驗者之一。我卻驚喜見到這樣一篇類乎加拿大女作家艾莉絲.孟若的舉重若輕,不那麼狂歡,不那麼稠密,卻探索流離與失格處境之短篇,那預示著音域更寬廣的小說可能。
胡淑雯擅寫傷害版神隱少女,〈液體的記憶〉是城市裡的愛麗絲漫遊,好奇攝像那街巷裡謀生男女的眼瞳卻死灰慘白,那使得她踩過的城市地面,皆灑滿玻璃碎渣:行李箱內的無名女屍、陌生人的歧視、急診室的氣味、塞擠這城市暫居遊牧青少年的貧窮感、自殺癮患者……其間扭轉之謎皆在於階級。這樣的角色,在「世紀末的華麗」已過去十年的台北,談論著上個世紀成長小說永遠的經典《麥田捕手》,「不成熟的人,渴望為某個理由高貴的犧牲」,那難免讓人喉頭一緊,像補綴著裂成片片的,我們這個世代努力將自己打破、變貌、離散,終於「到處不存在」的記憶。追憶流年似水成了真正各式各樣的體液。而原本以為會流光血液變成屍體的小異,卻將〈慾望街車〉翻轉成〈變形記〉變成了女人。「治療何時終結?」「矯正如何收止?」如果童偉格的田園詩是一座完美的精神病院,胡淑雯的城市則是縫補系的一間外科急診室吧。
費瀅的〈鳥〉讓我想到王朔的〈動物兇猛〉滿漲著光影、樹木與市集的氣味;似乎每一個字都有表情:作為成長小說,這樣的文體有一種青春才有的本色和奢侈:晃遊、動物性、無結構無工匠技藝痕跡,一種令人欣羨的滿溢,但或正是王安憶曾說的,典型的,可遇不可求的「處女作」,那麼鬃毛發著光的原創與力量。
許琇禎的〈裹〉展示著令人懾服、強大的寫實能力。奇幻的是以一台灣作者,動員中國三○年代小說之話語氛圍,嚴密構建了一個宛然如在,如超現實夢境的「擬寫實主義小說」:一個賈樟柯電影中的視鏡。大陸春運車站鐵柵欄外的流民,單一的個體(包括物質、尊嚴、甚至我們慣習對小說人物的身世縱深,皆被剝奪了)在流體般的群眾中旁證著那更巨大、無明的剝奪。閱讀這篇小說時很容易召喚起我們在不同年代閱讀的許多小說:茅盾的、殘雪的、韓少功的……,一條小說話語印象的河流。讓人戰慄亦不是,哀憫亦不是的一個森冷而恐怖的「花布頭巾」劇場。
書寫一個並不在場,異質卻宛然存在的「中國」(一個劇場,一張「霧中風景」式的底片而反照出一趟旅程,甚至存在於之前的許多篇小說的擺設、元素與符號);讓我們反思那不同臉貌的「阿嬤」們,家族照片、廟戲或葬禮,……是真實存在的「台灣」嗎?
而阮慶岳的〈廣島之戀〉,借莒哈絲劇本、雷奈電影(甚至莫文蔚與張洪量的情歌),像Ozon的〈砂之謎〉那般電影膠卷的曝光與反差,「廣島」成了一對同志愛侶在東京旅館房間,電視播出的二戰美軍投擲原子彈紀錄片畫面。連擬借名字典故的城市都界質迢隔地由電影的時光意義(而非真實的時光意義)。「他們為何要在廣島丟下原子彈?」「非這樣做不可的。」「為什麼?」「因為他們害怕如果不這樣做,別人會對他們先丟下原子彈。」「這是被迫以及不自由的選擇嗎?」無聲的,遙遠年代以前的,幻異超越人類自毀極限的原爆影像,成為愛侶間孤獨、渴望靠近,卻又本能地離開、傷害對方的形上迷惘。
壹通的〈壁虎〉的魔幻技藝讓人想到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古怪、陰森、說不出的詭異,將一個典型的台灣老阿嬤之死,從傳統語境剝離孤立,以一個「地獄變」般妖麗噴燄的金爐裡鬼物、爬蟲、人頭混戰互咬,充滿運動感的冷酷異境,嫁接對應上真實世界裡阿嬤離世這事家族子孫既徬徨卻又淡漠無可如何的認命。事實上老人活著的時候,到死亡的發生,都和土地公廟神桌之鳳梨紅燭、紙錢、乩童老人,甚至「帝阿公」這類神明,虛實不分,孤獨內向於一個老輩人存在其中,斑斕神祕、既寒傖卻又豐饒,鬼神認識論的小宇宙裡。
這樣將不同感官界面、不同次元時空壓縮、錯置成一「如夢之夢」的短篇構造,到了楊富閔的〈逼逼〉裡,呈現了一個背景聲如嘉年華狂歡,不同國族、不同歷史時空、不同記憶感性,卻挨擠於「此在」─佳里(家裡)─的布萊希特「勇氣媽媽」本島版(「猛嬤」)舞台。如果說以童偉格、甘耀明為本土魔幻之極限展現了「死者與亡靈」之境,〈逼逼〉則是一個「活著」的世界:因為活著,所以委屈與榮耀、風流與負欠全被時光泥河混沖成一種老輩人自嘲、堅韌、詼諧的熱鬧與無奈。寫古詩的讀冊阿公、大地之母的水涼阿嬤、菲傭、大陸假新娘、電腦世代年輕兒孫、越南媽媽……〈逼逼〉真是把巴赫汀之「眾聲喧譁」小說之雜語特性用眼下台灣活蹦亂跳、生香活色的語言劇場。一如文中所言:「多謝五十年的妳。像詩。」
那不啷的〈回家〉可視為這些年文學獎某一系書寫:「家變」(森田芳光的〈家族遊戲〉?三浦朱門的〈箱裡的造景〉?)之變貌。「家」作為這個資本主義都市人際關係最基本隱私之最小單位,其實早被揉碎擠壓不成框格,父不父、母不母、子不子、女不女,身份在其間瞬變流離。個體的自由、慾望的實踐、經濟的焦迫……讓「家」的倫理對位變得僵直單薄,但用「搬」到「回」之意象來重建這種關係廢墟中,一種細微索索、含蓄溫柔的「愛之能力贖回」,這是一篇讀了讓人心生暖意的小說。
同樣的,當年輕一輩的小說創作者以魔幻風格炫示著高蹈華麗的電影運鏡視覺,強大的物質界面遞換幻術,語言音樂性與挪借象徵的技藝,像林聖月的〈爬牆〉這樣一篇閑淡悵然、敘事充滿懸惦卻什麼事也沒發生的「新感覺派」,便顯得秀異罕見。有點近似石黑一雄的淡景與壓抑。你以為是校園師生同志小說,卻沒有體液橫流,沒有傷害的身世,主人翁像隔著霧玻璃看這世界,靜靜的生活,拘謹地感傷。
駱以軍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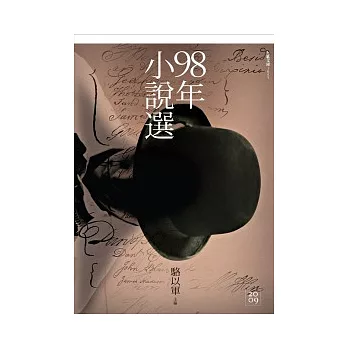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