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為什麼要寫《老子這樣說,這樣活》
人們多愛貼標籤,或說把人歸類,聽說我寫了《老子這樣說,這樣活》一書,朋友就說我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這當然省事。只是我不知道文化有什麼需要保守的,那些聲稱需要保守文化的人其實是在玩弄文化,使得窮苦匱乏的心靈深受污染、毒害。文明的每一次大創造之後,都會產出不肖子孫來敗家造孽,偉大的五四諸子之後即如此,偉大的先秦諸子之後也如此。我寫老子,希望能夠藉老子的人生來示範一種文明或人生常識。
時至今日,愈來愈多的人明白,我們的現代轉型是一種僭越人生常識的仿生生活,一個偽現代笑話。這其中有錯誤,更有罪行。用西方人的話,人民都犯下這樣那樣的罪錯了;用我們東方人的話,這是我們的共業。我們共同的業力帶來了共同的報應,水的污染、空氣的污染、食品的污染、土地的污染,地火水風或說金木水火土都污染了,天怒地怨……這個笑話通過手機、網路、電視等傳媒,無遠弗屆地傳遞給大家,大家笑過後繼續造業。
我帶著我的《老子這樣說,這樣活》回到闊別兩年的「首善之區」或所謂的文明社會,仍為房價等盛世現象吃了一驚。聽著八○後朋友說開車堵車的憤怒和無奈,看著那些權貴或超級富豪們一樣堵在人生的路上,聽說少有人知的知識分子將有長達十一年的和諧歲月,學者也不得不做電話訪問……禁不住想到我的類人孩們,他們或我們至今仍無走路權也不會走路,沒有交友權也無意集會,沒有說話權也不敢自由放肆,我明白共業之於當代的意義。
在上海,我跟朋友去新落成的虹橋二號機場時,朋友們走進平行滾動梯裡,我則在一邊昂首闊步,結果我遠遠地走到了朋友的前面。朋友們出了便捷的滾動梯後一臉沮喪,問我為什麼有先見之明。我說,無他,看見了前面有三個人高馬大的「類人孩」,只要有三個以上就會擠作一團,自然會把滾動梯裡的快步通道擋住。
我同樣仍為媒體的無恥和勢利而吃驚。一個義大利朋友說,你出去這麼久,沒看到你們的媒體更垃圾了吧。那麼多的小說、養生、中醫騙子……都是有毒的啊。是的,我確實看到了那麼多談身心健康的書刊,看到了那麼多跑馬場繼續無恥地跑馬圈占同胞的頭腦和心智,看到那麼多養生班、生命調理一類的講座。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但這都是怎樣的醫者和媒者?捨本求末地指導同胞的生活、裝模作樣地妖魔化我們的祖先。而五四一代和八九一代,這社會的中堅兩代,多少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卻也仍緣木求魚地、隨波逐流地關懷自己所謂的身心健康。
我知道有權的媒體仍在威福,無勢的媒體在裝孫子做二丑地媚俗或媚雅;只是確實仍為我的朋友參與其中的罪行吃驚,雖然我的媒體朋友多半不會同意我的意見,我一些媒體朋友甚至感覺好極了悲壯極了文化極了。媒體不願意發表年輕無名者的思想,不願給精神生長的空間,它們說,那樣的文字太慢,那樣的文字需要解釋,那樣的文字沒有市場……它們追求把大家的眼光抓住的速食文字,讓大家的心跳、腳步、呼吸、生活節奏加快,再告訴大家要注意平和、身心健康;它們提倡文化,它們自己從不曾有三天安靜的狀態去讀書思考親近自然;它們污染讀者和市場,卻說是在為讀者和市場服務。它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笑話,不覺得自己在造業。
我在《非常道》裡收了有關魯迅的一則軼事:在他去世前兩三年,他跟朋友談論最多的話題是「中國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說:「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網密犬多,獎勵人們去當惡人,真是無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聲對朋友說:「遺憾的是,我已年過五十。」我經常想起這條言行,因為我自己也年過不惑,我日益面對自己失去新銳敏感的心靈而無能自已。
是的,我已經日益脫敏。我不願意冒犯我的朋友,不敢冒犯我們的媒體。我不再是一個敏感詞了。但這一切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啊。我的身心疲憊。我跟同胞一道犯下業力。生態、世態、心態秩序完全失衡,我們多多少少參與了這種種罪行。我寫了龔自珍以來的「中國男」,讀者朋友好意地理解為是我呼喚純爺們的作品,其實我哪裡還有那樣的心力。
在一個污染的時代,個人有何作為?我經歷了中年喪亂,在窮窘孤絕的狀態裡,我回到自己的文明源頭,我寫《老子這樣說,這樣活》,我知道只有能夠面對自己的人才有解救之道。我在公開場合盛讚存在主義思想家毛喻原是「中國的齊克果」,毛先生說一個人的幸福程度在於他面對自己時微笑示意的程度。我希望我的《老子這樣說,這樣活》能夠救贖自己,我們必須先把自己救出來。確實,在寫作《老子這樣說,這樣活》的日子裡,我對自己的微笑最多了。那確實是開心的日子。我希望我寫的文字能夠慰藉人類的良心。吁嗟默默,誰知吾之廉貞?有朋友說,《老子這樣說,這樣活》是我回向社會的溫情之作,我同意。老子本來就是一個有著至情的人類之子。就像人們對我的誤解,說我是中國精神的最大破壞者一樣,人們對老子的誤解也是令人悲憫的。
據說老子的《道德經》的西文譯本有兩百多種,在西方的傳播非我們所能想像。大數學家陳省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當年進愛因斯坦的書房,看到愛因斯坦的書不算多,卻有德文版老子的《道德經》。時隔半個世紀,陳先生還記得那一情景。但從黑格爾、尼采、托爾斯泰到愛因斯坦、海德格,都未必讀懂了老子。卡夫卡坦言:「老子的格言是堅硬的核桃,我被它們陶醉了,但是它們的核心對我卻依然緊鎖著。我反覆讀了好多遍。然後我卻發現,就像小孩玩彩色玻璃球遊戲那樣,我讓這些格言從一個思想角落滑到另一個思想角落,而絲毫沒有前進。通過這些格言玻璃球,我其實只發現了我的思想非常淺,無法包容老子的玻璃球。這是令人沮喪的發現……」我希望這些往而願返的現代精神能夠在我的書中找到呼應、安慰和歸宿。
我在上海短暫逗留的時候,北大的朋友給我出了一個上聯:海上繁華難破老子寂寞。我對的下聯是:山中雲水願征諸君深情。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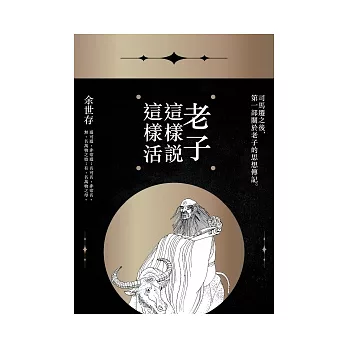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