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不老文字的魔法泉源
何致和
就文學作家而言,厄普代克應該算是最熱衷書寫續集的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兔子」系列每隔十年出版一部,連續寫了四十年。以虛構猶太作家亨利.貝克(Henry Beck)為主角的小說亦寫了三集。就連美國總統布坎南(James Buchanan)這位歷史人物,他也拿來作為題材先後寫下一部劇本和長篇小說。厄普代克作品產量驚人,幾乎年年都會繳出新作,他為以前寫過的長篇小說加個續集,倒也不是什麼出乎意料之事。
不過這次他真的讓人跌破眼鏡了。《東村寡婦》(The Widows of Eastwick)是《東村女巫》的後續之作,這兩本書的書名,厄普代克只改了一個字,把「女巫」(witches)換成「寡婦」(widows),讓人一眼就能看出兩者的賡續關係。《東村女巫》出版於一九八四年,故事時間背景卻是六○年代晚期,三位迷戀魔法與愛情的女性主角,彼時皆為三十歲左右的輕熟女。這部作品曾被好萊塢和百老匯看上,改編成電影和音樂劇,在銀幕舞台熱熱鬧鬧紅極一時,導演和編劇相中的不外乎是這三位女性主角的年輕貌美,以及她們追求愛情與慾望那種無所畏懼的動人魄力。然而,當厄普代克在二十五年後,又讓這三位女性回到那一年被她們鬧得天翻地覆的東威克村(Eastwick)時,這幾個女人都已龍鍾老矣,光是一個人的年紀就已比當年的兩個人加起來還多。生平喜愛琢磨性愛情色題材的厄普代克,竟然會對像這樣的三個老女人感到興趣,這點當然會令人感到訝異。
在前作《東村女巫》的故事中,雖一樣具有厄普代克慣常關注的主題,但憑心而論,這部作品只能算是遊戲之作。儘管這三位女主角都是明顯的女性主義者,或多或少反映了美國六○年代末的激進主義女權運動,可是作品的分量仍難以與「兔子」系列相提並論。厄普代克在相隔近四分之一世紀後,為這部不怎麼叫好的舊作編寫續集,對向來需要大量題材的他來說原本無可厚非。只是,新作《東村寡婦》出版才三個月,厄普代克便因肺癌病逝,讓這部小說「意外」成為他漫長寫作生涯的最後一本長篇小說。
許多讀者不能接受厄普代克驟然辭世,也不能接受《東村寡婦》竟是他留給世人的最後一部著作。厄普代克寫小說向來不注重結構,他總是緩慢優游在自己的故事叢林中,興致來時,甚至會在原地停留,一頭鑽入某個場景或思緒中,讓情節久久不動。對《東村寡婦》這樣的一部續集,讀者的期待當然會落在這三個女巫一起返回故里後所造成的騷動,但厄普代克並不急著這麼做。他先讓這三個女人跟著觀光旅行團,前往加拿大洛磯山、中國北京和埃及金字塔遊歷,並且花了近百頁篇幅,仔細描寫這些知名景點,又一點一滴記錄下這幾個女人旅途中的見聞與互動。這樣的慢條斯理不免引來詬病,讓許多首次閱讀厄普代克的讀者感到失望。有人認為這部小說的前一百頁根本就是冗長乏味的旅遊導覽或文化觀察報告,與那些活力四射的女巫八竿子扯不上關係。也有人認為,儘管厄普代克的女巫故事夠資格稱為女性小說,但厄普代克根本就不瞭解女人內心世界之複雜,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太太。
關於這樣的指責,讓人不得不說,如果你以前沒接觸過厄普代克的小說,那麼《東村寡婦》不應該成為你閱讀厄普代克的第一部作品。老牌作家和忠實讀者之間存有一種默契關係,透過長時間的文字相處,在某種程度上可說已有點像老夫老妻那樣親密。對讀者來說,他早已熟悉作家創作上的脾性習慣,既能欣賞作家長處,也能以最大的寬容接受作家的偏執與缺憾。對作家來說,他知道自己的讀者能容忍他在創作上的任性,這樣的包容讓他自在安心,使他在揮灑時擁有更大空間,可恣意讓靈感橫徵暴斂為所欲為。這種作家和讀者隱而未宣的共謀關係,往往能造就出不凡的作品,甚至是作家能否走得長遠的關鍵因素。厄普代克一生作品產量豐富,光算作品數量就是個超自然現象,說他有魔法加持也不為過,而這個魔法的泉源,正是由無數讀者所形成的。在一路伴隨厄普代克走來的讀者眼中,喜歡書寫自己所處時代與中產階級生活經驗的厄普代克,他的作品就像是一個個時空膠囊,替他們完善記錄保存了他們曾經如此用力生活過的世界。
從這個角度來看,厄普代克把人生的最後一部著作留給《東村寡婦》,可說完全恰如其分。厄普代克寫作此書已高齡七十六歲,而他筆下三位主要女性人物的年紀也不遑多讓。你可以說他不夠瞭解「老女人」,但你絕對不敢說他不瞭解「老人」。厄普代克如此寫道:
你活在世上,周遭是越來越多的陌生人,在他們看來,你是個可以丟掉的礙眼的幽靈。只有像珍這樣認得在俏麗、探索的盛年時期的她的人,才能夠原諒此刻正在老去的她。
唯有老人才能瞭解老人,尤其是那些老人在年輕時就已經認識的朋友。無奈的是,隨著時光流過,這樣的人不斷辭世,日漸凋零。《東村寡婦》無疑是厄普代克在辭世之前,寫給老友的最後話語。他在小說裡忠實記錄下各種尾隨在老人身後,無論如何都揮之不去的陰影:死亡、癌症、失能、失去重要性、失去家庭親情、失去性能力與愛情滋潤。他不期待年輕人的理解與同情,因為老人們也有尊嚴需要維護,他只透過這三位不甘於平淡的老女巫之重聚,來安慰他的同世代朋友:「面對現實吧,親愛的。他們只認為我們很無趣又讓他們丟臉。只有我們才會在乎我們。」
話說回來,對尚未進入老年期的讀者來說,《東村寡婦》絕非沒有可觀之處。厄普代克小說的特質都還在,尤其是他的招牌優美文字。他如此形容戴面紗的阿拉伯婦女:「面紗後面那靈活而水汪汪的眼睛直視外面,像是被抓到的甲蟲那亮閃閃的背部。」甲蟲油亮的背部除了在視覺畫面上能用來形容眼睛,背後更含有被困住之甲蟲欲振翅飛離的希望,完美隱喻了面紗後的婦女的存在處境。好的小說家往往是善譬者,而厄普代克這方面的功力顯然更高人一等。他在《東村寡婦》中展現意象鮮活且層次豐富的譬喻修辭術,足以證明他的文字仍充滿活力,永遠不老。
除了文字,厄普代克在此書中也同樣展現出第一流的觀察和批判能力,他的目光仍銳利無比,批評的火力也依舊強大,完全沒有因為年紀和衰老而有半分消退。儘管他在小說首章對異國地景與文化的觀察,對在地人來說可能不是那麼地道,充其量只能算是個有思想的高級觀光客。但當小說到了第二章,當三位女巫重聚在虛構的東威克鎮,讓厄普代克結束觀光之旅回到國內後,他馬上恢復成最頂尖的歷史學家、文化研究專家、社會批評家、神學家和人類學者。他從生活出發,細膩描述他眼中美國社會的諸多現象,有時諷刺挖苦,有時沮喪感嘆,無一不深深說進美國人的心坎。
這是厄普代克小說的共同質地,不過在《東村寡婦》中,他除了和過去其他作品一樣寫出了美國人的集體意識,還坦然寫下了自己的恐懼。他不止一次透過主角亞麗珊卓之口,說出他擔憂和恐懼癌症的心情:「你害怕什麼東西,就會使它成真。就像一個懼高的人走在一條窄窄的木板上,他一緊張就會失足而摔下去一樣。」透過這樣的作者與其筆下人物的情感相通關係,我們可以合理推斷,故事中亞麗珊卓對年輕時所做錯事之懺悔,在某種程度上應可代表厄普代克在耆老之年回顧人生時的心境。小說中的亞麗珊卓害怕罹患癌症,只是因為擔憂年輕時對別人施展的惡咒會報應在自己身上,但厄普代克早有癌症病史,那種不知癌症何時會捲土重來在體內哪個地方復發的恐懼感,即使是最厲害的小說家也難以向人言明。厄普代克或許已預見自己的死亡,他在寫下《東村寡婦》百日後旋即辭世,讓這部作品成為他留給世人的最後遺言。此書也許不該是你閱讀厄普代克的第一本書,卻絕對會是你無法繞過或閃躲的一本小說。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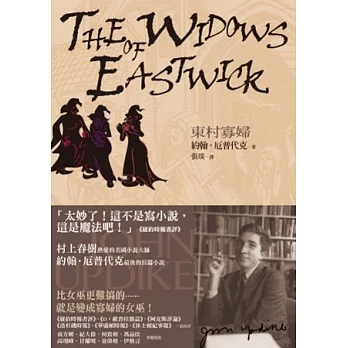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