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航向烏托邦《小國的靈魂》的閱讀策略∕吳叡人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阻擋不了浪潮,那就航行吧。」--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
1.
在後福島的年代--在資本主義全面失控,物質主義洪水肆虐,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重新崛起,人類精神再度淪入荒原狀態的頹廢年代,分處地球一南一北的兩個小國,兩座在洪水中遙相對望,殘存著夢想與純真的島嶼,成為受困的人們想像另類文明的投射對象:南亞的不丹,以及北歐的挪威。試圖以「國民幸福指數」(GNH)的浪漫神話取代「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的不丹,象徵著牧歌式的,前資本主義秩序的最後淨土,而以小國航行於強權夾縫的惡水之中,一意追求屬於自己的民主、平等、質實剛健、自主獨立而又兼善天下之道的挪威,則代表著另類的,後資本主義秩序下的文明典範。厭倦了貪婪與慾望的無限擴張,不甘於自我毀滅坐以待斃,以及渴望從帝國強權欺凌下獲得解放的,受苦的,受困的人們,於是紛紛築起想像的方舟,航向這兩座世界邊緣的烏托邦之島,航向島嶼靈魂深處,在過去與未來的夢想之中,過去與未來的夢想之間,搜尋屬於現在的希望。
2.
李濠仲這冊《小國的靈魂》,就是一部受困中的臺灣人航向烏托邦的紀錄,而他選擇的目的地,是未來之島--挪威。然而如同所有的烏托邦紀行,如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波斯人書簡》,《小國的靈魂》也是一冊雙重文本,記錄著平行的,或者交錯的靈魂探索之旅:文本(text)是挪威,次文本(subtext)是臺灣,而文本與次文本之間,則存在著一片比較,對照,與反思的餘白。所以,《小國的靈魂》的一個可能的閱讀策略是,順著這片餘白,思索挪威與臺灣的分歧與交會,探究從「北方之道」(Norway)迂迴通往南方之島的航路,並且想像南十字星如何可能閃爍在恆久的白夜。
3.
為何南方之島會渴望北方之道?臺灣人這個「北方意識型態」從何而生?答案其實是明顯的:對於百年來一直依附於美、日發展模式,乃至如今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向當代中國發展模式靠攏的臺灣而言,挪威經驗代表了一種更為優越的文明選項。理由是列舉不盡的。比方說,首先,做為高度資本主義化國家,挪威卻有效地馴服了資本主義惡靈,建構了以平等主義為核心價值的均富社會,與令人豔羨的社會福利體系。其次,擁有北海油田的豐富資源,但卻自我節制,以後代為念,不濫用資源,同時也悉心愛護國土環境。第三,做為民主先進國家,挪威不僅在國內的民主、人權的表現舉世敬服,讓歐、美、日瞠乎其後,甚且還成為對外輸出民主、人權、和平與其他進步價值的最重要國家。第四,做為僅擁有人口五百萬的小國,現代挪威的文化成就驚人,出現了作家易卜生、哈姆笙,音樂家葛利格與畫家孟克等偉大藝術家,界定了整個現代人類心靈的風貌。最後,也是最為驚人的,就是做為國際政治的小國,挪威不僅靈活運用結盟與不結盟的策略,長期遊走於對峙強權之間,更進一步超越現實主義邏輯,有效建立人權推廣與和平中介的「品牌」,發揮軟實力,成為國際政治中道德規範的仲裁者。
如此一幅富而好禮,天人和諧,自尊自主,兼善天下的小國圖像,如何不讓長期仰大國鼻息生存,現實、「務實」到幾乎喪失了夢想能力的小國臺灣人也為之動容動心呢?對美與善的事物動心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然而我們不得不先抗拒這個渴望--因為挪威與臺灣同樣身為「小國」的事實,只是地緣政治的表層現象。我們必須深入這兩個國家形成的歷史--他們在世界史出現的時間與過程--才能比較正確理解與分辨這幅動人圖像之中,哪些是結構與偶然(contingency)的產物,哪些是意志與智慧的選擇結果。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無法複製,難以抗拒,屬於命運(fortuna)的領域,而後者才是我們可以師法的,可以從事行動(action)的範疇。
4.
首先,讓我們觀察這兩個小國在世界史出現的時間。現代挪威國家的形成屬於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形成運動的最後一波,整個過程在二十世紀初期已經完成;而臺灣的國家形成,則與二十世紀亞、非與東歐殖民地發展為民族國家的前後幾波浪潮重疊,是一種「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至今仍在發展之中。雖然兩個國家的形成史都有「連續殖民」的類似結構--挪威在五百年間先後為丹麥、瑞典所支配,而臺灣則在四百年之中經歷荷蘭、西班牙、清帝國、日本與(美國支配下的)國府的連續外來統治--然而在世界史出現之時間差異,從一開始就促使這兩個小國走向歧異的發展道路。這個命題有兩個主要涵義。第一,從一八一四年的埃茲伏爾憲法到一九○五年正式脫離瑞典獨立,挪威在這九十年之間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基本工程,也確立了高度穩固的民族國家認同。臺灣的國家形成源於日治、國府兩政權的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與制度積累,而在八○年代後半以來的民主化過程中才逐漸確立國家意識,然而這個晚熟的國家認同至今尚未穩定,使臺灣因內部分裂,遲遲難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國際政治行動主體。第二,挪威獨立(一九○五)雖然較西、北歐各國為晚,但仍然在第一個主權國家壟斷組織(亦即一九一九年的國際聯盟)出現之前,因此不僅獨立門檻較低,並且還有機會參與日後國聯與聯合國的建構與發展,甚至運用此一舞臺合縱連橫,創造小國的國際空間。臺灣的國家形成時間與中國的國際崛起重疊,以致遭遇到被中國支配下國際主權國家壟斷組織驅逐、封鎖之命運,不僅獨立門檻大幅提高,而且也完全無法運用此一舞臺。
5.
挪威的民族國家形成運動的第二個重要歷史特徵是,民主化不僅是民族建構工程(nation-building)的一個重要面向,同時也先於工業化而發生,這使得民主、人權、平等諸價值比經濟發展先得到鞏固與確立,成為挪威政治文化的霸權價值。這是當代挪威社會平等主義、民主、人權等非物質主義的普世價值比在一般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獲得更高尊崇的原因。然而民主化之所以先於工業化出現,主要的結構性因素,在於挪威沒有土地貴族階級,卻存在著強大的自由農民層。十九世紀初期挪威民主化與民族形成的動力,主要正是來自這個領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層與城市的激進知識分子的結盟。這就是現代挪威左翼政治霸權的社會根源,而勞動階級政黨則是到了二十世紀三○年代才在政治上崛起,取代農民階級成為主導階級,並且開創了挪威著名的組合主義體制(corporatist regime)。專研民族主義的當代挪威政治學者托尼森(Stein Tonnesson)稱這個由農民而工人的政治整合過程為「經由階級路徑而形成民族」(class-route to nationhood)的模式。
這也是臺灣完全無法複製的歷史經驗。臺灣的民族國家形成,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模式。一九二○年代臺灣民族運動的出現,主要是由若林正丈教授說的「土著地主階級」,亦即臺灣本土地主階級所主導,戰後民主運動的主導力量,則由一九六○年代的地主階級仕紳,轉換為一九七○年代以來的新興中產階級。而不論戰前、戰後,臺灣的弱勢階級如農民、勞工等,都長期受國家力量的嚴厲壓制,遲遲無法形成政治行動的主體。臺灣左翼政治傳統的薄弱,適與挪威的左翼政治霸權成對比,究其結構性根源,恐怕在於臺灣移民社會階級形成的相對不穩定,以及先後殖民國家的長期鎮壓。而左翼政治傳統的薄弱,可能就是造成臺灣社會重自由而輕平等,重物質而輕人文之政治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6.
前述信手拈來的兩個例證,已足以說明挪威經驗的特異性,源於特殊的歷史經驗,因此非常難以複製。然而這絕非意味挪威經驗對臺灣毫無價值;相反的,學習「北方之道」的歷史經驗,對於臺灣人有無比的重要性,因為唯有理解歷史的限制與可能,我們才會懂得如何在歷史給予的條件下,冷靜地衡量與選擇我們的夢想與行動,並且公平地評價我們所擁有的成就。在處於內部分裂、民主倒退、貧富不均、文化淺薄,以及國際孤立困境的臺灣人眼中,挪威的圖像當然無比美好,然而只有深入理解挪威和臺灣的歷史--這兩個小國的靈魂--之後,我們才會理解到命運與偶然的力量,才會體認到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們是在何等惡劣的條件下,經歷多少艱辛歷程,才獲致了今日如此微小,但卻無比美麗的成果。
寫出傑作短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臺灣小說家龍瑛宗曾經在日治末期的隨筆〈熱帶的椅子〉(一九四一)中,抱怨臺灣的熱帶風土過於感官,野蠻,以致無法產生偉大的思想與文化,然而他接著說:
對於生自熱帶本身的文化,我是悲觀的。然而,既然生在熱帶,就不能對精神風景的荒涼袖手旁觀。自然是豐饒美麗的,但卻是文化的荒蕪之地。然而即使是寥若晨星,也想在那裡種上精神之花。
無獨有偶,挪威最偉大的劇作家易卜生也曾經在晚年如此描述他的祖國:
北方的人們所擁有的偉大而嚴厲的風景,以及寂寞與封閉的生活……迫使他們不去麻煩其他人,而只專注於自己的事,所以他們變得深思而嚴肅,他們思考、懷疑,甚至絕望。在挪威,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哲學家。而在那些黯淡的,覆蓋著濃霧的冬日裡,啊,他們多麼渴望陽光啊!
因為南方灼熱明亮的陽光,才迫使重感官的臺灣人開始思考自身的貧困與豐饒;因為北方嚴厲陰暗的寒冬,才迫使耽於思考的挪威人開始追求白夜的色彩,北方之光。我們都是自身歷史美麗與殘缺的產物,但我們不甘於只是歷史的產物,於是我們熱烈地觀看彼此,相互描摹。闔上《小國的靈魂》,我將挪威美麗的景致銘記心中,讓它誘發我的想像,然後用最臺灣的熱情,最挪威的虔敬,一段一段尋找、一筆一筆描繪從南方之島通往極北邊境的曲折航道。
二○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南港
序
二○一二年新年過後,挪威航空公司總裁休斯(Bjorn Kjos)接受挪威外國記者協會的約訪,親自在公司總部為我們簡報挪威航空的年度大計。自先前站上歐洲最大低價航空公司寶座後,休斯已購入最新機種,準備將挪威航空推向全球,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航空公司,首架直飛泰國曼谷的班機,當時已萬事俱備、蓄勢待發。雖然休斯態度溫文儒雅,卻掩飾不了個人自信滿滿的雄心壯志,就這約莫五百萬人口的小王國而言,休斯的表現稱得上相當有氣魄,真人不輕易露相的他,或許也是想藉此在我們這群外國人面前略展威風。
半個世紀前,挪威還是斯堪地那維亞最窮困的國家,一個世紀前,它仍是瑞典的屬地,兩個世紀前,它則歸於丹麥的附庸,歷史上有將近六百年的時間,它完全臣服於鄰國,二次大戰爆發,納粹軍隊亦曾占據挪威領土。總之攤開歷史,北歐童話世界述說的不光是美好無瑕的故事,至少落在挪威身上是如此。近代以來,挪威屢有如休斯這樣一號人物在歐洲社會崛起,意謂著它歷經瓦礫堆裡的重建,已然脫胎換骨。
在我暫居挪威這段期間,剛好是挪威各方表現最為成熟的一刻,產業經濟前景欣欣向榮,社會福利制度運作無礙,國家財政健全穩定。二○一三年二月出刊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將具有獨到政經制度的挪威、瑞典、丹麥和芬蘭視為下一階段可供各國政府學習參考的「超級模範」(The next supermodel)。
挪威自一九九○年建立起規模龐大的「政府全球退休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Global,詳見第十八章)後,從此邁入一個生老病死皆得照護的烏托邦社會,其境界堪稱斯堪地那維亞世界裡的一枝獨秀。因為舉國滿溢著平等主義,當地藍領勞工領取的工資,足足是英國同階級者的三倍,另一方面,挪威企業「CEO」平均的薪酬,則屬全球最低,人民貧富之別,遂得以有效縮減差距;少數原本運作顢頇的公務部門,在有效運作轉而私有化下,已可望逐步擺脫過往沉痾;販售石油和漁產,雖然為挪威帶來了豐厚的國家財富,唯藉由出口兩者獨門的生產技術,才真讓挪威油、漁產業相繼跨足全球。長期享有優渥的社會福利,政府組織隨時予以靈活應變,還能同時保有本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這是經濟學人奉其為超級模範的原因,就我幾年親身所見,它對挪威的褒揚誠屬切實而不浮誇。
然而我相信北歐國家發展的良窳,除卻人為制度,背後獨有的人民性格,應該會是一切作為的起始源動,挪威人也是據此勾勒出今天外界所見的北歐式思維。若純然推介挪威外顯進步的樣貌,似乎難以解釋它一路走來,究竟是順著什麼樣的軌跡得以絕處逢生。於是我一頭鑽進它的歷史和它的生活,試圖尋找一個足以被譽為先進國家的民族特質。我將幾年親聞所見撰述為文,為的即是希望有機會穿透挪威社會的表層,直接探究它的內在價值,或許可為社會升、沉的關鍵。過程中,我總忍不住拿它對照自己生長的家鄉,以寄望由此填補我們熟知的缺口,最好有機會迎頭趕上,甚至更加美好。
自二十世紀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性格決定命運」之說,這句話所能涵蓋的範疇,可能已不光局限在精神病理現象,民族的性格,不也同時左右了國家的命運?好鬥者帶來戰爭,怯懦者扶植獨裁,皆有史蹟斑斑可考。挪威是什麼?這也許還是個次要的問題,它所代表的民族性能對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啟迪作用,或許才是我於字裡行間最真摯期待的想像。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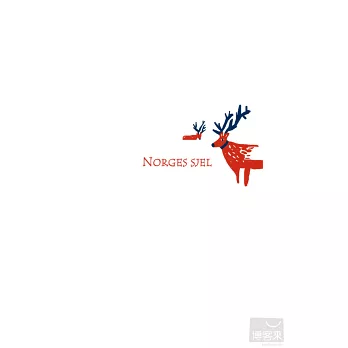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