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危機後的新局 卜大中
法國哲學經濟學家索爾孟把他最近幾年的筆記集結成書,對當時的國際事物給予針貶。作為新古典自由主義的信徒,他對金融海嘯後主張政府積極干預,並制定法規限制金融界的活動很不以為然。
他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前,2007年美國經濟已經開始衰退。是衰退造成金融崩盤;不是崩盤造成經濟衰退。他批評歐洲國家知識分子的許多想法是來自一種負面情緒-反美,因此看不清歐洲的真實問題所在。
我讀索爾孟的著作,感覺他是個理性、中肯、溫和、樂觀而又淵博的歐式知識分子。他擁護自由市場,定義自由經濟是良好的資本主義內涵,但也批評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所以即使金融危機還沒過去,他依舊反對羅斯福、克魯曼和史提克里茲那個系統經濟學家所主張的政府介入。他說,減少政府的干預才是經濟復甦的法門。這是他一貫反對大政府的立場,沒因金融海嘯而修正。
他親自到中國、印度、埃及、日本、韓國、土耳其觀察研究,並提出意見。對哪個國家都沒有成見,其立論的心態是與人為善,語句溫和慈祥,但也犀利地分析那些國家的問題所在。例如,他發現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是蘇聯高層統治階層的罪惡感。而這個罪惡感是中國統治者所沒有的。
他對台灣很有好感,贊不絕口,但對中國則有很多批評和意見。他對歐洲福利國家造成政府大量負債很不滿意,要我們注意不可重蹈歐洲式福利國家的覆轍。他強調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包括社會責任、創新、法治等元素,指出中國經濟的問題在於仿冒、跟隨,沒有創新的精神。
金融海嘯後,政治經濟產生很多反省。社群主義者如麥可.桑德爾等主張「社會愛國主義」,把道德元素加進經濟裡。大政府管制派,如克魯曼、史提克里茲則主張政府干預財經部門。索爾孟算是古典自由主義者,堅決捍衛自由市場、小政府、有限的社會福利。同時,他對中國的意見也很中肯,我們對他關注全世界的精神深感敬佩,期待他再寫出鞭辟入裡的文章和書籍。
台灣版前言
由於生性樂觀,我將談一談台灣。何以是台灣?有誰能在五十年前觀察得到,這個曾既遭孤立又遭威脅的台灣,現儼然已成亞洲最繁榮的國度之一,兼具科技新革、文化創新及民主聖地等優點於一身呢?絕對無人能預測得到,因為譁眾取寵式的災難預言,遠比正向樂觀式研究探討容易得多。自 1972 年起,我每有機會,即會順道造訪台灣,並對台灣人民的信心,日益堅定。我在此無需重述台灣如何從貧困進化成相對富裕,以及從專制獨裁蛻變成開放社會的過歷程,因為此成就眾所周知——在我已出版的著作《謊言帝國》中已提及。我對台灣人民深具信心,他們才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人」。
當我們訪問中國大陸,只能觀察遭共產政權羞辱後的中華文化災難:剷平城市、破壞廟宇、散盡祖產、簡化漢字、具獨立意志的藝術家不是身陷囹圄,就是遭到流放。假如我們想一探中華文明的精髓,台灣當然是最佳的場域:倘無台灣,中華文化可能早就像遭蠻族蹂躪後的羅馬文化,需在考古學中睹物思情了。
年紀稍長的台灣人民及悲觀主義者可能會向我提出抗議:在台灣的中華文化雖未受專制獨裁政府的摧殘,但卻飽受商業化及美國文化的肆虐啊!我可不贊同此種酸葡萄式的心態,因為當局者迷;我們未牽涉其中,反而較能全盤且客觀的觀察,台灣堪稱是一既亙久又彌新中國的最佳展現:假如中國大陸未落入共產黨之手,很可能各方面的發展就完全像另一個台灣。
任何文化或文明,是會與時俱進,而非不可撼動的。假如在臺灣的中華文化是僵固不變的,早可埋進墳墓中了。為何中華文化能在台灣倖存下來,或許是因為台灣人民「中外兼具」的特質?換句話說,台灣人民跟大部分的已發展國家一樣演進進化,從簡單的身分認同,變成多重的身分認同。五十年前,大家都曾侷限在單一屬地及文化:我是法國人,你們是台灣人。但現在,我既是法國人,亦是世界公民;而你們亦是台灣人,也是世界公民。現在你我都是世界公民,法國文化與中國文化往昔彼此剝奪削弱的時代早不復在,現取而代之的是彼此互相滋潤增長!
唯有專制獨裁的政權及個性乖戾的心態,既無法理解也無法喜歡以上具現代性身分認同的蛻變。有人將之稱為「全球本土化」,即是「紮根本土,胸懷世界」的展現,可讓生活更具多彩多姿。藉由閱讀本人法語著作的中譯本,或許可讓某些台灣讀者心靈充實。對我而言,直接與台灣讀者對話,暸解他們的想法,也讓我增進見聞。我對台灣發展樂觀並非是一膚淺情緒的展現,而是一植基於具體的論證觀察:倘無台灣,我可能不會快樂,我將跟台灣同在,享受另一多彩生命的愉悅!
導讀
金融海嘯之後 一個哲學經濟家的世界之旅 康奈爾 (Alexis Cornel)
用「哲學經濟家」形容季.索爾孟(Guy Sormon),再貼切不過。經濟學,也就是對物質繁榮起因的探討,原本包含在對人類政治和道德秩序的研究當中,後來的現代社會科學,才把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細分為越來越多的學術領域。拿亞當斯密(Adam Smith)這位著名的學者來說,他的研究範圍廣泛,當年稱為「政治經濟學」。在他的認知裡,他的研究跟哲學家對於人類與社會本質的思索並非各自獨立的研究領域。在很多方面,索爾孟算是老一代廣義的經濟學家。他自己曾說,對他影響最深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廣泛研究人類與社會的學者,例如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和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索爾孟寫作時使用的口吻,不像是個越來越專精的學術領域的專家,而像是個知識淵博的學者,以世界公民的眼光和關懷而審慎的態度,檢視我們這個世界的各種狀態。
索爾孟關懷世人,因為做為經濟學者,他瞭解人類生存的滿足感是以物質為基礎,而且他深信讓人民在法治的環境下享有經濟自由,是讓越來越多世人長期享受繁榮生活的唯一途徑。說他態度審慎,是因為他從不低估會影響追求經濟繁榮的非經濟因素。他充分體認不能把人類福祉簡化成為經濟的發展程度,而且清楚經濟發展受到文化和政治因素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他說:「世界或許在全球化,但有些地方仍停留在當地的時間。」而且他不認為這個「當地時間」未來必然會變得無關緊要。不過,索爾孟在檢視世局並提出建言時,核心焦點仍在於經濟自由對於人類利益與盼望的重要性,以及經濟自由實質與潛在的龐大價值。
索爾孟在對世局進行務實的研究時飽讀各種書籍和文章,但最大的特點在於他直接的觀察,以及與世界各地接觸對象對話而來的心得。他好像一直在旅行,但從來不是個普通的觀光客。他顯然有一種天賦,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重要的思想家和重要人物,並贏得他們的信任,甚至尊敬。透過索爾孟的文章,讀者可以看到他與世界各地重要概念的發想者和執行者之間引人入勝的對話。無論是在開羅或紐約與商人或示威者在一起,或者是在馬德里與聞政府高層會議,或者在北京與異議人士討論,索爾孟始終非常清楚人類進展的具體條件,以及人類虛榮心與狡詐所造成的難以克服的障礙。
索爾孟明顯支持市場機制(歐洲稱為「自由派」),但他的判斷和評論都十分持平中肯。有時從他的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公允的立場,例如他可能根本不同意某些作者的論點,但願意肯定這些作者的一些觀察。有時候,索爾孟會用稍微不同的角度,回頭去討論他自己先前提出的觀點。比方說,他一度對歐元區的前途深表關切,但後來他對於歐元區將會瓦解的預測表達不同意見:他說,歐洲整合的過程太過重要,「拯救歐元和歐洲的代價會有人承擔」。另一個例子是,索爾孟以同情的角度解讀1968年5月發生在巴黎的抗議浪潮,讓我有些意外。那一年的活躍分子以放蕩大膽和不切實際的幻想著稱,跟索爾孟的務實大相逕庭,但他能體會這些人對於法國社會專制結構的挫折感。同樣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跟索爾孟的觀點與理性大不相同,但他可以退一步,把「占領華爾街」視為主要靠新社交媒體推動的廣泛抗議運動的一部分,進而探討它的意義。索爾孟認為甘地對人間的邪惡極度天真,「有時近乎荒誕」,但他不會吝於給予甘地肯定。他認為,甘地是「20世紀唯一手上未沾染鮮血的主要政治領袖」。
法國知識分子在評論美國的時候,往往很難客觀持平,因此索爾孟在這個議題上平穩而細緻的觀點特別有價值。他很清楚美國的缺點,但他對歐洲人對美國的偏見─—以及跟著歐洲人一起看不起自己國家的美國人─—更不假以辭色。有一次他在洛杉磯接受一位右翼電台節目主持人訪問之後,以開玩笑的口吻談到美國和歐洲對政府角色的不同看法,並說自己被夾在中間。他說:「我在美國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在法國是個極端的自由主場提倡者。我想尋求政治庇護,但能去哪裡?」
他始終記得他的啟蒙者之一托克維爾給他的功課,因此他比誰都更明白,美國資本主義能有如此的活力、韌性和創新的能力,原因在於美國基本上是個公平的社會,以及大學和企業之間存在獨特的結盟關係。前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紐約被控性侵飯店服務生的新聞傳出之後,索爾孟沒有論斷史特勞斯卡恩,但他提醒法國人說,史特勞斯卡恩「不是被害人,他並未受到(美國司法制度和媒體)特別的迫害。此事充其量只是顯示美國的文明與法國大不相同」,因為法國人往往不瞭解,自己的許多觀點源自於貴族社會。另一個實例是:索爾孟跟歐洲其他人一樣,合理質疑華爾街主導金融界的情況,但他也樂意感謝美國第七艦隊為全球貿易提供安全保障,並做出這樣的結論:「美國資本主義是最糟的經濟制度,但也沒有一個制度比它更好。」最後,最能證明索爾孟具有深刻的文化同理心與無盡好奇心的事例,莫過於他在全美各地訪問時,都會上當地的教堂,因為「不上教堂,就等於決心不要瞭解美國的文明」。但索爾孟對美國百態的耐心,在莎拉.培林(Sarah Palin)出現之後面臨某種侷限。他形容她是「粗糙反歐的人士......揮之不去的大西部選美皇后」。他說,這位曾任阿拉斯加州州長的副總統候選人「身材玲瓏有致(至少他願意承認這一點),代表了某種美國夢」,但索爾孟最後向她所代表的美國夢投降:「想要瞭解也沒用,更不用說比較了。美國是獨一無二的。」
索爾孟對事情的評斷雖然往往很持平,但這不表示他不會做出堅定而清醒的道德批判。這樣的批判最常出現在他對於中國的諸多評論當中,而這些評論出自於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多年的個人觀察,還有跟中國重要人士的聯繫和往來。比方說,如果讀者想多瞭解最近流亡到美國的陳光誠,就可以在本書中找到許多背景。索爾孟直言稱中共領導人為「暴君」。有些知名的評論員和公眾人物喜歡為中國打壓異議的做法辯護,說它有古老的文化背景,對於這些假裝淵博之人,索爾孟是毫不留情。他在談論中國時說:「不是每件事都可以拿全球化來解套。當有個危機改變了一切,道德的盤算也可以改變。」在這裡就可以看出,在人類自由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索爾孟既是經濟科學家,也是道德哲學家。
如果要問索爾孟何以如此樂觀,答案似乎在於他知道人類生而渴望自由,而且不斷追求經濟的成長。舉個引發許多爭辯的例子來說,他相信穆斯林最終會選擇「政教徹底分離」,因此,穆斯林將獲得政教必須分離才可能實現的自由與繁榮。索爾孟非常注意人類生存的經濟層面,因此一般而言,他對於拿歷史和文化論點來為某些人基本生活無法改善辯護的做法不能苟同,但這不代表他漠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文化與歷史因素,或低估睿智領導和關鍵政治抉擇的重要性。「自由始終必須靠自由的人警覺和維護。」索爾孟的名言是:「經濟不會說謊。」但經濟本身並不涵括人類生存的全部。他始終沒有忘記,經濟學是一門以人類為對象、為人類而進行的科學研究,而他在提倡經濟自由時,始終保持著對全人類的同理心。他寫道:「資本主義的根本,在於它激發信心,並且提供具體的服務。它本身並無可愛之處。」因此他坦誠分享往往是左派人士會提倡的人道主義論點,但他也不斷警告世人不該抱持跟基本經濟現實背道而馳的幻想。「既想要社會主義福利,又要有自由的經濟,而且要過得幸福快樂,這就是天真的自由主義,也就是虛構的意識型態。」因此,他很明確地抱持反烏托邦的人道主義觀點:「經濟學常見的選擇,不在於選好或選壞,而是得在壞跟更壞之間做個選擇。」
除了資本主義可以提供的「具體服務」,索爾孟在熱心提倡經濟學時,經常觸及最能反映出西方文明精華的精神自由,也就是社會與經濟創新的根源:「西方國家如今已更清楚它們自己的矛盾,更能尊重它們當中的多元現象。但缺了自我反省的獨特能力,西方文明還有什麼價值?」個人認為,這就是索爾孟樂觀的源頭:他深信人類有能力超越嚴重的偏見和意識型態的幻想,能逐步而有效地學習。他寫道:「市場經濟明顯並不完美,而且只能帶來相對的物質進步。這種細微的變化,永遠無法滿足追求完美的人。但預告末日將會來臨的人最終總是落空;資本主義經歷一個又一個危機,但總是能夠回彈,而經濟學家在不斷地學習新的功課。」
在讀完《金融海嘯之後——一個樂觀者的日記》之後,我發現自己變得更為樂觀。建議各位也細讀本書。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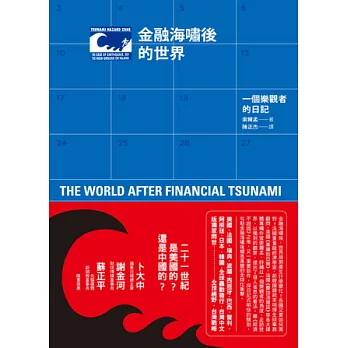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