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既近又遠的原鄉──我讀《幽黯國度》 王瑞香
台灣第一次將文學目光投向加勒比海區域,應是一九九二年瓦科特(Derek Walcott,出生於聖露西亞的詩人暨劇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設若當時(甚或更早)得獎的不是瓦科特,而是奈波爾(長年來奈波爾屢屢被認為有望得到諾貝爾獎),那麼台灣必定早已有許多奈波爾的中譯作品問世;因為奈波爾的著作量豐碩,品質也都在水準之上。有人認為,若非奈波爾在作品中透露對第三世界那樣無情的嘲諷與鄙夷,諾貝爾文學獎很可能早就落在他身上。不過話說回來,奈波爾的憤世嫉俗和譏諷挖苦畢竟是他的真情流露;因此,這樣一位作家的頭頂若加上諾貝爾獎光環,反而會有點不搭調吧。
奈波爾於一九三二年出生於千里達,祖父於一八八○年代以契約勞工的身分來到這個英屬殖民地,從此在那裡定居;父親是一家報社的記者,並從事少許的創作。奈波爾的家族到他這一代共出了四位作家,他是當中最傑出的一個。奈波爾於一九五○年前往牛津大學就讀,一九五四年開始寫作,未幾即嶄露頭角,幾十年來在英語世界文壇上的地位屹立不搖。
奈波爾的早期寫作生涯以經營小說(先短篇,而後長篇)為主,八○年代之後則主要投注於旅遊寫作,至今他共出版了二十二本書,其中小說和遊記約各占半(各為十本與八本),兩者所受的評價均極高。儘管一再與諾貝爾獎緣慳,奈波爾卻榮獲不少其他文學獎項,包括英國最富聲望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以及英國獎金最高的大衛.柯衡英國文學獎(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此外還於一九九○年受英國女王冊封為爵士。無論是小說還是遊記,奈波爾的作品往往將讀者帶到第三世界的最遠處,而他對第三世界的描寫向來是不留情面的冷嘲熱諷兼帶深沉的無奈,這頗迎合歐美知識分子的胃口,但卻相當地激怒了第三世界的讀者,甚至引起廣泛的爭議,就這一點而言,《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一書所導致的情況最為激烈,以《東方主義》一書馳名世界的學者薩依德(Edward Said)即對奈波爾做了嚴厲的批判。但即使是薩依德這樣的「敵人」亦不能不折服奈波爾在寫作上的功力。事實上,奈波爾雖然在文學上享有至高的聲譽,他孤傲尖酸的個性卻為他樹敵無數,有些記者即不掩其對奈波爾傲慢態度的厭惡;甚至奈波爾過去亦師亦友的著名旅遊作家索魯(Paul Theroux)也與他反目。不管討不討人喜歡,奈波爾這個特點為他造就了寫作上的正字標記,不過在八○年代末期以來他的作品逐漸出現了較為溫和的色調,這為他贏得了另一種讚賞的聲音。
雖然到牛津求學後即以英國為主要居住地,奈波爾的心靈卻一直漂泊無所寄託,甚至軀殼也長年來游移於英國、千里達、印度、非洲、美國之間。所有這些旅行經驗都化作文字,他也成為當今世界上旅遊文學的翹楚。除了遊記報導之外,這些異地經驗也提供奈波爾豐富的小說素材。他的小說多半在探討第三世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逆境,以及個人的流亡經驗,內容亦虛亦實,有時帶有自傳色彩,不論在技巧或見解上都極具有可讀性,其中以《畢斯華士先生的屋子》(A House for Mr. Biswas, 1961)、《模仿人》(The Mimic Men, 1967)、《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享譽最高。在他的遊記報導中,有關印度的作品無疑是最具個人意義也最值得重視的。在這方面奈波爾共有三本著作,這本《幽黯國度》是其中的第一本。
奈波爾最早的作品是以千里達為背景的小說,雖然獲得好評,但由於意識到這樣的作品有局限性,他於一九六○年開始旅行,刻意博得更多的讀者,擴大他的文學版圖。一九六二年,他首次踏上印度土地,探訪他祖父輩的家園。這時他才三十歲,卻已有豐富的寫作經驗,共出版了四本頗受肯定的關於千里達的小說,及一本記述他首度返回加勒比海區域的遊記報導。他為期一年的印度之旅從在孟買上岸開始,先到德里,然後在喀什米爾住了四個月,接著短訪西姆拉,往南到馬德拉斯,再到加爾各答,最後造訪他外祖父的家園。
加勒比海區域的居民都不是當地的「原住民」,而對被迫以奴隸或契約勞工移入的三大族群的後代(非洲裔、印度裔、華裔),重訪或重返原鄉的企望很自然成為重大的心願。比較而言,非洲裔的尋根之旅充滿回歸的喜悅,華裔很少在這方面訴諸筆墨,而印度裔對原鄉的態度則頗為曖昧。奈波爾面對印度時,除了曖昧之外,更帶著深重的失望。
在本書中他呈現各種令人不安的印度亂象,並對大英帝國做犀利的批判,讀者可以見識到奈波爾作品所慣有的尖酸刻薄與陰沉的無奈,及其令人佩服的寫作技巧。一開始的序曲即把印度的兩大問題點明了:令人窒息的官僚體系與令人沮喪的種姓制度。奈波爾為了索回在海關被沒收的兩瓶洋酒,來回奔波辦理那繁瑣得任誰都會發火的手續,女伴大約中暑,一時昏倒在衙門裡。奈波爾向機關職員大呼要水,卻毫無動靜,只換來幾聲輕笑。又叫,仍無人理睬。最後一個雜役慎重其事端了杯水過來,奈波爾才恍然大悟,「職員是職員,雜役是雜役,各司其職,不相混淆。」在印度傳統中,越是屬於勞力的工作越下賤。因此,一個速記員在上司(國外回來的)的逼迫下終於打出一封他速記的信時竟然哭了。他覺得很受辱,因為他是速記員,不是打字員。
官僚體制的瑣碎與荒謬有時令人不解。奈波爾曾發現一位「表格與文具視察員」,他的工作是機密的,就是到各個火車站「摸清屬下每一位站長的底細」,以查核其表格與文具申請單。他給奈波爾看一份某個站長的申請單,所申請的一百本便條紙被這位視察員刪除到剩兩份,他解釋,這位站長有六個孩子,這些便條紙有九十八份是要給他孩子用的。
成長於殖民地的奈波爾所關注的重點之一,很自然地,是印度後殖民情境的種種相貌。不論是對印度本身的罪惡,或英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他的批評都不假辭色。他譏刺地說,全世界各色人種之中,印度人最具模仿天賦,但印度人模仿的並不是真正的英國,而是由俱樂部、歐洲大爺、印度馬伕和傭人組成的「盎格魯印度人」。而這些假英國人是那個玩夠了,感到無趣就拍拍屁股走人的騙子──英國──留下的。在他後來的一部小說《模仿人》裡,奈波爾對這種「假英國人」和大英帝國的禍害做了盡情的發揮。
身在印度,奈波爾始終有疏離感,總覺自己是個異鄉人、是個過客。他只能安於他想像中那個從「外祖母的屋子延伸出來的土地,跟周遭的異文化完全隔絕開來」的印度。儘管這趟旅程他並無歸鄉之感,並試圖以客觀的眼光去看印度,但他仍不可自己地感受到震驚、厭惡、絕望、憤怒、羞恥等種種情緒。印度舉國上下到處大解,人人對排泄物視若無睹,垃圾、人、牲畜、食物等堆在一起、司空見慣的孱弱小孩、一座座貧民窟……等令人怵目驚心的現象,令奈波爾招架不住。不過,在一段時間後他便找到了逃避的竅門。但對於他的認同他便無法輕易妥協了。
其實,在探訪印度的同時,奈波爾也在進行一個內心之旅:透過他的書他企圖探索自己歷史的各個面向。例如他的身分認同。他嘗試懷著觀光客的心態走訪印度,卻又對真正的遊客看不順眼。例如,看到年輕貌美的美國女子樂琳,他發議論:「這種美國人男女都有。他們雲遊四海,混吃混喝。」看到美國老太太施捨零錢給學童,他心裡起了無名火,一怒便將學童都嚇跑了。這樣的語帶譏刺、嫌厭與不屑正反映了他在認同上的掙扎。置身印度,奈波爾不止一次咀嚼童年時被一位同學(也是印度人)認出是「真正的婆羅門」的欣悅感覺,流露了他的階級優越感。或許他在火車上結識的錫克人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在本書中我們幾乎聽不見印度人的聲音(要到《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我們才能在他的文字裡聽見印度人的聲音),發聲最多的就是這位「對膚色存有偏見」而又尖酸刻薄、卻深深吸引奈波爾的錫克人。在此,奈波爾運用小說手法,藉著這名錫克人道出了自己對印度人的惡感和輕蔑。
他對印度真是吝嗇,即使在看到美好的事物想要讚美時,也要先挖苦一番。看到一位相當順眼的男子,他寫道:「髒亂、腐朽、視人命如草芥的印度,竟也能產生出那麼多相貌堂堂、溫文儒雅的人物。」一直到最後描寫到他外祖父的家鄉時,他的筆才溫柔起來,流露些許的情感。不過,等見到鄉親,看到他們對他有所求時,他卻又立即收起他的溫情,板起臉來,顯得被動、冷漠而寡情,甚至連一個小孩梳洗乾淨了想搭他一段便車,他都毫不思索地拒絕了。
奈波爾對印度會有這樣的反應,是因為他在心態上是個典型的「殖民地子民知識分子」,對自己所出身的殖民地、自己淵源所在的第三世界缺乏愛心與信心所致。
在這次的印度之旅之後,奈波爾每每在印度的召喚下回到它的懷抱,而於一九七七年出版《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記述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間甘地夫人治下的印度,筆調仍和前一部一樣充滿憤怒、震驚、疏離與失落之情。《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是他的第三部印度遊記,在這部優美的記述裡,奈波爾陳述印度驚人的改變,以及他對印度較樂觀而同情的看法,此時的奈波爾成了一個溫和、熱情、寬諒的旅遊記述者,令人不禁覺得,這個漂泊者雖未必找到了他心靈的故鄉,卻至少收斂了他慣有的對第三世界的無情嘲諷與陰沉的不屑,而成為一顆較成熟、晶瑩的靈魂。這三本書都是一個旅遊者所寫的書,但不是寫給觀光客看的;而不管你喜不喜歡裡面所呈現的印度或奈波爾,你都必須承認它們是了解印度不可或缺的書。
身為旅遊作家,奈波爾從加勒比海區出發,在《幽黯國度》裡我們看到他到了先祖的印度,爾後他將走訪非洲、中東、非阿拉伯的回教國度(南亞、東南亞)、美國南部等地,並根據這些經歷寫出一部部擲地有聲且廣泛引起爭議的遊記,在旅遊報導上樹立了獨特而重要的典範。
在各方面似乎都離我們很遙遠的加勒比海區在文學上值得我們探究。雖然存在那裡的是一些蕞爾小國,沒有久遠的歷史或顯赫的國際地位,它在文學上卻不乏世界級人物。除了奈波爾與瓦科特之外,值得注意的尚有以英語寫作的藍明(George Lamming)、芮思(Jean Rhys),西班牙文方面則首先令人想到古巴的「國父」荷西.馬蒂(Jose Marti)。奈波爾是我們認識加勒比海文學一個很好的開始,而《幽黯國度》是我們見識其遊記作品魅力的最佳起點。
(王瑞香:文化工作者,著有《一個女人的感觸》)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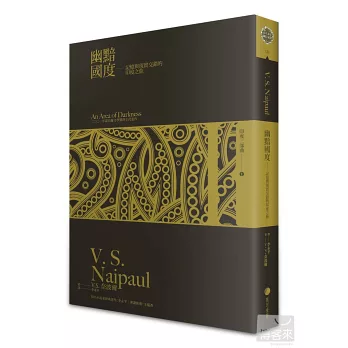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