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道盡頭,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坐在寬敞、兩面有大窗的角落辦公室裡,他坐的位置,剛好可以俯看世界銀行。六十四歲的艾克曼是精品投資公司──岩港資本有限公司(Rockport Capital Incorporated)的總經理。一個晴朗的八月下午,他用Powerpoint向我作簡報,大談「風險收益」。然而他所顯示的圖表,跟投資、紅利與財經都沒有關係,他所談的是推翻獨裁者的最佳方法。
二十五年前的艾克曼不像個諮詢專家,會忠告別人如何對付世界最殘暴的政權。當年的他忙著在華爾街賺大錢,還是垃圾債券大王麥可‧米爾肯(Micahel Milken)的得力助手。一九八八年,艾克曼負責幫忙槓桿收購雷諾納貝斯克公司,成交值為兩百五十億美金,他自己賺了一億六千五百萬的佣金。米爾肯後來因為內線交易坐牢,艾克曼則繳了八千萬美金的罰金免除牢獄之災,得以保留五億美金的資產。
現在,他大部分的資產都流入各種管道,專事推翻全球專制政權。二○○二年,艾克曼創立了「非暴力衝突國際中心」,籌辦研討會、工作坊、訓練課程,主題是如何用非暴力策略與技巧成功地推翻暴政。埃及、伊朗、俄國、委內瑞拉、辛巴威以及其他十幾個國家的運動人士都跟艾克曼都很熟,某些人甚至遠道前來,拜訪他在華府霧谷區(Foggy Bottom)的頂樓辦公室。另外一些人則參加他在海外數個國家首府設立的工作坊。
還有一些人看過他拍的影片,最多人看的一部叫作《推翻獨裁者》(Bringing Down a Dictator),內容是塞爾維亞青年在二○○○年十月讓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下台的故事,這部影片曾經獲得美國公共電視台最佳電視紀錄片之皮巴底獎(Peabody Award),還被翻譯成阿拉伯語、波斯語、北京話、越南話與其他七種語言。
喬治亞人普遍認為它對喬治亞二○○三年所發生的「玫瑰革命」很有啟發:喬治亞人在該次和平的民主反抗之中,成功地迫使共產黨總統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辭職下台。二○○六年,艾克曼開始投入電玩市場:開發電腦遊戲《一種更強大的力量》(A Force More Powerful),讓反對人士可以在虛擬世界裡練習各種推翻獨裁者策略。
他還想辦法將數千份光碟偷偷送進世界上最專制的國家裡。二○一○年他又推出該遊戲的升級版,稱之為《人民力量》(People Power)。他說:「我花了數百萬美元改良這個遊戲,這是我做過最具顛覆性的事。」我問他為什麼把打倒暴君當作一生的志業,他看著我說:「我做的只是物流業,只是滿足客戶的需求,如此而已。」他其實還可以再加一句,生意好得很。
今日,要當一個獨裁者並不容易。沒多久以前,獨裁者──不論是民族主義軍頭、革命英雄或共產黨黨棍──往往會利用武力鎮壓,讓人民不敢輕舉妄動。史達林把千萬人送進古拉格。毛澤東則針對知識分子、走資派、以及任何在他心目中不夠「紅」的人,發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
之後他還發起大躍進,在短短幾年之內就餓死三千五百萬人。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敏的政權殺死了五十萬人。在三年之中,大約兩百萬柬埔寨人死於波布的殺戳戰場。一九八二年二月,敘利亞的哈菲茲‧阿薩德(Hofez Assad)鎮壓了哈馬市(Hama)的市民起義,他以攻擊直昇機以及重砲武器包圍該城市,而他的軍隊進城後,即挨家挨戶入侵民宅,到了二月結束之前,已造成兩萬五千名敘利亞人死亡。
獨裁者仍然有犯下滔天大罪的能力。然而,今日的暴君比起過去遇到更多抵抗的力量。冷戰結束以後,許多獨裁者失去了主要的支持者及金主蘇聯。一夜之間,民運組織遍地開花,另有西方的專業人士、人權運動人士以及選舉觀察者蓄勢待發,準備揭發違背人權、貪汙腐化、選舉舞弊等情事。二十年前,當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時,北京的領導人只須注意廣場上是否出現攝影鏡頭的反光,在宣布戒嚴以後立刻把CNN的插頭拔掉,讓畫面播不出去即可。這樣的好事已經沒有了。二○○六年,一群歐洲的登山客在喜馬拉雅山區高達一萬九千英呎的山隘口,拍攝了中國軍人射殺圖伯特僧人、女子、小孩的影片,它很快就出現在YouTube上面,國際人權團體立即對中國射殺難民做出譴責。
二○一一年,敘利亞禁止所有外國記者報導國內反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ssad,即哈菲茲‧阿薩德之子)政府的人民起義事件。沒關係,當政府的狙擊手射殺和平示威者、送葬行列成為槍擊對象時,敘利亞異議人士也在網路上張貼政府殘暴鎮壓的驚悚畫面。今日,全球的獨裁者不能再夢想他們的惡行永遠不為人知,只要他們下令鎮壓──即使是遠在喜馬拉雅的高山隘口──都有可能被iPhone拍下來,立即傳播到世界各地去。專制獨裁的代價沒有比現在更為高昂了。
其實早在網路、推特流行,甚至蘇聯解體之前,獨裁者的運氣就開始走下坡了。他們的苦難是一九七四年在葡萄牙開始的。更精確地說,是四月二十五日中午十二點二十五分,里斯本一家廣播電台播放了〈黑色小鎮格蘭多拉〉(Grandola, Vila Morena),向葡萄牙軍隊打暗號,示意政變開始。第二天,葡萄牙的獨裁者馬爾塞洛‧卡丹奴(Marcello Caetano)就被放逐了。根據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教授的看法,那一天所釋放出來的政治力量,就是全球民主浪潮的濫殤,接下來的數十年間,威權政體紛紛倒台。
緊接著葡萄牙之後,南歐一連串右翼的獨裁者開始垮台。接下來,輪到拉丁美洲的軍頭以及東亞威權統治者,每一個都讓外界感到驚異,然而一九八九年東歐共黨國家的垮台,更使人跌破眼鏡。一九七四年,全世界只有四十一個民主國家,到了一九九一年蘇聯也倒台的時候,民主的政府的數量已經躍升到七十六了。
而那只是民主蓬勃年代的第一章而已。非洲很快就出現了十來個新民主國家。印尼與墨西哥等主要國家也發生了重大的民主轉型。一九九八年,美國在全世界超過一百個國家設立了促進民主轉型的機構。二○○○年塞爾維亞發生革命,讓民主國家的欄位裡又多出一個新成員。二○○三年喬治亞、二○○四年烏克蘭、二○○五年吉爾吉斯等國所發生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s),象徵了自由對抗獨裁的高潮。到了二○○五年,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總數,比起葡萄牙的年輕軍官聽到廣播電台播放那首號召起義的歌曲時,已經增長了三倍以上。
然而好景不常。民主浪潮達到最高峰之後,世界上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政權──獨裁者、暴君以及專制政府等等──也不甘示弱捲土重來了。根據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接下來的五年,世界各地的政治自由開始一蹶不振。自由之家創立四十年來專門評估自由趨勢,他們認為這五年乃是政治權利以及公民自由最長的連續低迷期。
亞洲多國發生軍事政變,民主政府被推翻,另一方面,民粹的威權體制在南美洲站穩了腳跟。即使是新取得成功的喬治亞、烏克蘭以及吉爾吉斯,原來的成就似乎也土崩瓦解。到了二○一○年,民主國家的數量降到一九九五年以來的最低點。若以較長遠的眼光來看,被標識為「自由」的國家,其比例已經十多年都保持不變,固定在百分之四十六。杭廷頓的民主浪潮似乎已經壽終正寢。
問題不在民主本身。如同阿拉伯之春於二○一一年提醒眾人,即使全球面臨經濟不景氣,政治以及經濟自由的理想還是不失其重要性。各地方的人依然憧憬自由。改變的,是獨裁的「性質」。今日的獨裁者以及威權統治者,已經比從前精明老練靈活太多了。壓力漸大的時候,最聰明的獨裁者不再把自己的國家變成警察國家,也不再鎖國了;相反地,他們學習而且適應新情勢。民主的進逼迫使數十個專制政府不得不從事新實驗、使用有創意及狡詐的伎倆。現代的獨裁者練就了繼續掌權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獨裁制度帶入新世紀。
今日的獨裁者知道,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較為殘暴的威嚇方式──大規模逮捕、行刑隊、血腥鎮壓──最好以較柔性的強迫方式取代。今日最有效率的獨夫不再強行逮捕人權團體成員,而是派出稅吏或者衛生局官員讓反對團體關門大吉。政府把法律寫得很寬鬆,但遇上它們視為有威脅性的團體時,運用起來卻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委內瑞拉的一個異議分子開玩笑說,烏戈‧查維茲(Hugo Chavez)總統的座右銘是:「我的朋友,榮華富貴;我的敵人,法律伺候。」)今日的獨裁者不再關閉所有的媒體,而是保留一些小型的言路──通常是報紙──民眾雖有討論空間,卻是有局限的。
今日的獨裁者在演講時,三不五時提起自由、正義以及法治,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常常講到民主,還自稱是人民所選出來的領袖。這些人已經了解作表面功夫的重要性。二十世紀的時候,極權國家的領導人常常舉行選舉,然後聲稱自己高票當選。蘇俄的領導人總是宣稱他們獲得百分之九十九選票支持,這當然十分荒謬,事實上他們是以舞弊的方式贏得選舉。今日,克里姆林宮派出的選務人員作法不同,票箱達到七成滿的時候,他們就不再往裡面塞選票了。獨裁者已經了解到,最好是贏得一場表面上看起來有競爭的選舉,而非公然舞弊。
我們總是以為獨裁政權好似恐龍──笨拙、愚蠢、動作遲緩的大怪物,彷彿蘇聯的末期,或者某個充滿不安全感的南美香蕉共和國。當然,一些老派而落伍的獨裁者確實步履蹣跚地來到了二十一世紀,如北朝鮮、土庫曼以及赤道幾內亞。然而他們所代表的是獨裁者的過去,他們並不想掩飾自己的真面目。在其他國家學著進化、改變甚至繁榮的時候,這些老派獨裁國家落得偏遠而落後的下場。沒有人想成為下一個北朝鮮。
結果證明,極權主義只是二十世紀的一個現象。它是有史以來最充滿野心的非民主賭局,而且表現極差。目前只有北朝鮮還可能緊抱著極權主義不放,這是因為它持續發展核武,還有金正日願意讓自己的人民餓肚子。現代的獨裁者往往利用民主制度與威權政體之間的模糊空間,會想辦法讓人民滿足,贏得人民的支持。假如沒辦法讓人人高興,他們也可以透過恐嚇以及特定的威攝方法,讓異議人士無所適從。委內瑞拉的異議分子帕提達斯(Alvaro Partidas)告訴我:「我的父親老是說他寧可住在古巴那樣的獨裁國家,批評政府的話,他們就把你關在牢裡。現在他們透過不確定的感覺來控制人民。」
遠遠看上去,世界上許多威權國家看起來好似民主國家,其憲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等權力分立,但還是跟民主國家有重大差異:某些國家只有一個立法機構,而非雙層的上下議院制度,某些職位並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指派,而權力監督的程度也有異。然而這些威權國家的許多機構,其特徵──至少在紙上──看起來與最稀鬆平常的歐洲民主國家非常類似。
拿俄羅斯為例。縱然普丁愈來愈像一個獨夫,他卻一直尊重俄國憲法;他的方法是遊走於俄羅斯政治系統的縫隙,透過一些表面看起來民主的管道進行中央集權。克里姆林宮要求國會選舉必須有最低得票率門檻(每個政黨必須至少獲得百分之七的選票),批評者抱怨這阻礙反對黨候選人進入國會,乃是違反民主的犬儒伎倆。它的確是。然而普丁指出一些正牌的民主國家,如波蘭、德國以及捷克共和國,也有類似的選舉制度。再比方說,查維茲總統提出,委內瑞拉各地的省長不再經由直選產生,而是由總統來指定區域的領導人。
這又是另一個集中政治權力並且消除政敵的明顯伎倆。然而世界上一些民主國家也實行這種制度,例如波羅地海的愛沙尼亞以及立陶宛。重點是,這些措施本身單獨而論並非權力的濫用。現代威權政體的許多特色,單獨看起來與健全民主國家的制度似乎相差無幾,但只要改變其中某個環節,就可以創造很大的模糊空間。畢竟連美國民主的某些面向──例如選舉人團與聯邦準備理事會──都是不民主的。所以你必須仔細觀察威權政體的實際運作,還必須要直接接觸生活在其中的人。
少有人比八十四歲的阿列西娃(Ludmilla Alexeeva)更清楚獨裁政權已經鳳凰蛻變了。她是最後幾位資深的人權鬥士,他們早從一九六○年代末期的布里茲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時代就開始反抗莫斯科。即使到現在,雖然年老體弱、必須靠人扶持才能走遠路,她仍然帶頭反抗,希望幫俄國人民爭取到集會自由。那天早上,我坐在她莫斯科的公寓裡,電話響個不停。她笑著說:「現代人對人權鬥士的需求很高,我們在本國很受歡迎。」她當年開始參與反抗運動的時候風險非常大,蘇聯的異議人士必須「準備犠牲生命,不然就是坐牢或者被關在精神病院」。「今天的話,他大概會被斷手斷腳或者謀殺。」過去政府的作法是直接抓人,之後就下落不明。今日的話,此人往往會發生車禍,或者在意外的攻擊事件之中受傷。
蘇聯過去沒有明文保障公民權利,今日的俄羅斯已非如此。阿列西娃說:「俄羅斯的憲法跟任何西方國家的憲法一樣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然而實際上,真正被尊重的只有一種權利──旅行到國外的自由,離開的自由。」許多本來可能反對政府的人乾脆就離開了。在以前的蘇聯獨裁模式下,邊界要嚴密封鎖,現在的普丁俄羅斯威權系統卻開放邊界以及放寬護照條件,以此維持政權之不墜。世界也許已經改變了,然而爐火純青的獨裁者並沒有坐以待斃。世界一改變,舊規則一旦不適用,最有技巧的統治者也會跟著學習,變得更厲害了。
獨裁制度之最高不可侵犯之原則,就是中央集權。以少數統治多數的這項原則,讓今日的威權政體越來越顯得格格不入,彷彿時代倒錯,因為在現代生活的每個層面,階級正在瓦解消弭。獨裁政體的中心守則,也顯得愈來愈過時。因此,在一個資訊爆炸以及邊界洞開的世界裡,要維繫威權政體於不墜,必須小心經營、反覆規劃並強化的各種人為計畫。對那些最惡名昭彰的國家來說,事情比較不複雜,他們只要築起高牆,把世界隔離在外,也許可以維繫政權幾年、甚或幾十年而不墜,然而他們也被自己築起的高牆關在裡面。
比較複雜的是現代獨裁者,他們選擇與世界互動,而且願意面對龐大的壓力,而過去的獨裁者可能會選擇自我封閉。他們努力將法規跟迫害混在一起,不但從全球的政治系統中獲得好處,又不危及自己掌控權力。現代的威權政體有精心設計的結構,需要經常地修整與維護。其原因不只是抽象的現代化要求,而是因為獨裁者越來越靈活,另一方面,想要把他們推翻的人也一樣愈來愈聰明了。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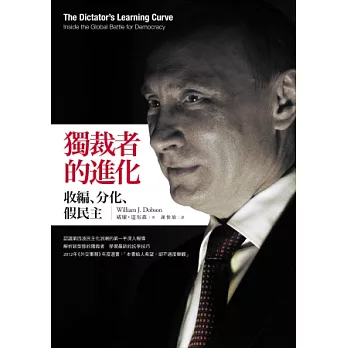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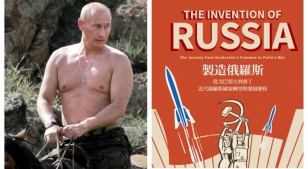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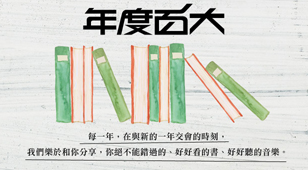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