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香港文學未有一本從本地觀點與角度撰寫的文學史,是説膩了的老話,也是一個事實。早期出現多種境外出版的香港文學史,疏誤實在太多,香港學界乃有先整理組織有關香港文學的資料,然後再為香港文學修史的想法。由於上世紀三〇年代面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被認為是後來「新文學史」書寫的重要依據,於是主張編纂香港文學大系的聲音,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不絕於耳。1這個構想在差不多三十年後,首度落實為十二卷的《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際此,有關「文學大系」如何牽動「文學史」的意義,值得我們回顧省思。
一、「文學大系」作為文體類型
在中國,以「大系」之名作書題,最早可能就是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出版,由趙家璧主編,蔡元培總序,胡適、魯迅、茅盾、朱自清、周作人、郁逹夫等任各集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系」這個書業用語源自日本,指有系統地把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匯聚成編以為概覽的出版物:「大」指此一出版物之規模;「系」指其間的組織聯繫。2趙家璧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五十年後的回憶文章,就提到他以「大系」為題是師法日本;他以為這兩個字:
既表示選稿範圍、出版規糢、動員人力之「大」,而整套書的內容規劃,又是一個有「系統」的整體,是按一個具體的編輯意圖有意識地進行組稿而完成的,與一般把許多單行本雜湊在一起的叢書文庫等有顯著的區別。3
《中國新文學大系》出版以後,在不同時空的華文疆域都有類似的製作,並依循着近似的結構方式組織各種文學創作、評論以至相關史料等文本,漸漸被體認為一種具有國家或地區文學史意義的文體類型、資料顯示,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繼作有: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三七—一九四九》(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
>《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七六—二〇〇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九)。
另外也有在香港出版的:
>《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一九二八—一九三八》(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六八)。
在臺灣則有: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一九五〇—一九七〇)(台北:巨人出版社,一九七二);
>《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台北:天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臺灣一九七〇—一九八九》(台北:九歌出版社,一九八九);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貳)——臺灣一九八九—二〇〇三》(台北:九歌出版社,二〇〇三)。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地區有:
>《馬華新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新加坡:世界書局/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七〇—一九七二);
>《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一九四五—一九七六)(新加坡:世界書局,一九七九—一九八三);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六五)(新加坡:教育出版社,一九七一);
>《馬華文學大系》(一九六五—一九九六)(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
內地還陸續支持出版過:
>《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一九四五—一九七六)(北京:華藝出版社,一九九九);
>《新加坡當代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一九九一—二〇〇一);
>《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廈門:鷺江出版社,一九九五);
>《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大系》(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一九九三)等。
其他以「大系」名目出版的各種主題的文學叢書,形形色色還有許多,當中編輯宗旨及結構模式不少已經偏離《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傳統,於此不必細論。
陳國球(節錄)
導言
一
在所謂的新文學四大文類中,散文的身份向來曖昧。新詩、小説、戲劇都算是「純文學」,散文卻因為「不純」而有點遜色,像朱自清《背影‧序》所抱歉的:「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説,便只好隨便一點説着」。1幸而他後來大大擴展了文學的界域,不但兼包美文、小品,連帶雜文、通訊、特寫等,也都可以帶有「文學意味」,要不然本卷的選擇範圍就極為有限了。2
這種朱自清命名為「文學報章化」的現象,並非指作者或作品向「純文學」的本質靠近,而是研究者追蹤着不斷冒現的新作品,努力論證它們具備新的文學品質——既説這些作品和以前的不一樣,卻又肯定兩者同是文學,未免有些弔詭。朱自清借用胡適「至大無外」的文學定義:「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又稍稍改易胡氏用來解釋「妙」和「好」的「明白」、「動人」,以求新舊品質表面殊異而內裏相通,其苦心可以理解。但「報章化」的文學一定「明白」、「動人」嗎?如果「報章化」的文學比以往的文學更「明白」、「動人」,原因在哪裏呢?
「文學報章化」最基本的意思,是報紙成為文學作品主要的發表場所,這一媒體或載體的特性主導了作品的特性,以至並非在報紙上刊登的作品也多少受到影響。在香港的散文寫作上——最少在本卷的時限裏——,報紙副刊正擔當這種角色。因此要了解香港散文有沒有、有哪些特點,也不妨從媒體、載體入手。自然副刊不是孤立的,它從屬於報紙,報紙又連結在更大的商業、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中,而在這些關係網絡上活動的是人。所以媒體結構即或決定了基本的性質,個人意志有時也能闖出新路。
樊善標 (節錄)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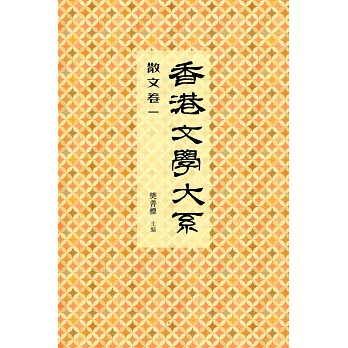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