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們三代人》斷斷續續地寫了三年,現在總算完成了。如果問我,對這本書滿意不滿意,我會坦白地說:我不太滿意,沒有把我所想寫的都寫出來。但現在也只能如此了,因為手頭還有其他幾件事要做,再抽不出時間補充、加工,對此只能抱憾了。
這本書對我祖父湯霖寫得很少,我手頭沒有多少他的材料,如果我有時間回湖北黃梅家鄉和到他任知縣的甘肅渭源、碾伯等地作點調查,也許會得到更多的材料。對我父親湯用彤,我也沒有全面地寫他的為學為人,因為關於他的傳記已經有好幾本了,寫他為學為人的文章至少也有上百篇了吧!因此,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他的生平事跡等等也就不需要我多用筆墨了。
我寫這本《我們三代人》只是想通過一些具體的事,寫出我們這三代不過是眾多的「詩書之家」中的一家,而且我們這一「詩書之家」到我之後就不能再繼續了。雖頗有些感慨,但也無可奈何,時代不同了嘛!
我祖父雖是一位能淡泊名利者,但也希望能「立功立言」;雖是一位清朝的進士,但卻也對「新學」有所留意;雖是一位身在衰世的知縣,但卻有憂國憂民之心。我認為,也許我祖父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是把我父親送入新式學堂,特別是讓父親進入了清華學校的留美預備班和他對我父親的「國學知識」的傳授。因此,我父親得有良好的「國學」基礎,又能對西方文化有深切的掌握,致使他在學術上取得公認的成就。當然,祖父的「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等為人處事的榜樣,對我父親也有著深深的影響。十分可惜,我沒有能更多地了解我的祖父,這無疑是我一生的遺憾。
現在學術界都認為我父親是「中國佛教史」、「魏晉玄學」方面的權威學者,是當代的一位「國學大師」,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太炎先生以後,幾位國學大師,比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等,都是既能鎔鑄今古,又能會通中西的。……我認為,湯用彤(錫予)先生就屬於這一些國學大師之列。這實際上是國內外學者之公言,決非我一個人之私言。在錫予先生身上,鎔鑄今古、會通中西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正因為我父親能「鎔鑄古今,會通中西」,他的著作才能成為傳世之作。從表面上看,我父親對現實中的問題並不注意,是一位「為學術而學術」的專家。但如果我們透過他的學術研究就會深深地感到他對中國文化有著一種存亡繼絕的使命感,這點正如賀麟先生所說:「他(按:指用彤先生)根據他多年來對中國文化學術史的研究和觀察,對於中國哲學發展之繼續性(continuity)有了新穎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掃認中國哲學的道統在孟子以後,曾經有過長期失傳的偏狹的舊說。他認為中國哲學自來就一脈相傳沒有中斷。即在南北朝隋唐時代,當佛學最盛,儒學最衰時期,中國人並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來的文化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國人利用之,反應之,吸收之,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並促進中國哲學的新發展。他這種說法當然是基於對一般文化的持續性和保存性的認識。這種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於積極推行西化的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在當時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於促進我們對於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我父親早年留心於儒學,後於「中國佛教史」有深切之研究,而後又來研究以老莊思想為基礎的魏晉玄學,於1941年初的一次講演中,用彤先生說:「中國文化即儒學,若釋、道均非中心。」可見其所涉獵遍及儒、釋、道三家,而中國文化之正宗仍為儒家。就此,我們可知用彤先生對中國文化及其發展前景的看法,並可深切體會其對中國文化的特殊關懷。
我這本書中不是要全面介紹我父親,而是根據我所了解的其他學者少談到的方面,用紀實式的寫法,來寫我覺得應該向讀者介紹的方面。例如,在《湯用彤全集》中未收的用彤先生關於《印度佛教漢文資料選編》,我做了重點介紹。我讀了他的這份資料,深感他對印度佛教有其獨到的了解,特別是他抓住印度佛教發展的關鍵,這點不能不說他是借助了他的西方哲學的素養。對1949年後,我也只是用幾個典型的事件,來說明他的變化。但在這本書中,我特別介紹了用彤先生和當代學者的交往,我認為這方面的材料對於我們了解老一代學者的為人為學以及他們之間的友誼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應該受到重視。
至於我寫我自己,我也只是擇要的寫,其中有兩部分我認為也許會使讀者對我有所了解,這就是《我與中國文化書院》和《我的哲學之路》兩部分。現在我已七十多歲了,但我仍然夢想把中國文化書院辦成一所綜合性私立大學,也許這終究是個夢吧!但是我仍然會走「我的哲學之路」,很可能我會把「中國解釋學問題」繼續研究下去,或者寫一部《中國哲學問題論》。我仍然認為,我自己不能成為一名「大哲學家」,但我卻可以不斷提出一些哲學問題,這無疑對後來的人有其一定意義。
湯一介
2003年7月4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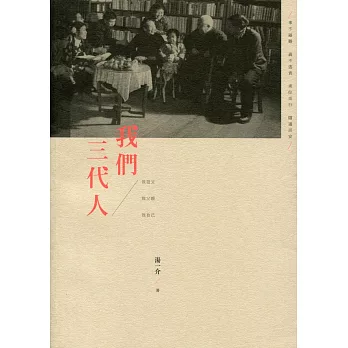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