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凱撒的還給凱撒
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1162-1227。名鐵木真,中國歷史上的元太祖),他所帶領的部族(clan)崛起,在時間上對人類歷史的發展帶來震撼;空間上對中原王朝、北亞、中亞乃至歐洲部分地區影響延續至今。身為中外歷史上的世界征服者(World Conqueror)之一,他是最受西方人所認識的「東方帝王」,更是文學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2015年初《國際財經時報》(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引述英國《自然》(Nature)期刊,提到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遺傳學家Mark Jobling的研究,指出成吉思汗的遺傳基因是亞洲影響最廣者,其「子孫」佔據亞洲男子的20%,全球男子的0.5%,此一論證是否攧撲不破或可不論,例如所謂的染色體Y中發現的11個獨特序列如何確認來自成吉思汗?真正的意義亦不在於是否能賦予成吉思汗「亞洲之父」的頭銜,而是昭示了這位蒙古世界帝國創建者的魅力,即使在學術圈,亦能吸引不同領域的研究者,而不拘於文史學界。如同作者文中曾提到據稱麥克阿瑟稱其為「全人類的皇帝」;波斯史家志費尼(al-Juwayni,1226-1283)於《世界征服者史》中描述:「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歷山大,在使計用策上當是成吉思汗的學生;攻城略池的妙策上,最好盲目地跟著成吉思汗走」;也引述拿破崙感嘆自己不如成吉思汗一般有四個虎子效力的好運。綜言之,成吉思汗可說是英雄界的標竿,其知名度與影響力自不待言,以至於關於他的學術研究、文學傳記與通俗戲劇、音樂、電影作品更是汗牛充棟。
本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考驗作者如何獨樹一格,帶領讀者再度認識成吉思汗。內容共分八章,首章先從孕育成吉思汗的外在環境出發,從地理、文化背景架構出當時部落林立的北亞草原,再論及草原內部與周邊政治體之間的關係。第二章則描述一代天驕的出生與成長過程所遭遇的苦難。第三章為統一草原各大部族的戰爭過程。第四章到第七章則涵蓋了蒙古國的正式建立;取得成吉思汗尊號;汗權與神權的結合;開始走出北亞草原;畏兀兒(Uihur)、哈剌魯(Karluks)的降附;征西夏;南下伐金;滅西遼;開啟西征;摧毀中亞大國花剌子模,最終於西夏投降之際病逝於清水縣(今甘肅天水)。其中關於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蹟,絕大部分立足於《蒙古秘史》、《史集》與《世界征服者史》等重要文獻,這些確實是迄今為止書寫成吉思汗最不可或缺的直接史料。在格式上,作者遵循基本的學術規範,力求史實,每章皆有完整註釋,筆法則企圖在通俗文學與專業論文之間取得平衡,可說是少見的立足於專業史料文獻之上的傳記文學。
成吉思汗作為研究與書寫的題材,不僅古老而且歷久不衰。廣義來說,中國的《元史.太祖本紀》可為濫觴,狹義則以十七世紀法國傳記作家克魯瓦(Petis dela Croix,1622-1695)利用了當時尚存、現今已佚的中亞多種語言文獻,撰成《古代蒙古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偉大成吉思汗史》,開啟近現代成吉思汗傳記的序幕。整體說來,成吉思汗的傳記數量之多,亞洲史上的帝王與名人皆無出其右,通俗性作品如蘭姆(Harold Lamb,1892-1962)的《人類帝王:成吉思汗傳》(Genghis Khan: The Emperor of All Men),書寫特色是生動活潑,引人入勝,但內容卻謬於歷史事實。在學術界影響最廣者,以俄國漢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B. Ya. Vladimirtsov,1884-1931)的《成吉思汗傳》(The Life of Chingis Khan)以及法國東方學家格魯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的《世界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World)。前者稱成吉思汗為「天才野蠻人」(savage of genius),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こばやし たかしろう,1905- 1987)曾藉此說法刻劃成吉思汗結合游牧戰士與草原領袖的理想性格。符拉基米爾佐夫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後的蘇聯社會,被指責具有「唯心主義觀點的本質」,將成吉思汗的個人成就凌駕於社會發展之上,符拉基米爾佐夫最終在壓力之下,在其遺作《蒙古社會制度史》之中改採唯物史觀描述成吉思汗的角色,否定其西征的正面意義,但是這本成吉思汗傳,對於共產國家以外的學術界影響深遠。
格魯塞則是與東方學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齊名的學者,他在1944年出版的《世界征服者》,雖是普及性讀本,卻嚴格遵守了歷史的客觀原則,除了生動傑出的敘述,書中極少發表個人議論,但透露著對成吉思汗英雄特質的崇拜,也提到蒙古西征的殺戮,導因於蒙古文化與當時正義觀的侷限,並非成吉思汗個人性格上的嗜殺。對於蒙古征服的影響,則以文學手法說道:「將環繞禁苑的牆垣吹倒,並將樹木連根拔起,卻將鮮花的種子從一花園傳播到另一花園」,暗示其西征在促進文化交流上的正面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對於成吉思汗的各種書寫,基本上延續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的唯物史觀,秉持著「肯定其統一蒙古諸部的相關作用,卻不應過度歸功於成吉思汗」,尤其是強調征服戰爭中造成了人民的傷亡、流離與對各地的破壞。但隨著共產世界中政治情勢的變遷,關於成吉思汗的評價也隨之再度擺盪,例如1962年成吉思汗誕生八百週年紀念,中國學者韓儒林為了反駁蘇聯對成吉思汗的否定,展現中方史學界的自主,強調成吉思汗對中國歷史的貢獻,以及西征功大於過的評價。蘇聯學界對此馬上做出回應,其科學院院士邁斯基(Ivan Mikhailovich Maisky,1884-1975)撰〈成吉思汗〉一文,肯定其統一蒙古諸部的貢獻,但是否定其征服活動。另外一方面,在成吉思汗的故鄉蒙古本土(蒙古人民共和國),在身為蘇聯附庸的時代,蒙古人民也一度喪失頌揚民族英雄的自由,直到蘇聯解體之後,蒙古共和國的民族主義勃興,展開對成吉思汗的重新評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學者比拉(Bira Shirendev,1911-2001)的影響,他譴責過去共產政權對成吉思汗的評論是削足適履,曾說道:「成吉思汗在歷史上既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他是一位功績與矛盾兼具並且充滿傳說與神話的偉大歷史性人物」,更不無情緒地說:「他將繼續是(蒙古)民族的守護神」。
從上述成吉思汗研究與傳記的正反變動中,可以發現歷史人物的形象與評價,常常受到外在政治與學術環境的牽動。本書作者除了透過客觀學術史料建構成吉思汗的一生,在最後一章「解讀成吉思汗」中,也提到「成吉思汗是中國人還是蒙古人」的問題,如同作者所承認,這已經超出了歷史研究的範疇,更確切一點說,這已非學術問題,無論是從詞彙的概念定義著手,或從人種學上切入,都難以解答,更無法符合不同立場者的期待。
著有《世界征服者及其子孫》一書的蒙元史學者楊訥曾反思道:「何以相同的事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採用了不同的衡量是非的準繩」,用在成吉思汗的書寫與評價上,頗發人深省。歷史只有一個事實,成吉思汗是中國史、蒙古史也是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政治、學術環境的變動則不免會因為需求而在不同階段以不同的標準做出衡量。在此,我想借用我的業師,已故的蒙元史學者 蕭啟慶教授對長久以來中外成吉思汗傳記的評論:「上帝的還給上帝,凱撒的還給凱撒」(Give to Caesar the things which are Caesar's, and to God the things which are God's),作為最後的總結。成吉思汗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他愛酒、愛色、愛馬,更愛狩獵;他謹慎、自制、尊敬上天,也光明磊落,作為學術研究者,應該致力於將真實面貌還給這位歷史人物。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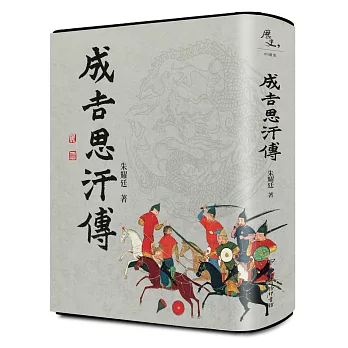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