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情僧錄
a
周夢蝶:周公自號夢蝶,取莊周夢蝶,兼李義山「莊生曉夢迷蝴蝶」之意而成,後乃以號行。他大半輩子禮佛習禪,「但知奉眾,不曾憂貧」,其實像煞了一名雲水僧。
「契濶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生天成佛我何能......尚有微命作詩僧」,以上這些曼殊上人當年自寫句,若移到今日說周公其人其詩,似也頗恰當。
更要緊的,曼殊上人既是他自道的「行雲流水一孤僧」,也是,在這點上他與周公初無二致,一名既愛如來,又愛善女子的情僧。
怪哉此二人,既出世,又入世;既孑然一身,又奉眾利他。不僧不俗,亦僧亦俗;漫言「以情悟道」,多情卻似總無情。
生活於世俗當中,行徑乍看與眾人無異,他們的內心世界迥非一般凡俗所能理解。
余光中在悼詩「送夢蝶」裡,細數周公「文學家譜」,其間也點到蘇曼殊的名。「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這等恍惚迷離的句子,倘挪來描摹夢蝶詩自然精妙的化境,誰曰不宜。
b
這裡無意將上世紀一前一後,百年難得一見的兩大詩僧簡單劃上等號。曼殊上人被譽為與弘一法師同屬「驚世絕才」,影響深遠,不在話下。可他的詩再空靈,再清奇冷洌,猶不脫傳統藩籬,大抵仍以「身世飄零,自傷懷抱,兼寓故國故人之思」為基調。
而周公畢竟是一個澈底浸染了歐風美雨,復從古典詩詞蛻變而出的臺灣新詩人。遠在《孤獨國》、《還魂草》時期,最早的苦吟背後便摻有那麼一層,濃濃的現代派,存在派色調在。剛出道的夢蝶詩,每以日記體,懺情體為本色,以內在獨白及戲劇獨白為擅場,反覆繞著孤獨和死亡的負罪意識在寫。
戰亂流離來臺,周公很快加入藍星詩社,但他詩中因死亡意識而起的,那難掩的孤寂及禁錮感,卻讓創世紀的人對他刮目相看,最早為文高度評價夢蝶詩的,不是別人,乃是張默和洛夫,個中消息,可見一斑。
c
繫在一九八○之下,寫於內湖的詠物詩〈九宮鳥的早晨〉是一大轉捩點。八○年稍早,周公胃疾入院,因病結束武昌街二十一載書攤生涯,搬到內湖,詩風也逐漸從早年的孤絕走向後期的澄明,澄澈。過去詩境中那層灰黑憂悒的底色不再,那些悲喜互尋,冰炭交織的矛盾語法,沉鬱頓挫的獨白式詩風亦不再(包括當年令人過目成誦的名句,如「誰能於雪中取火,且鑄火為雪?」),詩人從人生上半場僥倖存活過來(胃切去大半),也從詩的「內部」走出來,得與天地萬物,與大自然有新的相應相觀照。
此前,他大隱隱於市,少有單純詠物寫景之作。不同於同代人,不論藍星或創世紀諸友,從一開始詩人就默默走一條追求「詩禪一味」的路,但他不也說了,「詩與宗教有其先天性之差異。宗教是素的,詩是葷的。宗教再華麗也是素;詩再沖淡,再質樸也是葷」。回頭看,這葷素之間的拉扯是多方面的,不單存在詩與宗教(禪或佛),也存在文明與自然之間,後者尤其形塑了早期與晚期夢蝶詩的落差。
相由心生,酷似苦行僧的詩人由於長年在騎樓下擺書攤,一度被外媒譽為「武昌街上的先知」,傳誦至今。這騎樓地點並不尋常,乃是座落在當年西門町萬丈紅塵之中,臺北文壇大觀園明星咖啡館樓下。情與幻,真與假,色與空,以上既是詩人當年寫作的主題,估計也是他拿來參禪的話頭公案。早在一九六五年,周公即曾自撰打油輓聯兩首曰:「為愛徬徨,因詩憔悴;隨緣好去,乘願再來」;「生在句下,活在句下;憂在其中,樂在其中」。廁身紅塵二十餘載的周公,作為都會文明的某種「邊界人物」,直堪與十九世紀巴黎蒙馬特的畫家羅特列克比擬矣!
d
若干年過去,周公重返西門町,寫下他的長詩代表作「除夜衡陽路雨中候車久不至」,他已從內湖遷至淡水多年,遠離紅塵,感慨氣象又大不同。認真追究,一九八○的出走正是前後詩風丕變關鍵。這之後,詩人在題材及形式上屢闢新徑,不單寫了數量可觀的詠物寫景之作,且佳篇迭出(寫景有〈老婦人與早梅〉一篇,可入神品),形式上也益發簡練老辣,一步步打磨淬煉下,發展出他個人獨有的,始而如玉珮般清冷,終而如銀鈴般清脆,犀利的短句,引領讀者走入一種頌歌般,聖歌般的幽微之境。
周公封筆於二○○九,高齡破九十。雲水一生,與眾生結善緣,情緣無數(於風耳樓寫寄書簡亦無數),而一輩子同時修行寫作不輟,乃是詩境開拓成熟的原動力。古人說,「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古人又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周公畢生以濃濃「情味」寫詩,筆下每首幾乎皆是「情詩」,即使不然也儘可當「情詩」來讀。
妙的是,周公「情詩」層深思苦者有之,獨少自憐自艾者,原因無他,周公不單每首詩以深情,至性出之,且不以情思宛轉為限,直欲起情於「情所未起」之處矣!
周公有〈約會〉一詩,蓋已臻宋人所說,理,意,想,自然四種高妙的圓融境。不寫約會男女或過往情事,而寫每日傍晚,與詩人促膝密談的「橋墩」!
說來荒唐,又絕不荒唐,詩人說,此「橋墩」每天總是先他一步,到達約會地點,老是在詩人的「思念尚未成熟為語言」,就已及時將詩人的語言,「還原為他的思念」;而他們,詩人和橋墩,又總是從「泉從幾時冷起」聊起⋯⋯此詩結尾,詩人說,他等不及了,明日一定拈著話頭,拈著他尚「未磨圓的詩句」重來,且至少,他飆願說,也絕對要先橋墩一步到達云云。
願天下有情人,有朝或都能略識此中深意!
楊澤
序
跨界
曾寫了一首名為『周夢蝶』的歌,歌頌心中孤絕飄逸的詩人,才因緣際會與曾進豐和向明兩位老師一同前往周夢蝶先生家中,我從我的周夢蝶,一躍進入了我以外的周夢蝶,這兩者之間曾經有一道厚實的牆,就這樣被我跨越。那時還是過年後的春天,屋外是新店刺寒的強風,室內閃著清冷的日光燈,空蕩的客廳,書桌上壓著幾張他的字,極度瘦弱單薄的身體,承受一雙炯炯眼神,我致贈了我的作品和禮物,他邊看還幽默的說笑,說話時習慣揚起手臂,最後他拿起一張寫的好長好長的紙條給我看,他喜歡親手將紙剪成細長的尺寸,不留過多的空白,經他剪裁過後的紙張,搭配他瘦勁的筆跡,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立體的孤絕。
握過他冰涼的手,聞到他家中略帶潮濕的氣味,再看到他連寫著瑣事的便條紙都有理想的規範,每一個字的筆跡都留有不容匆忙的篤定,我不禁想著,『理想的生活』到底是什麼?他所有的喜樂與憂愁,如何長年安靜篩選只在文字中流動,當他決定拋棄身外物,如何看世事變化而能不介入,再用自己的人生煉成一道意味深遠的寓言?在街頭擺攤賣書,苦行度日,將人生過得如同筆下的字一樣再無可剔除的細瘦,需要多少勇氣才能拒絕伴隨命運而來的所有可能?
在周夢蝶與周夢蝶之外的世界,有一道牆,周夢蝶既是善於以輕功登牆的武者,同時是擅於化行動為意境的舞者,隱於市也任意穿梭在極少的物質與極豐厚纏綿的心靈之間,在詩的領域,在疆界不斷重組變形的意義之『界』,他不著邊際探索,他擁有用心靈消融界限的能力,是世人難以企及的。從一而終投身孤獨,每一次創作風格的轉變,每一次斷然婉拒世俗召喚,他將行到水窮處的『極致』,活出既深刻又警世的層次,也將孤獨國裡的『超越』,以寫實的方式矗立在現代紛陳的生活風格之中。
收到傅月庵先生的邀請,要我為周夢蝶詩集寫序時,我內心極為惶恐。流行音樂與文學素來有一道看不見卻明顯的『界』,這個『界』,像唸書時為叛逆而叛逆,沒頭沒腦跟著同學爬的那道牆,當興奮地掛在牆沿,看到自己可以瀏覽高處的風景而開心雀躍,但除了懼高,也害怕一躍而下因此受傷,進退兩難。凡人掛在每一道進退維谷的高牆,這時只要有人從後面輕拍一把,或是讓安全著陸的朋友吆喝一聲,一眨眼,忍住雙腳震動的痛楚,拍拍身上的塵土,是就該頭也不回的往前走去,這時刻,這道牆在意義上就該被消弭。但總有缺乏勇氣的人,會在膽怯中瞻前顧後,在勇氣滿載之前,被躊躇不安漫長的折磨,如此刻的我。
寫詩是孤獨的,以詩為業的人,一生都不斷尋覓一道又一道高牆,孤身一人,來去由我,妄自挑戰修煉字句的心境。我眼中的周夢蝶不需呼朋引伴,不理威脅利誘,甚至不必輕輕躍下,也沒揚起塵埃,只留下飄逸的文字,給這個世代叛逆有餘,勇氣不足的我們,一個輕盈脫俗的示範。
陳綺貞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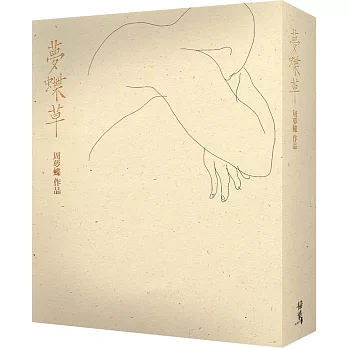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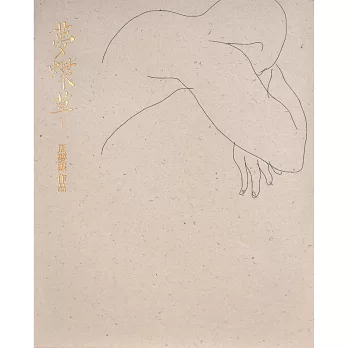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