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鬼魅敘事、倒退的時間 ――序許通元小說《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
張光達
許通元的短篇小說集《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內收小說九篇,取了個趣怪的名字作為書名,同時它也是書中第一篇小說的名字。整體上來看,這些小說具有詭譎奇幻的故事,頹靡不羈的文字,愛慾與死亡、感官意象與非理性的況味、古怪乖張的人物關係充斥全書。在種種古怪乖張的人際關係與人物生活情感底下,其中尤以溢出同志正典(homonormativity)的酷兒情慾最引人注目(或側目)。
近年來酷兒研究從空間(衣櫃、身體、地理、疆界)轉向時間的面向, 對酷兒與同志研究的學者來說,同志運動的批判性與政治性,已被新自由主義所強調幸福家庭和同性婚姻的單一論述所收編,主流同志都在提倡陽光正面的生活價值,其他處在陰影底下、具有負面的生活情感與情慾感受被同志自身所排斥棄絕。在最近這一波酷兒研究的時間轉向中,學者們強調一種酷兒的「負面」的時間觀,即酷兒時間的斷裂、倒退、落後,與恥辱情感的連結。(Judith Halberstam, Heather Love, Lee Edelman,丁乃非,劉人鵬)對這些學者來說,對抗新自由主義應許未來的強迫性欲望,拒絕主流正典所宣揚的幸福感的同化政治,酷兒或同志論述必須突破這個同志正典的形象,建構另類想像,擁抱負面性的情感和情慾,直抵死亡驅力本身。在許通元的小說裡,我們看到,在全球化資本主義所主導的進步線性時間觀的世界,還徘徊著許多異質存在,如小說中的提到的迷信、神話、傳說、宗教儀式、恐怖分子、非世俗的情慾和情感結構。許通元如何通過這些「負面」價值,被正典話語視為落後封建,或不符合進步時間觀念的生活情慾感受,賦予異質主體能動性,為這些異端存在發聲,讓追求正典同志的現代世界與現實生活,顯得鬼影幢幢、迷離荒誕。小說藉落後衰敗而又撲朔迷離的奇幻神話傳說,細緻鋪陳負面頹靡的異質情慾,發掘當代被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所棄絕和打壓的他者、邊緣人和被貼上負面標籤的恐怖分子,叩問和反思繁華與頹敗的共生鏡像關係,讓我們看到陽光背面的微陰處,不時閃現親密動人的浮光掠影,而在敘事時間的前後推移、斷裂延遲、重複差異下,小說中一幅幅斑駁漫漶的畫面,顯得捉摸不定,有待考證。這是許通元這部小說文字的迷人之處。
同書名的小說〈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作為小說集的開卷之作,以長度及內容的複雜度而言,〈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無疑是許通元這部小說集的主力作品。故事中的敘述者決定為自己安排一次逃亡,從新山城市出走,卻巧遇上了分別五年的大學友人「你」,在「你」的盛情邀約下,敘述者跟隨「你」 坐上了北上東海岸彭亨州的巴士,在巴士旅途中,展開了一段親密兼曖昧的對話與欲望互動。過後抵達彭亨州,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跋涉彭亨河和戈松山,遊山玩水。敘述者的思緒和感觸,頻頻回首大學生活的舊情往事,透過與「你」的對話和回憶,昔日的同窗也是眼前的嚮導薩風、大學老師也是今日流亡印尼的恐怖分子阿查哈里,這些人物的舊日大學生活往事、人際互動、難忘舊情,逐一浮現。小說籠罩於兩個強烈對比的敘事聲音,一方面當下此刻的敘述者與「你」的對話互動,無論是直截了當,談笑風生,諷刺幽默,或拐彎抹角,充滿了曖昧的意趣和欲望想像;而另一方面,作為敘述對象的「你」,則對敘述者頻頻回首話當年的人事細節,顯得興趣缺缺,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無論是在巴士旅程上或是在山水跋涉中,有意避開敘述者的追問,或對敘述者所發表的論見不置可否,讓小說的敘事情節的來龍去脈,顯得片斷、模糊、似是而非,沒有定論,或有待考證。而在兩人你唱我彈欲言又止的對話交鋒中,唯獨對「天才型」的大學老師阿查哈里成為恐怖分子一事,兩人的談話偶有交集,敘述者把此事件歸咎於政府高等教育學府的行政偏差,留不住人才,薩風也提供了一些阿查哈里追隨印尼回教祈禱團的原因,在回教祈禱團首領阿布峇卡的「誤導」之下,相信回教國貧窮是因為受到西方霸權及非回教徒的影響,甚至還把馬共牽扯上回教國,但「你」對這個複製國家主流話語或官方說法的版本根本不買帳,頻頻打斷敘述者與薩風的說辭,並對薩風所敘說的另一個彭亨州歷史故事―馬來民族英雄督•巴哈曼保衛國土對抗英國統治者的愛國事蹟不以為然。
小說的高潮在第十三和第十五節,第十三節兩人在溪水中玩水,「你」 對敘述者做出裸泳的性挑逗之後,留下敘述者一人浸在水中,正在享受森林蟲鳴鳥叫水流聲之際,阿查哈里驟然現身。多年不見的老師兼恐怖分子的出現, 令浸在水中的敘述者頓感恐慌,哈哈大笑的阿查哈里說明他並無惡意,僅要求敘述者償還欠他的一個人情,要求他把一枝金蝴蝶型鑰匙送去居住在馬六甲野新的父親家。過後在第十四節敘述者告知「你」這段奇遇,「你」嘲笑敘述者在繪聲繪影,在印尼西爪哇島活動的阿查哈里不可能出現在此,當敘述者掏出褲袋裡的金鑰匙來當作證物,它卻變成了一把普通的鑰匙。第十五節敘述者肚痛上廁所,阿查哈里再度出現敘述者眼前,生氣敘述者把金鑰匙一事告知他人,並希望敘述者這次可以保守秘密,在阿查哈里的念念有詞下,他手中的鑰匙恢復蝴蝶型,還拍動著翅膀,變回之前金光閃閃的原狀,然後他的人在黑暗中消失不見。聽到聲音跑來的「你」看到敘述者裸露下體,遂激起兩人的情慾火花,一觸即發。第十六節敘述者隔天醒來,「你」已不告而別,僅留下一張去吉隆坡和馬六甲的車票。小說第十七節也是最後一節,敘述者來到馬六甲野新的阿查哈里故居,把金鑰匙交給了他的父親胡仙,得知他們家受到警察、記者、陌生人的不斷糾纏,阿查哈里的老婆因承受不住盤問壓力而去世了。離去的敘述者身上只留下山中帶回來的一隻無聲的、普通的馬陸。
以上是這篇小說的故事梗概,當然實際上小說所鋪陳的故事細節要比這複雜許多。作為貫串小說兩位主要角色敘述者與「你」的重要人物阿查哈里,眾人口中的回教祈禱團成員的恐怖分子,他來去無風,在黑暗中出沒,也在黑暗中隱沒,能夠把一把普通的鑰匙變成拍動翅膀的金鑰匙,他究竟是人是鬼,是基本教義派的恐怖分子,還是替天行道的英雄?他對敘述者的恐慌作出安撫, 他把敘述者視為馬來西亞國族的一分子,無疑是對國家政權種族政策的當頭一棒。故事的結尾也頗費人猜疑,在一夜激情過後,「你」不告而別的離去,留下的車票,種種蛛絲馬跡,彷彿在暗示「你」也參與其中,一切都是設計好的,然而之前與敘述者的互動對話,又似乎「你」其實並不知情,也有可能是「你」故布疑陣,擾人耳目。敘述者與「你」一段曖昧游移的情愫,欲望想像,似有若無,因此與阿哈查里的恐怖分子身份,其可疑詭譎的神出鬼沒,亦真亦假的存在,可資對照。兩者同樣令人無從確認,孰真孰假,種種線索模棱兩可,留給讀者一道謎團,自行體會。
徘徊在過往的回憶,山水的迷夜裡,面對這個撲朔迷離的故事和結局,固足以引人入勝,興味盎然。但我以為〈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別有懷抱,許通元小說的魔幻寫實色彩,似真似幻,書寫馬來西亞本土現實素材,經營奇幻傳說的鬼魅(歌德?)敘事,在他之前的兩本小說集《雙鎮記》和《埋葬山蛭》 已有精彩的表現和佳績。相對之下,許通元這篇小說的野心更大,企圖另闢蹊徑,突破舊有的創作方式,除了神話傳說的魔幻色彩,還調動了人文地理、歷史記憶、飲食文學、旅遊文學、鬼話、同性情慾諸多次文類的元素,堪稱琳瑯滿目、別顯洞天。對馬華小說的在地書寫或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感興趣的讀者, 大可緣此追溯這篇小說中的地方誌、本土飲食、各族群的多元文化、揉雜的華語,而有所比附。政府的偏差政策、種族主義、貧富不均、基本教義派、宗教極端分子、殘暴野蠻的恐怖分子、國家機器對人民的箝制、欲望與死亡驅力、懸念……等題旨,在許通元這篇小說角色的對話與回憶裡,欲言又止,不說還休,總是幽幽浮沉於他的字裡行間,成為百難紓解的負擔。政治現實的無從紓解,未來也看不到出路,與國家主流話語所宣稱的未來發展大藍圖,及追求進步線性時間承諾幸福生活的××宏願,實在相去甚遠。前方既看不到任何出路,當下此刻也充滿了重重懸念,小說的敘事時間因此頻頻倒退後顧,經由當事人事前事後的心路歷程與生活感受,來再現或重述創傷的原初場景,藉以指認一段生命創痕或精神逃亡的歷史緣由。但如同後結構主義詩學指出的,任何的重述或再現記憶的努力,終究是片斷的、散裂的、吉光片羽的、無法完整被呈現的。面對時間的傷痕,歷史(精神)的裂變,發生的已經發生,未來惘然待解,我們看到無論是小說中的敘事語言或故事情節,從來不是完整連貫、黑白分明的,就連小說所欲召喚的那個原初場景,也模糊莫辨,處處充滿了裂變、斑駁、幽邃詭異的細節和痕迹。
如同小說敘述者所體認到的,精神鬥爭之可怕決不亞於任何一種戰爭,精神逃亡之痛苦,也決不亞於任何一位戰爭難民所負荷的。安排逃亡的敘述者, 因此恰可與逃亡印尼的回祈團恐怖分子阿查哈里形成對照。前者的精神逃亡起因是個人的情慾創傷,後者的身體流放則是不見容於國家政體。在逃亡的旅途中,兩者都同樣借助於一種倒退斷裂的時間觀,即欲望/情慾/身體的頹廢流連的時間,與非俗世的倫理教義時間,提出對國家所服膺的現代性時間霸權, 及承諾幸福家庭虛假意識的質疑和批判。由此來看,在都市文明無法容身的兩造,執意在原始的山林間,梭巡傷痕累累的原初場景,無論是個人非正典的情慾認同,或恐怖分子神出鬼沒令人驚悚的幽暗身影,既為污名又鬼魅般的存在,兩者的異質性詭奇地交織在一起,又在時間的斷裂縫隙間交錯而過,形成了文本性/政治性的辯證結構,在這一點上,小說敘事暗含著對俗世線性時間進步觀的批判,對國家主流話語的虛假承諾的決裂和背棄。一向被國家主流話語所貶抑的非正典欲望,以及恐怖分子非俗世的倫理認同,反倒成為對國家身份認同最基進的質疑。
〈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中敘述者的精神逃亡與阿查哈里的去國流亡, 因此可資對比。但要如何進一步表白敘述者的精神逃亡,敘說這一段欲語還休的精神創傷,成為許通元此篇小說的最大挑戰。在書寫的層次上,許通元細緻鋪陳敘述者與「你」的情感交流與情慾想像,也在山林中的最後一夜讓兩位角色得償夙願,成功解決這個原初的「匱缺」(lack)。但如同我們在上文提過的,無論如何調動記憶,重啟回憶,終究只說明了那創傷、那原初場景、那倒退的時間的無法再現。作為敘事遺漏或斷裂的部分,那無法完整再現的再現,因此必須不斷以補遺或增補的面貌重複述說。在下一篇小說〈傳說也跟著逃亡〉,小說作者兼敘述者因此調動更多的傳說神話,編織更多的逃亡理由,最終讓傳說也跟著敘述(者)共同逃亡。〈傳說也跟著逃亡〉,就是類似的嘗試,許通元在這篇小說中盡情發揮他說故事的本事,調動了印度支那(東南亞)的傳說和神話作為敘事的象徵資本,小說的形式設計堪稱有趣,每一節以一則傳說與一個理由交替出現,全篇共四則傳說與四個理由。傳說的部分揉雜了從印度支那到東南亞的歷史、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構成古王國的逃亡史(敘述與敘述者再次塌陷於倒退的時間),曲折動人;而理由的部分則交代敘述者的精神逃亡,重複/重述了〈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中敘述者的精神逃亡的緣起,有意思的是,整個「B理由」一節幾乎重複了〈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第一節全部的文字,只在一些句子作出稍微的更動,「C理由」一節也是如此,重複了〈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中的一些段落。重複的文字和段落,出現在〈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與〈傳說也跟著逃亡〉兩篇小說裡,換言之,兩篇可形成互文,延展對話和思考的空間和時間,而後者更像是前一篇小說的增補,一個敘述者有兩個(或多個)表述,前者的精神逃亡以出沒原始山林的恐怖分子為參照,後者的精神逃亡以區域古國的逃亡歷史傳說為參照。兩者有所重複,但在重複的文字中有形式的差異,在重複的欲望中有情慾想像的差異, 重複構成差異,重複也再現差異。因此這不是一個還原歷史救贖記憶的故事,而是一則歷史斷裂時間倒退的故事。
另外兩篇書寫同性情慾的小說〈懸吊半空的男人〉與〈身上藏隱一股鬼氣〉,也值得注意。〈懸吊半空的男人〉的敘述者與「你」在現實生活中的互動(吃飯、看電影、打掃屋子、共乘機車、洗澡),兩人之間親密對話的情慾試探,到小說結束時在浴室裡的情慾纏綿,敘述者的情慾認同或想像,似乎再度重複(或上演)了〈我的老師是恐怖分子〉的敘事結構,差別在於這一篇的欲望場景發生在當下此刻的現實俗世生活中,在情感結構上缺少了一層可資參差對照的向度。不同的是,〈身上藏隱一股鬼氣〉再向酷兒倒退的時間觀借鏡,寫「你」在多年以後仍對敘述者的情意/情慾念念不忘,衰弱身軀猶死守著敘述者一件多年前的短褲,如信物般的守護著。此作看似黑色幽默,實則更能道出靈肉、神魔或人鬼間的情慾糾纏。「你」對敘述者的禁色之愛/慾,驚世駭俗之餘,讀來仍然令人心有戚戚。這裡的關鍵不在於「你」欲望敘述者的不夠耽溺,而在於「你」欲望敘述者的過分耽溺、至死不悔。當最純粹的愛慾成為一種最敗壞的人性蠱惑,最負面的情感結構形成一種最幸福的終生執念, 欲望與身體無孔不入的相互滲透和侵蝕,直抵死亡驅力本身,莫此為甚。一種倒退落後的心理時間,與恥辱情感相連結,其中對欲望/墮落的耽溺與追求, 是如此的魅惑感人,也是如此的動魄驚心。
上述提及的幾篇小說,是這部小說集的佳構,也最能見出許通元書寫相關題材的創意才情。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倒有另一種看法,許通元作為一個有心的小說家,當然不必隨俗高唱酷兒/酷異口號,但在思考新世紀的酷兒情慾或種種的異質情慾時,若能時時向酷兒的倒退負面的時間觀借鏡,注入情天慾海的裂縫與創痕微陰處,而能賦予這塊土地上的人情事故更複雜的、更異質多聲的面貌和意義,應是他未來創作的目標。
完稿於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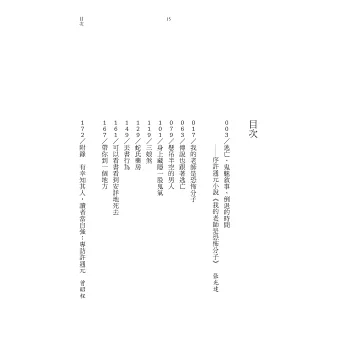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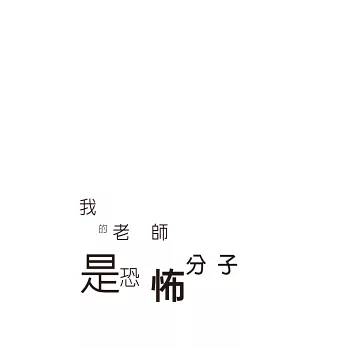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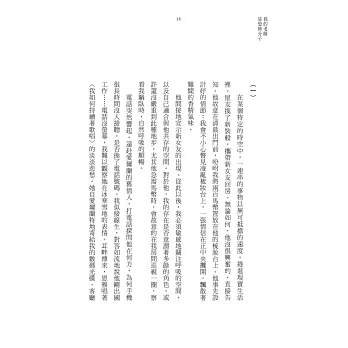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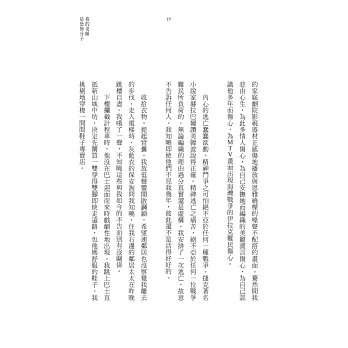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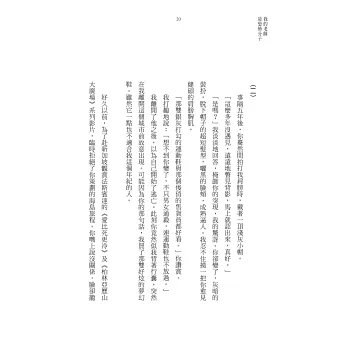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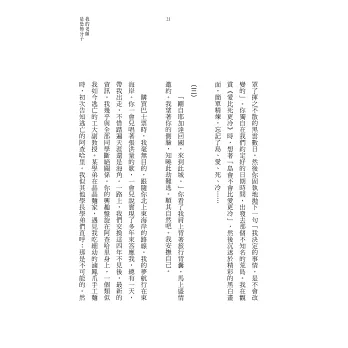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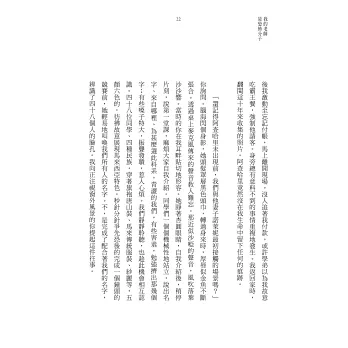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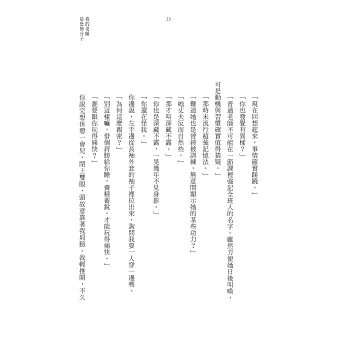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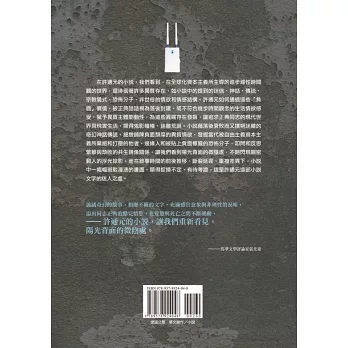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