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序
寫小說
作為小說年度選的挑選人,首先擔憂浮上心頭的,不是揀選時的猶豫為難,更是怕漏看了什麼好作品。因為如何選小說,本就是絕對主觀的事情,好像品嚐一杯杯的紅酒,只要第一口繞嘴下喉,加上縈繞的氣味,愛與不愛就要苗頭初現,第一口能過關的,繼續追飲下去,體質、勁道與餘韻收尾,大約就底定心中答案,要真的說起來,並不怎麼難的,其實就只是端看嗜飲者口味的高低與何在。
另一個真正迴旋難去的念頭,卻是回到為何要讀小說,以及為何要寫小說?這樣有些俗氣的現實問題。在一年的閱讀過程裡,清楚感覺到短篇小說的發表量,並不如想像中來得豐沛,可以發表小說的園地,其實也因之寥寥可數,文學雜誌(譬如《印刻文學》)以及副刊(譬如「自由副刊」與「聯合副刊」)依舊是主要鎮守者,反而蔚為各方流行的文學獎,或因其可能會帶著短期競賽的壓力,有著炫技爭先的必然意味,大半難以顯現沉穩內斂的質地,遺憾地大半不大符合我的飲酒品味習性。
另外,不少會吸引我目光的短篇,其實是從長篇小說裡擷取出來,這有趣地顯現出小說創作的能量,確實有集體往長篇方向移動的趨勢。所以如此,可能也反應了讀者已然不耐閱讀小說的事實,作為往日短篇小說主要孕育園地的副刊,因此已經見不到過往發表的繁茂風華,創作者改而以更漫長艱辛的長篇做出路,這雖然像是不得不爾的現實回應,其實也可能是另一條文學風景的路徑啟始。
而關於寫小說在現實裡的難為艱辛,王德威其實早在2002《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的前言裡,就有些暮鼓晨鐘地點出華人小說家在應對時代巨變狀態下的現實時,各自選擇後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王德威同時意有所指地暗示著寫小說這件事,本就有著與世道相互背離的必然特質。他寫著:
「中國『現代』小說,果不其然要隨著二十世紀成為過去?有能耐的作家,早已伺機多角經營。他(她)們或為未來的作品累積經驗,或藉已有的文名隨波逐流,是非功過,都還言之過早。與此同時,就有一批作者寧願獨處一隅,以千言萬語博取有數讀者的讚彈。……從自我創造,到自我抹銷,滿紙是辛酸淚,還是荒唐言?兩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獨的身影,依稀重到眼前。而我們記得,《紅樓夢》寫了原是為一二知音看的。」
確實,不僅是辛酸淚與荒唐言樣貌難分,自我創造也與自我抹銷共生同謀,讓小說文學不免顯得異音紛雜,看起來既是繁盛似錦、卻也恍如廢墟顧影,面對走馬燈般乍乍逼來的新世紀時,更不免要露出舉足躊躇、四望茫然的孤單。然而,王德威並不因之絕望,尤其指出「有一批作者寧願獨處一隅」,並且懷抱著有如曹雪芹書寫《紅樓夢》,那樣「寫了原是為一二知音看的」心情,繼續這樣不絕於履的寫小說艱辛路途。
也許,這就是我閱讀小說時,不斷迂迴想著的文學事實與寫作人身影。我的挑選由是攜帶著我對這樣執著於「獨處一隅」者的敬意,這同時反應我覺得小說品相與內涵的文質彬彬,是閱讀時相對重要的衡量點。
以下,我就先簡述一下年度選入的作品,所以會引我喜歡的原因所在。
童偉格的〈任意一個〉,描述懷抱著某種神聖使命的神父,遠離家鄉並到達這遠方的島嶼,因而周旋在人間歷史裡的國姓爺,以及不斷尋求能與之作對話的上帝之間,展開了聖與俗的交戰辯證。雖然還不能透過擷取的短篇,來窺探整體的全貌與意圖,然而文字醞釀的氣勢已然驚人,以著彷彿遠自天上觀看世間一切的說書人腔調,以及聖經文字般崇高的舒緩韻律,講述著一個人間歷史的宿命與悲劇。
羅浥薇薇的〈斷代史〉,敘述一個漂泊與游牧靈魂的愛情自白,以碎片般的自由態度,開放著在分合偶然中的生命機運,卻也在尋求絕對的自由與真實時,屢屢突然地回顧徘徊。由內在思緒主導行走的敘事風格,成功避免文字的矯情與裝扮,流淌出有如林間小溪的清澈無懼,以及某種飄逸不群的文學氣息。
宋澤萊的〈一個小鎮上不及格的驅魔士〉,以著極其樸素平白的語言,描述一個小鎮具有驅魔能力者的自白與反思。除了反覆表述聖與魔的必然存在,以及信仰自身具有的強大力量,更是透過幾次驅魔的現場描述,反照自己在其中依舊存有的虛妄與慾念,謙卑的自省是最大的話語。十分罕見的宗教驅魔題材,蓄意平凡的自省書寫,直指文學本質與內在靈魂,本來可以連結相通的事實。
陳柏煜的〈寫信給布朗〉,小說文字加入日常口語的綿長獨特,有著散文的輕盈與詩的迷離,敘述風格同樣飄忽有致,在人稱與主體間自在撲朔移動。小說陳述一對戀人的相愛、背叛與分手,是游移在現實與非現實間的懺情書,也是對愛情恆久的青紅燈閃耀質疑。
黃錦樹的〈論寫作〉,一個對忽然離世友人的私己瑣碎回憶,其實卻是對於逝去青春與夢想的緬懷召喚。流利動人卻也龐大浩瀚的鋪陳,是談文學、談生命意義,也談到了純真與愛情,滿是感嘆的生命回顧裡,款款道出意欲歸反原初的企盼。看似悲劇自絕的結尾,其實透露著對生命虛假的棄絕,以及求仁得仁後的安然自在,不是悲觀的哀鳴,反而是對現世價值的批判,以及澈悟後的省思提醒。
吳憶偉的〈練習生〉,描述一個邁入人生中段轉折點的男人,辭去不斷輪轉的各樣無趣工作,窩居在公寓頂樓的加蓋出租房,數年如一日的準備公務員任用考試,竟然發覺自己生命無所依歸的狀態,和這個簡陋臨時的違章頂蓋極為相似。在這過程裡,同時跟隨電視播放的韓國選秀節目,緊張地關心著某位選秀練習生競逐魚餌般冠冕的過程,一邊觀察隔鄰幾間同樣生命漂泊無依靠者的人生。緩緩平靜的敘述裡,隱約控訴時代有如無情的評審,視眾生命如練習生般篩揀棄置,觀視與敘述的淡然風格,讓人不覺有著「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悲傷感。
鄭如晴的〈廖齒科〉,將清淡婉約的一段昔日戀曲,透過女兒旁觀者的視角緩緩道來。沒有激情或戲劇性的情節,像是對坐喝著一碗溫去了的茶,偶爾抬頭互看一眼的人生相聚,無怨無尤的一席茶飲,安靜聽著竹簾外斜雨打芭蕉,然後溫柔道別離去。有著日本文學傳統的隱約徘徊,也有自然主義小說的悄然認命,最珍貴的是生命中擦身而過的彼此,依舊能夠蔓延一世的尊重與諒解。
章緣的〈失物招領〉,描述一個從南京被領養而移民到到美國的華人孤兒,在白人環境裡長大成年後,面對中國社會忽然的富裕,以及因之而來的孤兒返鄉尋根熱,必須因此側側觀看自己的生命歷程時,所表露對過往與未來的同樣不安。除了指出所失去帽子的必然難以替代,有如社會文化的看似相同、卻實則相異,也似乎隱約描寫及批判中國社會在過去的百年間,某種難以尋回的生命本體失落與無依狀態。
董啟章的〈愛妻〉,以女作家在大學教書丈夫的口吻,簡筆白描著女作家的寫作與立志歷程,同時鋪陳出道以來的每一本小說內容大綱。看似交錯也獨立的幾本小說情節,竟也勾勒出女作家的某種形貌,甚至觀看出夫妻間的分歧關係。小說反單一脈絡敘述的寫法,建立起一種「看似無意義的意義性」,讓彷如碎片互不相干的敘事,能在讀者各自閱讀後,生成奇異的連結。同時,也隱約辯證著文學本質在面對市場法則時,如何作因應的矛盾與困局,是對文學未來應當何去何從的嚴肅扣問。
王定國的〈訪友未遇〉,是極度柔軟與輕盈的小說,透過深深地扣敲著兩個寂寞男女心靈的內裡記憶,讓我們一點一點地感受著那種各自難以吐露或分享的生命苦悶困境。這篇小說有著台灣當代文學少見運用自然主義所具有既客觀描述又直逼內裡的特質,看似無一物的敘事章法,卻是精準與巧妙的真實呈現。尤其善用以意猶未盡的餘韻,來表露意在言外意境的手法,以及借用景與物來寫情的技巧,是讓人在幽然看完後,不由得會回繞與喟嘆的小說。
蕭培絜的〈在船上〉,用極度冷靜客觀、卻十分貼近角色內裡的語氣,描繪著一個看似過著幸福穩當人生的現代女子,如何面對自己其實已然完全透明失焦的生命體,雖然也有嘗試做一點點的對抗與掙扎,卻彷彿世間一切都波瀾不興的無動於衷。有著對生命是否就當如此荒蕪失溫的質疑,也是對於存在意義的荒謬本質發出嘆息,小說瀰漫著流動、冰冷也透明的氣質。
夏曼‧藍波安的〈大海之眼──失落在築夢的歲月中〉,描述一個離開故鄉蘭嶼的達悟族青年,開始他在台灣本島的生命旅程,他所要面對的不只是漢人的歧視態度,還有因之對自我身份與自身文化的質疑省思。作者以十分誠摯的文筆,款款凝看這樣自我啟蒙般的生命歷程,沒有尖刻或怒氣的不平控訴,只是平靜地帶著我們一起走過這樣辛酸的生命點滴,深思透過經濟不平等而生的文化傾軋,是如何真切地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命裡。
朱國珍的〈王正義〉,描寫一個原住民知識份子的選舉冤獄故事,文字準確冷靜,現實的連結感強烈,透著一絲魔幻意味與超現實的戲謔性,與選舉文化在小鎮顯露的奇異姿樣,成功地互相做出輝映。作者描繪底層現實的無奈與認命,運用寫實的貼近與溫度感,奠立了小說的紮實力道。
黃崇凱的〈夾子〉,極度迫近日常現實的簡筆描述,讓人有時會呼不過氣來,也被迫必須近距離去盯視這些身邊的事實。敘事不聳動地平實貼地,也許是蓄意在平凡日常中,翻飛出來一些荒謬感,是現實壓迫下曲扭的生命鏡象,文字簡約鏗鏘有韻,讓人想到七等生與王禎和早期作品的冷眼與孤單。
在這些我所選出來、看似歧異多元的小說裡,確實也呈顯出在世代、文學觀與寫作態度的差異,甚至也可以閱讀出來一些趨向與脈絡,我就用以下三點來做個人觀察的概述:
1. 小說與現實的距離
自魯迅以來的華人現代小說,向來與現實牢牢地相互緊扣,其優點是往往能透過這樣的緊密性,呈現出強大撲面的文學重量感,甚至因此直接涉入現實,對之做出是非干預與評斷。然而,這樣以現實為據的文學態度,也是其所以成之敗之的所在,後繼創作者似乎此刻也在尋求其他變異可能,譬如宋澤萊的〈一個小鎮上不及格的驅魔士〉,就探索形而上/神學的文學可能;王定國的〈訪友未遇〉,也讓我們見到如何從日常的私己生命做出發,以輕盈、冷靜及不介入的姿態,尤其避免文以載道的沉重,做出另一種貼近個己內在性的文學風貌可能。這樣拉遠與現實的距離,讓更客觀的內在與想像空間出現的處理手法,基本上已經廣為新世代小說家運用,譬如羅浥薇薇的〈斷代史〉與蕭培絜的〈在船上〉,都是有著這樣特質的小說。
2. 語言的世代差異
此次選出的小說作家世代並陳,資深作家的穩健與宏觀能夠繼續紮實共進,新進者則呈顯出鮮活的自我挑戰面貌,各自有其信仰與風姿,也難以直接做並比。比較有趣的是小說的語言使用,有著明顯從前世代習於將之嚴肅異質特殊化,尋求文字作為小說藝術的一個重要面向,同時也是作為塑造出獨特風格的個別語言,逐漸轉成廣泛去承接與貼近日常口語的傾向,然而二者對文字簡約與節奏的追求,大抵仍然相同,奧義與直白、反溝通與溝通或就是其明顯可見的差異點。尤其,創作者定位自我與閱讀者貼近/遠離的牽動關係,應是另一個背後動機策動的判斷點,譬如童偉格的〈任意一個〉與陳柏煜的〈寫信給布朗〉,就是可以拿來對照的二件作品。
3. 文學是什麼?
王德威在觀看新世紀華人文學走向時,溢於言表的某種憂慮,也同樣顯現在資深作家對文學的綜觀回顧上。董啟章的〈愛妻〉,就直接卻清淡的做出質問,對於文學與市場的關係,或是對於為何以及為誰寫作,都有著深刻的自省與批判。黃錦樹的〈論寫作〉,則是以對友人一生的凝看,來表述文學是否已然偏離初衷的沉痛感受;並以友人類同川端康成〈睡美人〉,那樣對著青春女體之美的純然崇拜,反而招引來社會道德的指控,這位退休者最後決定要燃盡自己的生命餘燭,只祈求能夠顧惜到殘缺的幼者,以能重回母體的溫暖懷抱,有如那只因破殼失敗遭棄的雛雞,令人驚喜的奇蹟復生,是在生命的哀嘆後,依舊寄予的微弱希望。整體來看,我覺得黃錦樹的〈論寫作〉,是很清楚點出文學整體狀態隱憂的作品,就是當小說文學在面對資本市場的強力傾軋時,究竟如何尋回文學的初衷,如何能藉此而在對抗的過程中,還可認真去顧惜那些不免殘敗受傷的軀體,然後依舊能選擇「寧願獨處一隅」,為「一二知音」寫作下去,所做出來的低調期盼吧。
年度小說獎得主為王定國的〈訪友未遇〉,因為書寫裡成功掌握短篇小說的侷限篇幅,以悠長緩慢的自信節奏,細緻迷人也精準內斂的語言,逐步地描述著一個暗隱的內心傷痛,同時展現出人與人之間,依舊能夠相濡以沫的溫暖情懷,是能夠有著宏觀大氣、卻身姿謙遜的優秀作品。
此外,王定國捨棄直接控訴現實、選擇以影寫光的書寫風格,讓我們見到在華人百年小說發展裡,某個程度過度籠罩在魯迅藉文學以救國族的寫實主義長久影響,得以往著類同自然主義方向移轉的可能。這樣書寫的特殊處,就在於能從幽微處下手,以見出大宇宙的鏡照,手法精妙卻毫不炫耀,有時甚至流暢平淡到會叫人不小心就視而不見的疏忽掉。
那麼,這樣的文學,又究竟有何好處呢?我個人尊敬的小說家宋澤萊,在1988年前衛出版社個人作品集的序言裡,曾這樣寫道:
提及自然主義文學,在大學時期我就知道它了,在未十分了解寫實、浪漫、超現實、意識流這些文學作品之前,它就被我喜愛了,並且懂得它的內涵,這種藝術是擯除主觀、直觀,以客觀的態度來平鋪題材的一種藝術。……最重要的是自然主義者一直努力揭示罪惡警惕人,而居然可以完全不帶說教的味道。
此階段的宋澤萊相信小說「只能張著眼睛,注視悲劇的到臨」,因為「世界的真貌其實就是那樣的」。這種相對來講顯得宿命的客觀與退讓態度,可能恰恰是對於另一浩瀚抽象世界(命運、神或上帝),因為尊敬而自然顯露出來的某種謙卑,此外也常可藉此冷靜的距離,抽離開或會導人涉入過深的此刻現實。
於我,王定國的〈訪友未遇〉,就是這樣時代價值的展現。
阮慶岳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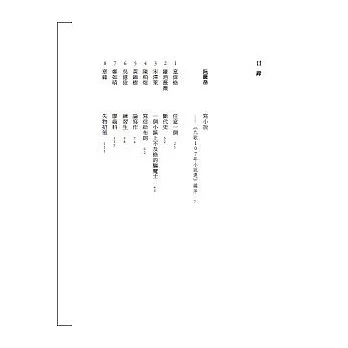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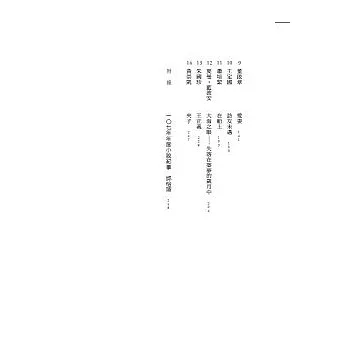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