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偏在
吳曉樂說起各種「可是我偏偏不喜歡」的時候,有一種腰桿堅挺的氣勢。
而且帶著動作。雙手攀扶摸索,向上。她想站直,正在站直,站上屬於她的位置,最終氣宇軒昂。
令我欽敬的意志續航力。
是世代差嗎?差一個年級,女人承擔的形象依然近似,掙脫的姿勢和力道卻大有不同。除了她,還有母親。她與母親之間的拉扯,特別吸引我注意。在韓國釜山得男佛前,她們在立心上拉扯。母親明白求子不可得的辛苦,希望她能預先置備庇蔭,要用就有,不用也無傷。女兒不肯,因為當年就是這種立心,傷了母親。此心不可立,不可縱,不可不戰,即使要戰的是整個世界。
這份心意,母親們跟上了嗎?
世上最嚴酷的警總,在女人心裡。但不是每個女人都意識得到自己一人分飾司令與嫌犯,刑求與招認,傾軋與窒息。父權社會對女人採取電擊項圈式訓練,多數女性早年就能學會,在一趟鼻息之間完成自審自囚的程序,不僭越世道不肯給的權益,而且因為發生得頻繁,久之還當是呼吸的一部分,行有餘力並且不忘提點她人凡事自罪,這個「她人」得用女字旁。
二人以上參與的審查和拘提,難免出現掙扎抗拒,而這二人的組合,因為社會結構的緣故,經常是母女,越是害怕觸電的母親,越常囚禁女兒,因為捨不得心愛的孩子在行走間受到更大的傷,乾脆自己先打,打怕她。母親們經常忘記兩件事實,一是女兒活的是她自己的命,二是女兒年輕,而且強壯。女兒未必遇得上母親曾經遭遇的電擊,即使遇上,未必經不住,有些人甚至智勇雙全,能挺著疼痛找出電源開關,一拳捶爆那些傷害過自己母親的東西。
能夠如此相互明白的母女,是最強大的支持團體,但「相互明白」不是一席話說完就能開花結果,要磨。書裡常能看到吳曉樂與母親的相互砥磨,也許直面,也許背對,但始終不曾中斷凝望。無論是笑是淚,她們在心裡一直看著彼此。她的躊躇,是她的堅毅;她的決斷,是她的牽掛。
人無法預測前路,卻能練習步伐。幼時的吳曉樂曾經埋怨母親不願為她放下正在閱讀的書本,日後卻領悟,能有個偏偏不願放下心之所向的母親,不是每個人生下來都配給得到的行路教練。人可以偏偏要,偏偏喜歡,也可以偏偏不要,偏偏不喜歡。倘若無論如何都有人叫好,卻也有人看壞,選自己甘心好樂的事來偏偏,總是不虧的。
一個人能站起來,不只是一個人的起來,尤其女人。行路有伴當然好,但最好的,終究是能站直來走,不必人扶。愛牽誰牽誰,不想牽的時候,任止任行,遠近高低熱鬧寂寞全由自己。想自由自在,首要條件是自己得在,無論別人如何不給不許,自己偏偏得在。吳曉樂,偏偏就是在。
江鵝(作家)
後記
來一把合於心意的開罐器
很多讀者寫訊息給我。其中,有些人是這樣子開場的:「把孩子哄睡了之後,熬夜看完了……」有時人生比較困難,開場就會變成這個樣子:「在孩子不斷的吵鬧下,好不容易讀完了妳的書。」也有一位讀者,可愛得附上照片:她低頭讀著書,雙腿收在椅子上,而她的孩子手持玩具戳她,試圖索取她的注意力。她沒有說掌鏡的人是誰。我猜是她的丈夫。
我這回在寫字時,說不上來為什麼,不斷地想起這些畫面。我理解到,原來我有一部分的讀者是長這樣子的。她們有孩子,而她們的時間被孩子切割得很零碎。她們很提心吊膽地閱讀,畢竟,要不被打擾地讀完一個章節,至少在孩子長大以前,是不易的。
在這本書從無到有的過程中,很多人關心地問:這一次書寫的主題是什麼?我獨自想了很久,到了中間階段,才有勇氣說,哦,我想書寫的是,我個人從小到大的一些感受。有些是與家人的聯繫,有些則是我身為一個女生的經驗。有趣的是,有些友人得知之後,沉吟好半晌,反問,女生的生活有什麼特別的嗎?怎麼要特殊強調?我很訝異,他們以為,既處於同一方水土,感受自是並無二致的。我幾乎要為他們的無知喝采了。
我也無知過。
情人是左撇子。一回午後,我們在廚房張羅晚餐,我遞給他一把開罐器和一個玉米罐頭,說,喏,你把這罐頭打開一下。旋即轉身,去照顧爐子的火候,順手把菜葉給洗了。好半晌,我還等不到玉米,於是嘟囔,你怎麼開一個罐頭可以開這麼久呀?我湊過去,把那顆咬了一半的罐頭端至面前,我說,你看我這樣辦。沒兩秒,罐頭咧開嘴。我以為是自己開罐頭的技術高明,直到他埋怨,那是因為開罐器是為你們右撇子設計的。我不信,把開罐器還給他,要他再示範一次。幾秒鐘過去,我看懂了,他是對的,那開罐器對付的簡直不是罐頭,而是他的左手。他得把開罐器託付於右手,也就是他的非慣用手,才能勉強地、事倍功半地,創造出一些進度。
這世界上散落著非常多顆罐頭,裡頭裝填著比玉米更閃閃發亮的物事,迷人的職業、夢想、志願、生活方式,或通往某些殿堂的門票。我很想要撬開罐頭。偶爾,我很幸運,旁人為我遞上了開罐器,我很明白,我比那些沒有開罐器的人還要幸運太多了。偏偏,這麼多年下來,我也想送給自己一個木箱,並且站上去,誠實地宣告,有些開罐器不是為我這種人設計的。我得把這開罐器交給另一個自己。一個比較不像自己的自己。當別人告知我,嘿,我覺得妳這樣很好,跟很多女生比起來,妳好理性,不情緒化。我只能視之為讚美,只能暗自壓抑著手的隱隱作疼。我那時還長不出聲音,去跟那些人說明,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十分明白,同樣是抒發情緒,男人這麼做是真情流露,女人這樣子做是歇斯底里。我得學習不要那麼常表達意見,這樣子會引來不必要的威脅。而在被允許表達意見的場合,我得慎於穿著,在無趣、醜和淫蕩之間,摸索出一套衣飾,既滿足審美上的標準,又不至於讓人誤認我別有用心。我漸漸對於自己撬開的與撬不開的罐頭發起呆來。我不能說我的手在痛,不能解釋我是以非慣用的自己在過活。女人一旦訴說起生活上的不理想,很難不被劃分為無病呻吟。我在書寫的過程中,不乏有人支持,仍屢屢感到難為情,甚至想著,也許該記錄更嚴肅的痛苦?
每每有這種意想時,那些女人的訊息,就如同從窗外探進的綠意,不驚擾任何人地,予我慰藉。她們也有這種淡淡的苦惱吧。多想要一些自己的時間。多希望孩子睡熟一點,讓我能夠安心地翻頁。我禁不住幻想,她們是如何輕手輕腳地步出孩子的房間,從櫃上取出書,翻到書籤的位置。壁上的時鐘顯示著十點多一些,或更晚。泡上一杯茶,在暖黃的燈光下,她們走進我的世界,還得留一隻耳朵注意孩子的細微聲響。而我,能夠交給她們孤獨嗎?讓她們再一次被說服,自己有時說不上來的鬱悶,並不值得認真以待?不,不應如此。過往的漫長歲月,身為女子的偶爾煩心與苦悶,被認定為小家子氣的討論,大家不必放在心上。我們該重新檢討這種謬想了。最好的時節是,若有朝一日我們見到一個人打不開眼前的罐頭,我們能夠想像到,也許他手上的開罐器並不好使;甚至,我們願給他資源,讓他得以設計更合於心意的開罐器。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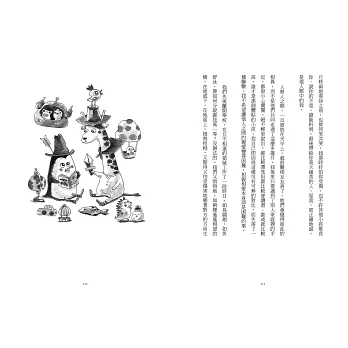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