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序
《簡愛》第一版不必有序言,所以我沒有寫。第二版付梓前,需要致上謝意,並做多方面的說明。
我要向以下三方致謝:
感謝讀者用寬容的耳朵傾聽了一個並非驚天動地、盡可能謙卑的故事。
感謝報紙雜誌為一個懷有寫作夢想、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提供了公允的評論空間,讓大家誠懇地暢所欲言。
感謝我的出版商以其務實而開明的態度,向一個沒沒無聞、無人推薦的作者提供了機智而強有力的幫助。
對我而言,報紙雜誌和公眾讀者是籠統的,所以我只能籠統地致謝,但我的出版商是明確的個體,一些慷慨鼓勵我的評論家們也是如此,只有寬宏、高尚、大度的人才知道如何鼓勵一個力爭上游的陌生人。對於他們,亦即我的出版商和那幾位評論家,我要誠摯地獻上謝意:先生們,由衷地感謝你們。
感謝過提攜、讚許過我的諸位之後,我還要對另一群人說幾句:就我所知,人數並不多,卻也不容忽視。我指的是那些大驚小怪、吹毛求疵的人,他們質疑《簡愛》這類小說的指向性,因為在他們眼裡,與眾不同就意味著不正確;只要他們聽到有人批判「偏執」這萬惡之母,就認定那是在汙蔑虔誠的信仰,褻瀆上帝在人間的威信。對於這些質疑者,我要指出一些顯而易見的區別,提醒他們認識到一些簡單明瞭的事實。
傳統並不等同於道德。自詡為正義並不等同於信仰。抨擊前者未必要詆毀後者。揭下法利賽人的面具,並不意味著將褻瀆的手伸向耶穌的荊冠。上述這兩件事、兩種做法是截然相反的,其迥異不亞於善惡之別,人們卻習慣將它們混為一談,但它們不應該被混淆。我們不該錯把外在表象誤認為真相,不能用那些只為了取悅、抬高少數人的狹隘的世俗教條取代基督的救世信念。容我再重申一遍,這兩者截然不同,黑白分明地劃出清楚的界線是件好事,而非壞事。
世人或許不樂於見到這些概念被區分得涇渭分明,因為大家已習慣將它們混為一談,覺得這樣很方便:把外在假象視為真正的價值,看到潔白的牆壁就認定那是清靜的聖壇。世人可能會痛恨那個勇於深入墳墓,掘出墓穴裡的遺骸,膽敢探究,剝掉表層的鍍金,揭露出下面黃銅本質的人。世人雖然會憎惡那個人,卻也受惠於他。
亞哈王不喜歡米該雅,因為米該雅從未向他預言好事,言必稱災禍。也許,那個善於諂媚的基納拿的兒子更能討亞哈王的歡心,但是,倘若亞哈王能夠拒絕聽信讒言,廣納逆耳忠言,也許他就能逃過死劫。
在我們這個時代也有這麼一位先生,他不會奉承、投他人所好。在我心目中,他來到社會上的大人物面前,正如音拉之子米該雅走到猶大及以色列諸王的面前,同樣坦白地說出深切的真理,同樣說出攸關性命、先知般偉大的言語,同樣表現出無畏的膽識。這位創作《浮華世界》的諷刺作家是否受到上流社會的青睞?這點我無從確知。但是我想,那些被他投以譏諷的火藥、遭受他閃電般譴責的人們之中如有人能及時接納忠告,他們與其後世子孫或許能逃脫基列拉末城外的致命劫難。
為何我要提及這位先生?讀者啊,我要提到他,因為我在他身上見識到了一種智慧:比他同時代的人們所能認識到的都更深刻、更獨特;也因為我視他為當今領先於世的改革先驅:
堪稱旨在撥亂反正、重整秩序的改革人士之領袖;更因為我認為,至今還沒有哪位評論他作品的人士找到了最適當、最貼切的詞彙來形容他,來切實刻畫他的才華。他們說他就像十八世紀的諷刺作家費爾丁,他們談到了他的機智、幽默和喜劇的功力。他與費爾丁的差別就像老鷹之於禿鷹:費爾丁會撲向腐屍,但薩克萊從來不這樣做。薩克萊的機智是巧妙的,他的幽默是有趣的,然而,相較於他真正的才華,機智和幽默不過就像是輕輕掠過夏日雲端邊緣的零星閃電,而非深藏在雲團深處的奪命電光。最後,我之所以提到薩克萊先生,是因為──倘若他願意接受陌生人的獻詞──我願將第二版《簡愛》題獻給他。
柯勒.貝爾*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柯勒.貝爾:夏綠蒂.勃朗特出版《簡愛》時使用的筆名。當時的英國社會保守,少有女性寫作小說,夏綠蒂和妹妹艾蜜莉、安妮出版三人詩作合集時,為避免讓出版社知道她們的女性身分,分別為自己取了較為中性的筆名:柯勒.貝爾、艾利斯.貝爾、艾克頓.貝爾。
推薦序
幾乎最美的愛情故事,都以悲劇收場,因為它得滿足世界那顆異常歹毒的心。
如果黛玉嫁給了寶玉,《紅樓夢》就得完蛋;如果傑克和蘿絲都沒死,《鐵達尼號》就得完蛋;如果羅密歐與茱麗葉私奔成功,莎士比亞就得完蛋;如果梁山伯與祝英台喜結良緣,兩隻蝴蝶就得完蛋。
所以,世上任何一個良善的作家都心力交瘁、萬般艱難。因為,他的任務就是:把美毀滅給人看。
幾千年來,人類為什麼如此痴迷於悲劇,痴迷於美的毀滅?
卡夫卡說,是因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嫉妒之火,是罪惡的擴散。
尼采說,是源於酒神精神,是人類要在悲劇的痛苦中感受一種更高的歡樂,看到生命永恆的美感。
佛洛伊德的說法更絕望也更極端:自從有了性,人類的悲劇就註定了。但佛洛伊德也沒打算變成蚯蚓、蝸牛與水母,甚至,這個偉大的釋夢者,一生都活在瑪莎的愛情美夢中。
蒙元以來,有一句著名的詩句被廣為流傳: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翻譯成白話就是,愛情究竟是一種什麼病?它為什麼讓人們無一倖免?為什麼每個患者都被它折騰得死去活來還心甘情願?
八百多年過去了,沒人回答得了,也沒人要聽答案。
人們心心念念翹首以盼的是作家筆下那對男女主角的病情,而且一定是病情愈奇特非凡、愈危如累卵、愈艱難困苦,人們就愈興奮、愈沉醉、愈狂歡。
《簡愛》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它讓全世界都望眼欲穿。
一個一無所有且長相平凡的女孩簡,與擁有一座莊園的憂鬱貴族羅徹斯特之間,是否會產生天雷地火的愛情?
女主人公是怎樣讓一個風度翩翩的貴族墮入愛河的?
沒有人不記得這樣一段有關自尊之美的獨白:
難道您以為,我貧窮、卑微、樸素、渺小,所以也沒有靈魂、沒有心嗎?您想錯了!我和您一樣,有完美的心靈!要是上帝賜予我一點美貌,再多一點財富,我就會讓您難以離開我,就像現在我難以離開您。
接著,讓人沉醉的時刻出現了:高貴的莊園主突然將她擁入懷中,向這個卑微的女主角求婚──屈膝於她的自尊之美。於是,麻雀重生,鳳凰于飛,幸福伸手可及,美夢就要成真。
但是(請允許我說但是),一個稱職的作家不會忘記自己的任務,他的任務是讓美毀滅,讓愛崩潰──正當這個女孩心花怒放地準備做貴族新娘的時候,折磨人的巨大的病痛開始了:
有人指認羅徹斯特是已婚男人,這場婚姻完全是個驚天的騙局。
一瞬之間,幸福灰飛煙滅,女主肝腸寸斷,她只能懷著一顆破碎的心悄無聲息地離開。
每個人都為她流下了辛酸的淚水。
怎麼辦?這一次,夏綠蒂.勃朗特展示了一個作家絕對的冷酷:她讓一場大火將羅徹斯特的莊園化為灰燼,不只如此,她還讓永遠閃耀著高傲目光的羅徹斯特在一場大火之後雙目失明。
只有這樣,受盡折磨的卑微的女孩才能重新回來,與這個一無所有的可憐的男人破鏡重圓,相親相愛。
於是,這個殘忍的故事贏得了全世界的讚美;而作家付出的代價是耗盡心力,英年早逝。
我理解人們如此持久熱愛悲劇的理由,僅僅是為了可以替他人悲憫,可以替自己糟糕的生活寬容、慶幸。
何三坡
二○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於雲間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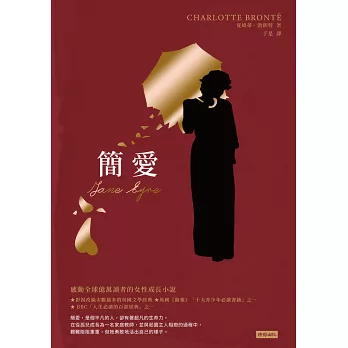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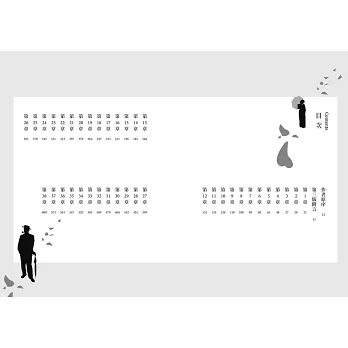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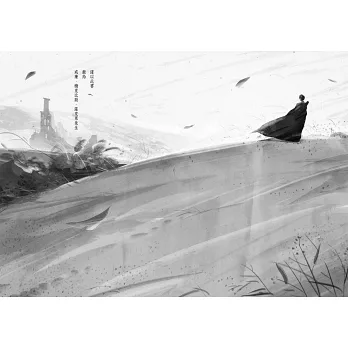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