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關於書名(直譯)《漢文脈的近代》,似乎需要加以註釋。通常,講「漢文脈」,是相對於「和文脈」而言;而其「脈」之發源處,即為相對於「和文」的「漢文」。但是,本書所念茲在茲的「漢文」,並非單純只考慮在日本所閱讀、書寫的漢字文言文而已。在此,我暫且將「漢文」理解為:近代之前,以中國為起點而流通於全東亞的漢字文言文;並且,將「漢文脈」理解為:以上述漢字文言文為原點,所展開的 écriture(書寫)圈域。
之所以說暫且,是因為「漢文」也可以稱為「中國古典文」,過去也曾有過「支那文」這種稱呼。我確實擔心,一旦言及「漢文」,是否會無意間傳達其做為日文、並以訓讀為前提的意涵;而我也瞭解,可能有人會認為「漢文」是徹底以中文寫就,所以應該稱為「中國古典文」。然而,「漢文」這種 écriture 的可能性,就在於它超越了東亞地域的諸語言而廣泛流通;去議論那究竟是日文還是中文,甚至會讓書寫語言做為書寫語言自身所帶有的可能性,被統一的國家音聲所扼殺。從而,比起「中國古典文」這種單純表示中華世界基礎的稱呼,我勉強選擇「漢文」,是因為這種稱呼流通於中華世界的邊境。這絕非所謂做為日文的漢文。相反地,我把重心放在它的越境性質。
本書的主題,是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日本與中國的 écriture 之演變,且在此演變過程中雙方相互交流、影響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我的考察對象,同時是書寫語言個別的變化,也是其結構的變化,甚至是對書寫語言之認識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陸東部與日本列島,不管是論述或是出版品的流通空間,都能看見雙方非常緊密的結合。由這樣的結合所構成的歷史時空,本書則稱之為清末=明治(期)。如此稱之,是想藉由連接個別國家所使用的歷史區分之稱呼,來開拓一條路徑,邁向新的視野。此外,在意識到「écriture的演變如何表現的」這個問題後,為了描述書寫者與閱讀者之間交互作用的場域,我準備了「文學圈」─為使近代以前的「文學」與近代以後的「文學」產生關連─這個詞。而本書也是一本關於「文學」的書,這是因為,我認為談論文學應該盡可能地切合書寫與閱讀的狀況。
本書共分為四個部分,以下就各部分加以敘述。
第I部是「『支那』與『日本』」。本部欲闡明日本國民國家意識之確立,以及將「支那」析出至外部的文學史文本之成立,這兩者有著密切關係;更甚,「支那」這個稱呼的出現本身,就預告了這一件事。同時,藉由分析「écriture史」的論述,我也嘗試追溯其被加上國籍的過程。今日,談論漢字、漢語、漢文的論述,源源不絕地在市場上供給著,其中「『漢文』是日文還是中文?」這樣的問題反覆可見,彷彿是個必然的提問,而這絕不稀奇。這顯示著我們做為歷史性的存在,不管願不願意,都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當中。既然本書的視角是要將「漢文」相對化,以發現新的可能性,那麼追溯其被加上國籍的過程,就是必要的。
雖說如此,也必須避免再生產出粗糙且陳套的民族國家論。舉出清末=明治期所寫的文本、並指出其中的民族國家意識,這本身並非難事。而所謂傳統的發現、古典的創造等概念,對我們來說也有些厭膩了。
盡可能切合文本,而不讓結論封閉。看清細部向量的多樣性,並對其中一個向量逐漸取得特權的該機制進行敘述。文本不該以單一角度理解,而是要放在複數的文本當中來理解。在第一章裡,我並非將三上參次、高津鍬三郎《日本文學史》當作起點,而是當作節點來討論,就是遵循上述幾個注意要點。在這樣的意義上,第I部也有為全書整體議論進行預備動作的面向。
第Ⅱ部「梁啟超與近代文學」,是以梁啟超這位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的小說論為中心來展開討論。或者,也可以說是從他的小說論,來討論梁啟超何以能夠是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在近代的範疇裡,詩文和小說都屬於「文學」,但是在傳統中國,詩文與小說並不屬於同一範疇;即便金聖嘆將之相提並論,那也始終是將相異次元之物並列的一記巧手妙著。如同經常被人誤解的,並非詩文位在中心、而小說位在邊緣。成對的中心與邊緣,暗示了這兩者是在可以交換的同一象限中;而詩文與小說,其象限實是相異的。梁啟超接受傳統中國的教育,說起來是以詩文的地平為立足點的知識分子,但在因戊戌變法失敗而無奈亡命日本時,他以日本的政治小說為契機而提倡新小說;由此,他在小說的地平上樹立了新的秩序,並企圖重組「文學」的概念。他導入「國民」與「進化」的概念當作軸心,而雜誌這種媒介(media)則是其基礎。以該媒介為舞台,梁啟超成為了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在那舞台上,日本的政治小說被翻譯成中文,而梁啟超自身也開始執筆創作、評論小說。
這個問題,用「明治期文學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以梁啟超為媒介的中國對近代文學思想的接受」等論題來敘述,大概也是可以的,但是本書並不採取那種影響或接受的掌握方式。梁啟超之所以能夠參照明治日本的論述,並構築新小說論,是因為讓這件事情成為可能的脈絡,早已存在;而本書認為此處才是應該關注的焦點。用影響或接受這種事先就預設了以被動立場為前提的掌握方式,很難凝視那個脈絡。主動與被動的二元關係之所以成立,還是在於它們之間的關係性。若梁啟超是這兩者間的媒介,那就是因為他的登場,才開始令這兩者得以做為二元來呈現;換句話說,是藉由這位媒介,日本才開始處於發信者的位置。況且,梁啟超還是位極擅長扮演媒介的知識分子。藉此,我將在第四章裡,探討他與他周圍的知識分子對傳統小說再評價的論述,而在第五章,則分析他語言意識的重層性;透過以上兩章的分析,應該會更清楚瞭解這點。
第I部與第Ⅱ部,主要是說明有關「建立écriture秩序」的論述;相對於此,從第六章到第九章為止的第Ⅲ部「清末=明治的漢文脈」,則進入各個écriture個案的分析。這也是本書的核心部分。
《佳人之奇遇》與《經國美談》這兩部政治小說,被梁啟超等清末知識分子所翻譯,雖然因此獲得了可譯性,不只停留在日本的國家框架中,但它們的核心卻未必因為這樣而變得明確。政治小說,是將中國傳統詩文和白話小說的措辭、構成等重新編組而成立的,而梁啟超等人的翻譯,則又再次將之重新編組,使之流通於清末的表現空間裡;第六章的目標,即是想就兩者各自的語詞進行追溯,來發現政治小說如何做為近代漢文脈的一種可能。第七章承接此看法,針對《浮城物語》這部做為《經國美談》嫡子的小說進行討論。起先《浮城物語》以新聞小說之姿出現,它有著強烈的意圖,要讓自身適合報紙這種媒介,並欲與讀者共享話語;與坪內逍遙等人所追求的「純粹的文學性小說」不同,它想開拓的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當它離開報紙紙面、附上序跋,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之後,其「非文學性」便受到譴責,掀起了論戰。結果,雖然《浮城物語》與政治小說一樣,都不被當作是近代文學史的主流,但這也顯示了「純粹的文學性小說」是藉由排除小說的通俗性與啟蒙性,才逐漸成立的。
在第八章,為了進一步探求漢文脈的所在,我將討論明治的遊記。遊記,亦即紀行文,在漢文脈裡雖是一種傳統的文類,但進入明治期後,其因航渡海外而擴大了題材,展現了種種多樣性,有大量的遊記被寫下。在學校作文中,遊記也是最適合拿來當成寫作完整文章的教材。以往écriture的基礎,到近世以前,是藉由寫書信文來習得的;但近代以降,紀行文卻漸漸威脅到其地位,而人們也開始摸索過去未曾有過的書寫表現。換言之,遊記的興盛,可說是明治文學的特徵之一,但不知是否因為太容易就會直接連結到傳統文學的世界,所以很少被當成近代文學的一種文類來關注。當然,在個別的作家論中,遊記被當成作家經驗的背書、作家固有視線的證明等等並不稀奇,但那終歸只是將遊記這種文類所具有的可能性割裂、套回至所謂的「作家」身上;如此,能從其中看見的東西自然有限。如果對近代漢文脈的摸索,著眼於這一文類中出現的特徵,那麼對遊記的分析,毋寧會浮現成為核心課題。
第九章,則是討論「翻譯」─明治文學中漢文脈的另一核心課題─並透過森田思軒來討論。思軒的翻譯,一般都被理解為「漢文調歐文直譯體」或是「周密文體」,然而實際的內容,則還有檢討的餘地。其實,思軒的翻譯,是與不可譯性之困境的奮鬥,在譯文中各處均可看見其奮鬥痕跡。那種困難,是自覺到西洋與東洋之距離,所造成的困難;也是將漢文視為從中國帶來的東西,所造成的困難。到明治二十五年左右為止的翻譯,仍無法好好安處於自身語言之中,其帶來的緊張感則制約了全體。藉由肯定賴山陽不介意和習而以漢文寫成《日本外史》之舉,思軒試圖以此來跨越那些困難。而那一瞬間,就是思軒即將自行開拓新的漢文脈之瞬間。很可惜地,未幾思軒驟逝,我們無法看到他的努力有更充分的進展,不過在明治二十九年以後的翻譯當中,則顯示了他所指出的可能性。
第Ⅳ部「今體文的媒介(media)」由第十章與第十一章組成,將討論明治期廣為流通的漢文訓讀體文章,以及作文教育。那既是漢文脈的大眾化也是近代化。首先,在第十章裡,將針對明治十年代起大量出現的、訓讀體漢字假名混用文的作文書進行說明。這種文體在當時也被稱為普通文、今體文等,並做為公眾場合的文體,被廣泛運用於報紙、法律、公文書、教科書等處。而如同第八章所舉出的,在學校的作文課中,這種文體也取代了先前的候文、漢文,成為學習的重心。人們學習定型規格,使用常套句,藉由以主題做分類的範例文集來習得作文能力。到近世為止,文體是隨著文章的主題自然而然地變化,但是明治今文體基本上不限文類,是一種能夠表現森羅萬象的萬能文體。而作文書,就是學習該文體的媒介(media);其書籍樣貌,則是洋溢著明治期新穎味兒的「銅版印刷」。這種頻繁使用注音假名(振り仮名)的漢文脈文體,與銅版印刷是極為相稱的。
進一步地,在第十一章裡,則針對當時的作文雜誌《學庭拾芳錄》、《穎才新誌》以及其所刊載的文章進行說明。這兩份雜誌,一開始都是從刊載學校命題作文中選出的優秀之作,但《穎才新誌》刺激了人們對追求個人名譽的欲望,擁有壓倒性的強勢,而《學庭拾芳錄》不過是轉載了不同學校的考試答案,不久就廢刊了。在《穎才新誌》裡,作文以外的投稿也十分活潑,有不少揭發作文剽竊或批判雜誌及投稿者之作。在如此構成的雜誌版面上,對使用定型規格的漢文脈之同化與反彈,伴隨著少年們對名與實的欲望而出現;這正暗示了漢文脈在下一個世代的命運。
而終章,則稍異於第I部到第Ⅳ部的內容,將討論一位西洋人、也就是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眼中的漢字。那是欲完成西洋與東洋之結合的西洋人視線,也是將漢字視為東洋之象徵、而欲獲得其靈魂的西洋人視線。而那樣的視線,不久也被帶進了東洋內部;在那時候,漢文脈也將展現出新的樣貌吧。之所以將本章置於終章,是由於我想打開通往那一問題之道路,藉此替本書作結。
以上,我依照本書的編排大致敘述了各部分的內容。除了新寫的第九章以外,其他各個章節並非原先就按照這樣的編排而寫成的,而是以一時的關心及成書篇幅之便為優先。當要輯成一冊書籍時,不只是要統一體裁,也得進行必要的修改與訂正;雖然有些章節更改較多,但我並未變動各篇文章的論旨與重點。我認為與其將之排除,毋寧說該歡迎這種細微相異意向的並存。
提到文章寫作的順序,第六章「小說的冒險」是最早的,也可謂本書的正中心。以此為起點,往梁啟超那裡開展的便是第Ⅱ部,再來是第I部;而從政治小說往明治期漢文脈開展的則是第Ⅲ部,然後是第Ⅳ部。關於表記方式,則照以下的原則。
・本文、引用文都使用通行的漢字字體,但藝、餘、辨等則為例外。又,為尊重首次發表時的形態,只有第六章並未更改引用文的字體。
・引用者所做的注記,以〔〕表示,中略則以〔……〕表示。只有必要的時候,前略、後略以同樣的方法表示。
・引用無句讀點,或者是句點、逗點兩者並無區別的漢文(中文)之時,將因應需求施加通行的句讀點。
・要將附有訓點與送假名(送り仮名)的漢文改寫成帶假名的日文(書き下し)時,若要添補原文所沒有的送假名,將以〔〕表示 。
藉由「漢文脈」這個概念,來俯瞰本書所敘述的問題群,恐怕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嘗試吧。成功與否,我只能交由各位讀者的判斷,但若能讓各位共享本書所關心的問題,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對身為著者的我而言就是無上的喜悅了。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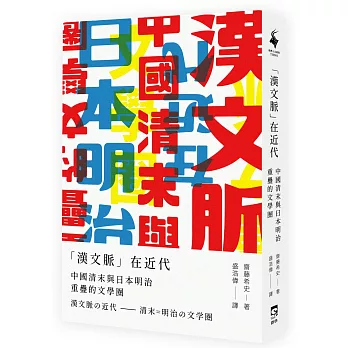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