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拼接試煉二維歧路──讀黃家祥《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
初讀這部短篇小說集,不難發現通往作者書寫小徑的那個岔路口。
沿著本書的編排,前六篇是一段歧路,後四篇是另一段歧路。作者何時佇足於岔路口,該是另一種關於寫者自身文本的探究。雖無法確知這十個短篇的寫作時間帶,但作者已將自身撕開,分裂為二。在選擇虛構的素材上,那精神力像似〈夢浮橋〉裡的K1與K2。雖如此假設,依然需要為原生者K保留一塊彼岸淨土。
或許,正因確立了分裂亦是虛構書寫本質性格之一,《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一書,才能進行更多層的解讀。
我想先提及,細胞分裂──是生物體生長和繁殖的基礎。通常由一個母細胞產生兩個或若干子細胞,是細胞週期的一部分。分裂,在生物特質上是為了延續活的時間;轉身論述,分裂,之於小說,也擁有「為了更新的誕生與繁殖」這層意義。由此,便容易理解基於分裂的敘事之後,為了創造有意識的虛構,需要透過拼接──拼接的敘事技藝,特別在前六篇短篇,成為書寫者對小說形式的索求方式。
寫作小說需要直面形式先決帶來的價值,同時也需要承受相對的反噬──私想,兩者皆是「需要」,但非必然。
企圖拼接的真實難處,在於敘事進行中,如何不淪為單純的拼接。小說的完整拼接與連續影像而完成故事的剪接,在構成要件、執行模組、結果目的⋯⋯若能細究,皆有不同。時常地,文字的拼接易於被使用,也大量被運用,拼接便只完成了拼接的執行。最終看似完成了拼接,卻不一定完成小說。看似進行了虛構故事的創作,實際卻失去故事、情節、角色──這些看似微不足道、卻需要被擱置於心的書寫前提元件。我也經常困於這「易於被使用」、「大量被運用」,以及「看似」,這三者的拿捏取捨。盡力在喘息之間,努力避免輕忽,努力避免漂移虛構重點,以免徒留書寫盲點。
在首篇〈夢孩〉裡,用以明喻的白孔雀的愛之殤與悲之聲,拼接了RPG遊戲夜間測試,再拼接上色情網站的性成癮。這些拼接,透過繁複的詞彙進行,一方面呈現意象的編織,也洩露了散文感的不安。如此不安,是否足以讓角色小柳與靜靜組裝完成人形?角色扮演遊戲裡的「另一個人生」,先彰顯了虛擬搭建的敘事,最後能否成立內建真實的敘事?此外,是否足以讓閱讀之人在詮釋時,堅信現實人生中未誕生的受精卵,在RPG的另一人生中自始自終都只是「可能的夢境」?──這些也是作為讀者我,同時反向寫者我的自問。
夢境擴張嶼記憶拼圖向來都是小說的便利之刃。但若夢境徒留於夢境,解夢之細節的工序,便可能失去爬梳真實記憶的象徵身分。
組裝模型,十分適合兌現拼接式小說的比喻,以及初論。
當寫者打開署名「小說」的組裝模型零件盒子,寫者若能提前一步預見包裝盒上的那個完成品──即便只是落身於想像上的完成品,也已足夠。寫者因為喜愛那尚未完成的完整體,並願意持續想像那「持續的未完成輪廓」,其後的寫,變成了宿命般的動作。動手組裝,等同實踐永遠不存在的流程說明書。那麼組裝步驟,便出現實質執行意義的寫。
另有一事,不容易迴避。在組裝的過程,偶爾會遇上故意遺失零件,甚至是將B組裝模型零件黏製於A組裝模型的嘗試。這是寫者的機巧。然我曾巧遇的機巧,一直建構在高度的技巧基石。以此進階一層討論,不難理解樂高積木可以是同時存有多重比喻與複雜深論的拼接式小說。
與各種強化形式的小說相同,即便完整拼接,小說依舊會在遇上讀者的時點,面對閱讀的臆測:作者最後完成的小說,還停留在零件的散體狀態,或者已經是可供辨識的有機體?──提出這其實無須多言的論述,是思考到在這個意義曖昧與歸零、同質也同值的現代,「拼接」面對這樣的提問,是較為艱難的。
〈通往夏日的歧路小徑〉也是透過拼接,嘗試建築敘事的迷宮。我、楊、小蘋三人有一個三角形,母親、他、她是另一個三角形。兩兩都呈現不規則的身形,任何一邊都可拼接。這也可能意味著詮釋之前的失準──單純是敘事的倒數,而非純粹的時間倒數。
我曾遇偶,那位身分複寫、敘事也複寫的年輕小說書寫者─在寫作最初的小說習作時光,想著如何透過減法,在敘事裡塗銷抹除自身的痕跡。即便是那些被耽誤與誤解的變造式真實故事,也是試圖「減去我」,或者是「除以我」。若能將自身在小說形成的方程式裡,歸零,那所寫下的,或許真的是寫下了。
少有迷宮在建立之初,單就只是為了讓進入者迷路。一個可供定義的迷宮,多半有可詮釋的出口。如此描述,也無法阻止,依舊有某些迷宮建築師,致力於沒有出口的迷宮。他們並非在創建迷宮,而是在驗證詩,以及拓荒詩意的邊界。那樣的迷宮,大於迷宮,也因大於,合理消解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的小說古典零件。
〈大王具足蟲之夢〉,透過表妹的意外橫死,回憶兩人曾經探索的回憶。這直視他人之死,也是操作小說拼接的演練時光。拼接一段內部敘事,拼接一篇短篇,並拼接出半部歧路上的短篇集。如此搭建迷宮的迴路,在這部短篇集裡,確實發生複寫。
紀錄平凡青春般的青春式愛戀故事〈日光夜景〉;在墮胎之前,瞬間短暫回溯而成的〈聲韻學〉;以及,不是雙胞胎的性與死的啟蒙書寫〈雙子〉,皆是作者不斷校對複寫而進行的複寫淬煉。這其中,〈夢浮橋〉可以作為理想的展示。這是一位消防局替代役役男分裂其精神的世界。在「持續救護」著K1與K2的分裂同時,又虛構紀錄著愛戀。作者將夢置入現實,不少時刻,夢與現實彼此偷渡,無能分辨,拼接夢境與拼接現實,成了迷宮的唯一出口。
前半部歧路裡的短篇,瀰漫著性、愛、死。些許部分也落入漫漫拼接的困境。「拼接而成」的小說血肉,是否是真切的血肉?「拼接後生成」的小說血肉,又該如何詮釋血肉的意義?這是可以不斷深述的自我提問。
這部短篇小說的上半部,展示了關乎記憶偽裝成夢境的嫁接技術。
在嚴格意義範疇去述說,這是聰明的偽裝,將虛構的執行落實於小說鍍膜層。那是一種將散文技巧高度演練的虛構敘事,極為手工,極為真切,面向敘事者表演的黑暗多重膜。
揭開這層膜,之後,另一分岔的歧路,轉向科幻小說的領域。
後半部也如這部短篇集前半部曾有的自我提問:現實又那麼值得讓人活在裡面嗎?
隨後接續的四則短篇,也在呼應這個提問。不過,稍稍放緩了拼接。炫目的美文詞藻,仍然繁密編織。作者更願意將古典意義的小說元素,透過科幻的類型,流現出來。
〈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論及死者記憶存取與輸出導入,另外淺觸了科幻小說常面對的身分階級命題。〈幻肢〉則借道了賽博龐克科幻,透過缺席者與缺席的肢體,寓意人工智能與女人機體之間的「人為何物」的未來問題。〈保險套小史〉則是一次時光跳耀,小巧地假設了某個科幻小史背景設定的可能。
〈女神〉則是末日科幻,觸及範疇較廣,也更多進一步想像科幻的討論──列舉幾點細節:
故事主人翁伊雯是否能夠理解葬禮?她為創生者老先生思索的葬禮,是否存有理解亡者為何的意義?身體的腐壞,也是自己甦醒而為人的認知⋯⋯誕生這類角色的意識設定,伊雯心生的「一種文明提早滅絕的惶然哀傷感」,便能在沉睡之前甦醒之後建構的自我認同,以及我是否只是局部藍色伊雯的自我猜疑。
不論是前半部青春的消亡拼接,或是臨摹科幻輪廓的後半部,作者致力於華美詞藻的細膩與用心,透過文字向外傳輸。另外,小說人物們的舞台劇對話風格,也生出了異樣的設定思考。舉例如〈女神〉的尾句:「又一個伽梨女神」──伽梨,若放置在印度教的神話,是軀體深藍色的地母。她是黑暗的、闇域的兇殘者。
女神的誕生,誕生於虛構,那神話軀殼,最終最終的本諭,依舊直指時間。
在那末世留存的城市裡,仍有無數複寫而成的女神。
在這部短篇小說集裡,性是複寫,愛是複寫,死亡亦是拼接之人與拼接之機體共通的複寫。拼接的目的,應是小說處於分裂形式最終可抵達的「活」。小說的生物性格與細胞分裂不同處,細胞分裂週期短暫,小說的生之週期──若誕生於分裂之後,便有機會大於少許可有可無的意義。
謹以本篇讀後感,向誕生的新作家致意,期待屬於他的下一次分裂與繁殖。
高翊峰
導讀
「巫」的延續
黃家祥的小說有一種「延續性」,並不是故事懸念、身世回憶的延續,而是一種我年輕時感覺到自己渾身毛孔裡有的,但如今隨著我的身體、意志衰弱而愈難召喚出來,類似「巫」的延續性。很像我年輕時讀吉本芭娜娜,甚至井上靖寫不倫戀的那些小說。有一種可能是,在那個年紀的靈魂器皿和所裝盛的液體,兩邊尚不協調,或未得到人世──不論是欲望、愛、經驗,還是對許許多多他者的理解──饜足的填滿。所以會透過「內部開掛」──最寂寞的戀人之間的潔淨性交;像奏鳴曲般的迴旋盤桓;穿過夜間森林,不同暗影中枝枒葉叢四面八方輕觸擊打的敏感;最後其實就是無人知曉其視框如何如含羞草葉片般,次第打開的夢。
這是一種非常珍貴的特質,或曰天賦。我都無法想像,對於這麼年輕即將自己演化成一架這樣危絕、純淨、向更高的難度挑戰,發出靈魂奏鳴曲的琴;或是做出許多讓人屏氣不敢呼吸的冰刃滑翔、空中三轉跳乃至四轉跳,乃至於一種年輕創作者不自覺的恣意跳躍。我究竟是要像個老頭,人世的過來人,不動聲色以「小說」更笨重、沉纍的繼續裝備、鼓勵他;還是就是在這樣的時代中,見到一隻著火的蝴蝶,像那些絕美之詩本來就寫於二十五、六歲的天才詩人,安心讚嘆就好。
我曾看過書上描述一件乾隆官窯釉裡紅瓷瓶「筆意纖細,釉水肥滿,色彩豔麗」。這便是我讀黃家祥的小說裡許多美麗段落時的心情,「性」當然是一部分,極親近之人的死亡(後座力)也是一部分,他在裡與外,個人與群體,敏感的心靈與不可測的命運戲劇性之間不斷變幻著,這和他自己在「幻影中搭橋建棧」、「無中生有」的建築執念如此接近。
《太陽是最寒冷的地方》以一個受創的「年輕者」(這是在日後,或世界上更多的大小說裡所終要取消、變形的敘事特權),去面對那未經協商即已丟給他的「很久以前就老去」的世界。但這些小說的願夢(而非殘酷)帶有一種「快樂王子」的,或前八十回的賈寶玉,那種只能以童話的無限柔羽以及無限的真摯,去成為那整個傷害「大爆炸」劇場,其中共同參與的一片。「我」不是無能的旁觀者(既非暴力的原罪、亦非受侮辱與損壞者),時間、夢境、重建的「原點」虛擬⋯⋯,這些都因為「我」如此形銷骨損、傷情而無法自拔。所以我們終究會慢慢理解到,其實這並不是「〈快樂王子〉的故事」,而是「說這些故事的『快樂王子』」。
這個「我」孱弱、年輕,但又如此全面啟動所有的「他感」;可是這個「我」又沒有我年輕時,身邊遇見的天才創作者,那種如同《金閣寺》、《人間失格》般,奮力摔爆自己這把電吉他的,那種「對未來無知」的倫理梭哈。
這怎麼辦呢?這樣珍貴的年輕歌者,其實更像比他早一百多年的那些垂死天鵝,或躭溺於倒影的納西瑟斯。但因為他終究是穿行過所有「變形記」都實現過的二十世紀一百年之後才出生的童稚一代,如果不選擇電玩的世界、社群網路、饒舌樂的快速拍點,或是YouTube 上那些「十分鐘看懂某某電影」,他會被一些老天使們規勸,語重心長的警告:「不只是時空歌者。而是悉達多之途。」
簡言之,我想對這位年輕的創作者說,你已是最好的弦、簧片,就像是分格蜂鳥每一瞬拍翅畫面的瞳術。要珍惜你的天賦,好好的去感覺、經歷現在這個當下,並持續地思辨未來,三十幾歲的、四十幾歲的、五十幾歲乃至更後來更老的生命,像眼下你的小說長出來的那些不可思議的觸鬚般,可以去體貼在遭遇輕重不同的傷害打擊後,人們之所以各自用那樣的姿態站著、蹲下、眼神空洞,或輕聲交談,去體貼人們之所以會如此構形自己(並且形塑他人)的能力。
祝福這本小說。
駱以軍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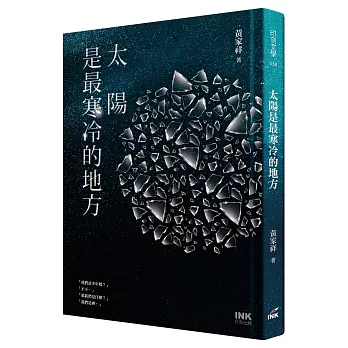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